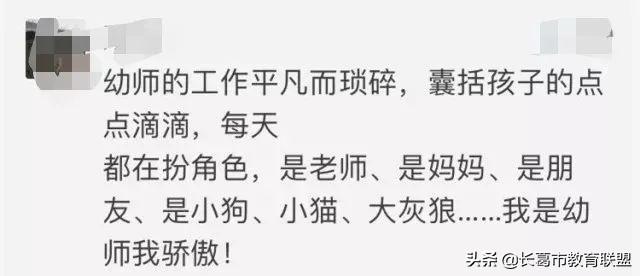文|郭晔旻
拜美洲白银所赐,整个欧洲(尤其是西班牙)俨然一个吃得脑满肠肥的暴发户。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雄踞亚欧大陆东部的大明王朝,却正在陷入“很差钱(白银)”的窘境。
隆庆元年( 1567),明廷宣布:“令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国朝制钱及先代旧钱,每八文折银一分,不许任意低昂。” 这标志着原来严禁交易的银两正式获得了明朝法定货币的地位。只不过,不同于纸币(“宝钞”)理论上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的情况,市场上白银数量的多寡取决于银矿的储量(及开采量),而中国恰恰是一个银矿贫乏的国家!
表面上看,明代中国的银矿似乎不少。湖广、贵州、河南、陕西、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多个布政司(行省)都有分布。可惜按照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的记载,在其中,浙江、福建的银矿,有些在大明开国时就已关闭,至于江西的银矿,干脆就是“有坑从未开”。至于河南、四川、甘肃等地的矿山虽然也称为“美矿”,但储量不丰,“生气有限”,“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

《波龙银矿图》
既然如此,云南的银矿产量又如何呢?比起新大陆上的波托西银矿,实在可以用“少得可怜”来形容。据记载,天顺四年(1460)云南省的白银产量为十万多两,这个数字已经占到了全国全部银产课额(十八万两)的二分之一强。十八万两是什么概念?依照明代的度量衡制度,十六两为一斤,一斤折合现代596克,十八万两也就是区区6.7吨。幅员广阔的大明帝国,全国的年产银量,今天用一辆东风厢式卡车就可以全部载走了。
之所以会如此,储量是一方面,炼银技术是另一方面。从秦汉以后,古代中国就一直沿用从铅中或用铅提取银的“灰吹法”。这种技术的原理是利用铅易于被氧化成氧化铅以及氧化铅可被排出或被炉灰吸收的性质,将金银从铅中提炼出来。其出银率不能与“汞齐化法”相比。按照陆容在《菽园杂记》的记载,一箩筐矿石重二十五斤,得银在三四钱至二三两之间,也就是说最高也才1.2%左右。
更加雪上结霜的是,长期开采导致银矿储量趋于枯竭,而采银的成本却在飙升。比如浙江东部的一个银矿,永乐时期(1403—1424)年产7万7千多两,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年产量已经骤降到1万两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