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卫霞
《礼记•乐记》上说: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当然,我们要明白这是先秦儒家学派从特定的政治角度来阐述音乐的:通过听音乐可以觉察世事人心的变化态势,从而反映政治。而我以为声响是音乐的本源,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对自身风貌、风尚较直接较客观较纯粹的表达。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也有说:乐听其音,则知其俗。
今天,就约你,单借声响,结识我的小村庄,走进我的小村庄——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愿我们能聆听到原汁原味的村风村貌。
乡村多声:常声奇声,乐声噪声,长声短声,大动静小音讯。
不信你且听——雨落有声,花开有声;鸟鸣、雀舞有声;草长、燕归皆有声;乡下更常闻听到虫儿呢喃,马儿嘶鸣;雷电风啸有声,霜雪冰冻有声;人,吃喝拉撒、婚配嫁娶、生老病死哪个没响动?
好,让咱们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首先调到乡村高音频道-一105.5(要栋屋)音频:“夯嗨来喽——开嗨夯喽,嗨啊嗨嗨……”天尚早,但见七八位壮汉光膀敞怀,手握溜滑油光的近乎包了浆的酒瓶口粗的麻绳,一条条麻绳正系在一个个钢环上,那钢环套在大索链上,而索链就紧紧地箍住圆台型重约二三百斤的石墩下围,石墩也就是夯砣,被装饰得凛然有型。
随着夯歌的节奏,夯手们齐用力,一提一松,一起一落。上起高至脖颈处,下落“砰咚”一声闷响,砸至地供(地基)一个夯砣凹印。
那夯歌号子喊得整齐有力,声势浩大,号子喊起来了,就来了劲了;喊起号子了,枯燥的劳作也就有了趣了。
那夯歌的唱词灵活多样,见啥喊啥,亦诙谐亦庄重亦热烈。
要掉头拐弯,夯头:“嗨啊嗨嗨--往东错啊”;有人偷懒溜号,走神儿了,夯头:“嗨啊嗨嗨--瞅‘假妮’(绰号)哟”,众夯手心灵神会,哄笑一番,和着:“软面筋呀”,或者和:“麻绳弯呀”反正,最后一拍都刚好落到一个点上。
如果遇到大活儿,工时长,干脆穿插进去名篇英雄人物故事连载;有时也会穿插进去当地的顺口溜;也有插荤打科。不管啥词,调门总是高亢激越,音色总是浑厚阔远。
看夯如看戏,场面热烈,一家打夯,整街喜庆。开夯、歇夯都有人关注,仪式感超强,打夯这农事为丰盈人们的市井文化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打夯为盖屋,盖屋为娶媳妇,一代代人烟,一辈辈希冀,夯歌咋个不动听?只是现在都换成了气夯、机器夯,那呆萌、敦实的夯具被遗落到了哪里呢?它是否也总会想起再一次跃起,再听听夯手们喊喊夯歌,来惊扰一下这寂寂的烟火尘世?
堪比打夯音量的,那要数得着唢呐声,接下来让咱们换到婚配嫁娶99.99(长长久久)音频。每到腊月,村里得接上三、四起婚事。
一切准备停当,喜日子一到,房顶上高音喇叭唱将起来,《百鸟朝凤》最为经典。
那声音力透村庄,响彻田野。
迎亲的马车扎成窑洞状,大红缎面的被子披挂周遭,迎亲的高头大马也给扮上,头顶红缨穗,踝系红绸缎,颈上套个大花环,这马中骄子更加俊逸了,咴咴嘶鸣,更加欢畅,引得鸭唤呱呱,鹅喊嘎嘎,猫啭喵喵,猪喘哼哼,犬吠汪汪,羊叫咩咩。
主事的大支(明白人)拿人分派使唤个不停:“四蛋,你去东墙贴上红喜字”,“倔根,你去点上两支红烛”……
院子里几口地锅阔挺挺地支起来,炉膛里干柴烧得“嗤嗤”作响;鞭炮噼里啪啦响不停,“新娘子进门喽”乡亲们前挤后搡,簇拥着新郎新娘,齐刷刷涌向天井处举行典礼。
锣鼓喧天,唢呐高奏,唢呐手铆足了劲儿,鼓动双腮,一吸一呼,似青蛙的大肚皮一凹一凸,那聒耳的高音就憋过长长的响器管突地从喇叭口扩泻出来,那调门儿就像迎风高扬的战旗昂扬欢腾,一浪高过一浪。配乐的吹奏手也跟着上紧了发条,加大了肺活量,那密密匝匝的音符就俏皮地跳到闹喜的孩童的门囟子上,弹跳到婆姨们的发梢上,欢快地飞到亲人们的眉宇间,又飞到树杈上,钻到菜园地垄里,散落到老爷们儿吧嗒嗒嗒吐出的烟雾里。
实际上,这激越的唢呐声声,婆家人,听着是欢欣鼓舞,饱蘸幸福;娘家人听来似恋念忧思,多有不舍。
院子里,四邻嬉闹着,锅碗瓢勺“砰砰啪啪”碰撞着,厨师们的菜刀“当当当当”响不停,热油“呲呲啦啦”爆香了葱姜大料。羞答答的新娘叫声“爹、娘”,众人都被暖化了。
“总算把媳妇娶进家了”,做了喜婆婆喜公公的爹娘,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怎么还有啜泣声?喜婆婆喜公公喜极而泣!主人散烟,劝酒声:“亲朋们,吃好,喝好,照顾不周,多体谅。”“明年孙子就哇哇叫了”众亲人捧场。
万事万物无不在辩证地行进中,人类繁衍生息也一样,有婚配嫁娶,也有终老病亡。接下来把频道换成音频88.88(拜拜喽)。
人离世了,孝子们披麻戴孝,涕涟涟,泪盈盈,哀嚎连天;唢呐转大调捏尖声,凄凄怜怜,告慰亡灵。那大悲调吹奏出的哀伤的《哭灵》把亲人们的痛丝丝缕缕地拽扯出来,把已故亲人在世时所有的哀怨、沧桑激将出来。“你怎么就狠心撇下儿女--”,孝子们越发哭天抢地,吹奏手吹得越发起劲,一波又一波的哀鸣涨潮般汹涌袭来,那切切的痛,深深的悲恋,撕心裂肺,惹得观礼的街坊,泪扑簌簌而下。
村庄哀鸣,天地呜咽,直叫人肝肠寸断,唢呐声声,送走了一尊又一尊亡灵。
小村庄的大喜大悲就是这么直白,喜就大喜,悲就大悲,毫不矫饰。尽是本色出演,渲泻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村庄的道白。
小乡村多音频,请把频道调到86.86(掰扯点聊)。小村庄的土腔民谣也别有一番风味。村民们不懂高雅的音乐,没有专业的艺术资源浸染。那土腔土调的顺口溜一样动听、有趣、温暖入骨,我们都是奶奶、外婆教着唱着这样的民谣长大的。
上了年纪的人,闲工夫多了,哄小孩儿又不需要多高的智商,哪管它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张口就来:“巴巴狗,戴铃铛,喤浪喤浪到集上,买个桃,桃有毛,买个杏,杏嫌酸,买个栗子面丹丹。”
小时候,你是否每到雨天就开唱:“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整日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的二婶不管见谁,一见面便招呼:“石头(任一人的小名),石头,臭石头,喊你三声不吱声,给你个驴粪团子压喉咙。”
娘把着娃的手腕儿外送里拉:“筛箩箩打箩箩,麦子下来吃馍馍,筛糠糠打糠糠,麦子下来喝汤汤。”
你又是否曾和小伙伴一起唱:“咱俩好咱俩好,咱俩赶集买唠佬(猪),我牵着你撵着,屙了屎你舔着。”好俏皮!
娘巴望着你,想到你长大的光景比对《墙头记》那场戏里的大怪二怪,不由唱起:“山喳子,蚁巴(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扔在高岗上,烙油饼打汤汤,媳妇媳妇,你先尝,我去高岗上接咱娘。”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岁两岁啊没了娘,跟着爹爹还好过,就怕爹爹娶晚娘。”年幼的你,那悲悯之情是不是就是那时启蒙?
还记得那个游戏吗?“‘荆棘灵,砍菜刀,你那边儿哩紧俺挑’,‘挑谁吧?’‘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爹抱,爹不抱,叫娘抱,娘不在,叽里咕噜滚下来。”其实这诸多的词中,也涵盖了一些当地的风俗人情,是不是勾起了你那么清晰的回忆,就正因为它简单到近乎粗陋,孩子们夜夜听着如此上口的歌谣甜甜地进入梦乡。
下一个频道,村庄文艺,音频66.66(乐悠悠)。听山东快书讲上一段《武松打虎》,更多的时候也听过坠子书,瞎腔,花鼓戏,两夹弦儿。
山东快书来咯“当哩个当,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这耳熟能详的段子,我猜剩下的你肯定会接。
小乡村,夜幕拉得急慌,家家的煤油灯闪烁着豆大的亮光。瞎子说书到点开唱,这瞎子,说书水平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他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反而自豪于自己的技艺,说起书来忘我、自信,“说书不说书--”拉声弦儿来开开场,那婉转悠扬的韵味一下就撒播开来了,金字招牌的嗓音,圈粉密实,只要他一到庄子,往那一坐,周围人群很快呜呜泱泱围将开来,他用音准,甩腔妙,虚实音结合得当,大小调转换适时,一声一腔一调,直叫人不吝亮嗓子叫好。村庄街头便铺上一层嬉笑开颜的月光,那半空闪烁的点点星光润饰了欢愉的腔调,好似有几路素雅的无名小碎花在空中开放。
至于山东梆子戏,花鼓戏,就略显大牌,耗些人力物力,小庄子得攒上几年才请得起那样的戏班子。
还有一个频道,播出的场面动静就不大上台面了。那就是骂街,吵架。
那声势浩大的场面,常让人面红耳赤,血脉贲张。
一般都是双方对垒,也有单方一头热(也就是自作多情)独奏的,当然,这样的戏是随机出演,无需购票,无需提前抢座,无需搭建舞台,随时随地,多发生在农闲时节,每每围观群众自动空出一块地作为演出场地。
这种较量种类繁多,形式各异,规模有别:有男女老少家族混战、有妯娌对骂、姑嫂暗讽、两口子武打、婆媳大战。有速战速决型、有拉锯持久战、还有你追我退我退敌追的翘翘板型、文争武斗型、也有连载,不一而足。场场精彩绝伦,猛料、黑料频频爆出,那污言秽语是少不了,多有拿人的生理缺陷开涮,常插播蹊跷呱,老俗理,明白账,俚语、谚语、歇后语,语出惊人;实词、虚词、象声词,层出不穷;打比方、举例子,明喻、暗喻、借喻,夸张、排比各种修辞;衬托、烘托、细描、白描、渲染、对比手法不一,有时骂几个小时不见重样的字句。
他们没学过表演,但他们是最好的演员;他们没练过写作,却是最出色的语言大师。这争斗的起因通常是你家的鸡、他家的狗,前街的菜地、后院儿的歪脖子柳,鸡毛蒜皮,你怨我翻白眼,我嫌你斜瞅。
骂街这档子名角要数村北头的二臭娘,天刚蒙蒙亮,她就早早爬到屋顶开了嗓:“谁偷俺家那只花公鸡来?你吱一声。搭谷子搭米搭工夫,养大了给你家鳖孙尝鲜了?若是……你要么……不然我骂你早着里。”突地切换了语调:“二妮,给我端碗水来”。确实,两天了,第三天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悠长。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这种骂街当属火药含量极少的,与婆媳相争、妯娌大战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妯娌大战应属火鞭中的二脚蹬,兑出来祖宗十八代,开卷不停歇,配上经典的肢体语言,伸长脖子瞪起眼、横起鼻子竖立眉,挽起袖子,跳起老鸹(蹦高),唾沫四溅,脖子、臂膀、手指、唾沫,凡位移则统统对准敌方,泼辣无比,机关枪似地爆粗口:“啊呀呸,得罪我,我饶不了你,摆什么臭架子,啊呀呸,试试,我咒骂不死你,呸呸呸--噎死你,呛死你,“咔嚓”撞死你;老天爷睁眼,……”很奇怪嘞,上来火,咬牙切齿地发狠,但,再狠再绝,过后,她们却很智慧地由怨化缘,一般很快就缓解了的,不耽误事事仍然相互帮衬。
我想,那艰辛的日子和繁重的劳作,把人熬苦了,这也是缓解宣泄的一种被动方式吧,当然不足取。也让我们认识到乡村不只是悠然,更有现实的骨感。
快换频道吧,你别再入了戏,哈哈。
好,就调到乡村买卖频道91.91(就要了)。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声声叫卖声,把个小庄子搅得痒痒的,也多了一丝生机和情趣,酿就了小村子浓浓的生活气息。
地排车挂铜铃,行几步,拉响一声,一步一“铛”,“换豆油哎,--换豆油的来了。”
卖香油的简便些,骑个二八自行车,后座上就可驮上油桶,一手把着把,一手敲梆子(绑在车把上的形似小枕头的中空木质乐器)。“梆梆梆”一路飘荡在小村庄的上空,无需动口,大伙都知晓买香油的敲梆子。
“磨嘞呀剪子嘞,戗嘞菜刀,修理钢筋锅……”。那捏腔拿调的叫卖声,抑扬顿挫,宽窄相称。“收酒瓶子来喽,~~”“破铺陈嘞喂,烂套子,烂鞋底子嘞喂,长头发,塑料纸,换盆换锅换碗勺嘞喂嘞。”“锔嘞喂盆来锔瓷缸,锔手镯嘞喂锔瓦罐嘞喂”叫卖诙谐多味,饶有风趣。“小(拉长音)鸡了来,嘞喂赊小鸡,小鸡了嘞喂赊小鸡……”这高质感的有腔有调的吆喝,被孩童争相模仿,也成为乡亲们日常经典的学段,比老师念的课文好听多了。
“卟唥卟唥,卟卟唥唥~~”货郎摇着货郎鼓,有的担担子,有的推担子车,百货齐全:梳子篦子;跳蚤药虱子药;针线叵箩,糖豆洋火,应有尽有。爱跟在这小商贩身后的,多为村子里的“逍遥客”,或是好吃懒做的佛系婆姨,这帮闲适派别占了一半的业务量,他们之间便尤其熟络了,村子内外的小道消息也由他们负责散播。
至今,这堪比梨园唱腔的吆喝声依然温度犹存,韵致纷呈,百听不厌,回味无穷。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一村又一庄.....”同是为生计奔忙,只是有人选择了去“闯”。
还有那村里的大喇叭的童音“滴答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承载了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苏轼《浣溪沙》,诗词中的乡音也很是入耳。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也为大家播放了一席乡村的田园生活,恬淡诗意。
如此林林总总的声响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娘在村口喊起的那句:“家来了,饭中了,吃饭哩!”
好恋念那回不去的乡村时光,那听不到的村庄原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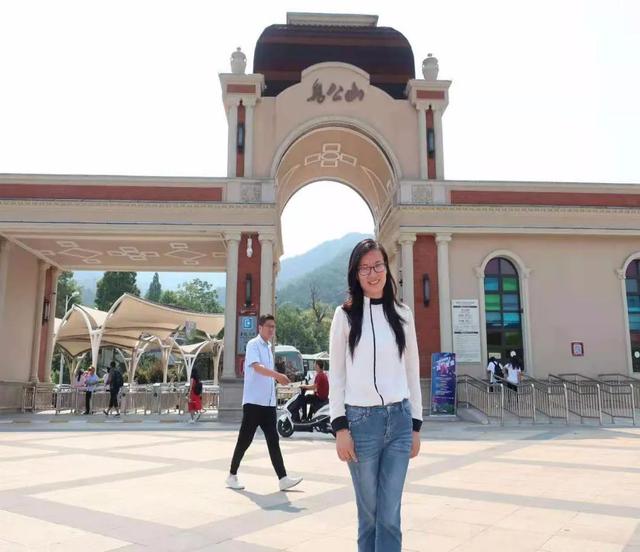
【作者简介】:张卫霞,笔名,文行我素。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为师,但求志洁行芳;为文,但求如琢如磨;为人,但求从简从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