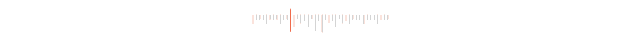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记忆里有这样一幅画面:广场上立上两根高高的树杆,一根麻绳系在树杆两端,中间挂上一白色的大幕布。那曾经是我们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也许你会说:“这不就是看电影么?有啥稀奇的!?”。 是的!现在电影院里买张票,说开始就开始,还有爆米花饮料果汁,影片的名字可以自己任意挑选,环境舒适,几号厅几号厅自己甄选,3D影厅?2D影厅?巨幕厅?几十块钱一张的影票,也不贵。你!就是主人,任意挑选,“运气好”,甚至还可以包场!但是无论如何,再也买不到当初那时候观影的味道。时过境迁,同样还是看电影,从前的那“味道”只存在我们的记忆里,再也回不去了!
再想感受那种疯狂,那踮起脚跟,拼命插队,抢占前排正中方位,打起雨伞不离场的激情;那种影片突然中断观众齐刷刷回过头瞅着放映员的期待眼神,那种放映员还未到场现场就满满的入座率。没有锣鼓喧天,但有人山人海。这感觉,只有在几千上万人的体育场、剧院看明星演唱会才能找到了。

露天电影,其实兴起很早,从解放前的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再到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开始比较普及,七八十年代进入高峰期,一直到90年代末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这些年某些时段偶尔也会有特殊情况特殊时间地点放放露天电影,但都是零星开花,非主流了,例如某些地方旅游景点特别放场露天电影,集体感受,带给人们一点怀旧情怀。那就如同是博物馆的古董,你是在瞻仰,不是在把玩。你享受的只是回忆,而不是电影本身。
笔者最后一次看露天电影是在北京某工地施工时,炎炎夏季,公司工会给广大农民工慰问送福利,直接放了一场电影《大笑江湖》,有几十人观影。笔者看了几分钟,特留下几张照片,电影没看完,照片拍了不少,情怀场景的捕捉。因为很珍惜这场景,当做是一个“仿古”作品记录下来吧。而真正的“古董”,只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我是80年左右出生的人,正赶上改革开放春风吹满地,沉寂了十年的中国电影业低谷期正复苏。露天电影,是往我前面数的50、60、70后,往后一直到90年左右出生的人都有过的美好记忆。文革十年动乱,几乎没有什么电影可看,都是些类似革命样板戏,政治影片,电影胶片大都被烧毁或封存。
1978年开始,电影业逐渐复苏,各类文艺青年开始大显身手。那时张艺谋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唐国强刚进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来成功饰演了电影《小花》里的赵永生,冯小刚呢,他还在部队里当文艺兵。中国电影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沉寂十年,才子佳人们酝酿已久,观众如饥似渴,演员们也是精打细磨,执着于为艺术而艺术,为观众而艺术。不是我老了过时了,也不是我怀旧,客观评论,80年代的电影和90年代的歌曲是中国文艺复兴出现优秀作品最多的年代。笔者去年特别去看了朱时茂主演的1982年拍的老电影《牧马人》,忍不住手机录屏保管画面和对白,就产生反思,如今电影在技术层面上是提升了,为何很多影片质量却不如以前?2021年坐电视机前第一次看这部老电影,还是让我感动了许久。这电影被剪辑在自媒体上又再次火了一把,不少90、00后的年轻人也一样推崇。

老照片-村部旧址 2008年摄

村部主干道 — 露天电影挂幕处 2008年摄
上图就是笔者童年记忆中,我们家乡露天电影放映的主场地—村部。那时候村部流行的喊法是“大队部”,去镇上就是去“公社”,南岳庙公社、鲇鱼须公社。这是2008年我回乡探亲特别有心捕捉的画面,当时就想着某天,我要把这里的美好记忆抒怀。从前的广场比这个大,旁边没有这栋摩托车旁的房子,那个大牌坊大门头的礼堂如今已拆了。
辞旧迎新,现在是崭新的村部大楼。


80年代,电视很少,一个生产队也只有几户人家有电视机。看场14寸的黑白电视也是排号入座,自带板凳,还要跟主人拉关系。那时家家户户能普及的就是收音机吧,还有村里的高音喇叭,童年记忆里,我父亲带着我听收音机,啃大发饼,就是每天晚上最温馨的时刻。至于电影,那是奢侈品,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是1985年左右,在上面那个大礼堂看的,那是我最早的关于电影的记忆,片名《大刀王五》,只记的有一个砍头的镜头哗的闪过,血一洒,其他就什么都看不懂了。大概因为村部有会议召开,总结大会,政策宣贯,全体村民必须参加,为提高群众积极性,村领导们会搞点小福利,例如放场电影,或者按人头发两个发饼。
80年代,一般是镇上或者县城才有电影院。其实我们村还算时髦,你可别小看这破门楼,当时可是显赫一时,威震八方!大概在1988年左右,这个建于1983年的村部礼堂因为拥有400个座位,几乎可以容纳全村每户一个代表开会,特被人抓住商机由私人承包,平时放映电影,取名“石英影剧院”。村里广播发达了,会议就减少了,村部礼堂摇身一变主要身份成了民营电影院了。记忆中小时候感觉石英影剧院那门楼是雄伟威武,门口两边墙上是贴的醒目影片海报,里面高大的舞台,长长的座椅,两排电动吊扇。我每次路过那里,就如同如今经过城里的体育场、大剧院一样膜拜,经常大门口凑热闹,窗户口闻闻味道。绝不是下图这灰不溜秋,乌鸦栖在枝头的破败景象。

石英影剧院-遗址 笔者摄于2008年 现已拆除

影剧院内部
由于内部照片无法提供,只有用一别的地方拍摄的照片代替了。村部礼堂改的“石英影剧院”,当时可是火爆了好几年,里面火到啥程度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从来没买票进去过!反正比我接触的我家乡岳阳的某万达影城入座率要高,也比我定居的某城的不远处某某大影城要牛叉。除去和放映《战狼》那段时间比,当初的入座率对比绝对是碾压级!
我讲几个故事说明,当初的火爆程度有多大。买完票,进检票口要经过礼堂南侧面设置的一个两侧铁护栏的大概3-4米长的检票通道,这个两排的护栏有一米五高,反正我小时候是够不着。为啥这么高,怕插队的翻过去呗!那就是买了票的观众也要排着队挤着进去看,因为检票需要时间!如果电影晚上七点半上映,要想看完整的,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在检票口开门前早早排好队。这样可以保证看到激动人心的片头。如果来晚了,可能排在检票通道口就错过了片头。电影的票价是三五角后面涨到七八角直到最后1块。我记忆里最常见的票价是七角八角。电影海报就贴在这个图上破牌楼门子的左下角,我记的有《阮氏三雄》(1988),《阿龙浴血记》(1986),《鼓上蚤时迁》,《我在黑社会的日子》等。香港的电影会价格高一两角,为了宣传,村广播站会在领导讲完政策通知后,喇叭里突然传来一个地道的华容土话声音:“喂 喂,各位观众朋友们,今晚八点,石英影剧院!准时上映!香港彩色武打功夫片-####,故事惊险,有血有肉,请要看的观众朋友们,到我院准时观看!” ,一般播报两三遍,这时候通过生产队里的喇叭就传到每家每户了。
物价关系,七八角的票价其实在当时也算是不低,因为一根绿豆冰棍也就是一两分钱,拿得出手的压岁钱也就是两角钱。据我最近采访电影放映队的乡友了解,85年左右集体制的公社电影队放映员一个月的工资是25元,全职的,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放电影。拿影剧院早期五角钱的票价打比方,他们半天的工资大概只够买一张电影票,而家乡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大概是集体公社职工的一半,那就是一个农民一天的劳动付出,只够换一张当时的电影票。比对如今的物价水平,一个工人日工资三百左右,一张电影票,可不是类似于如今的演唱会门票了?这么打比方可不就是了解当时的供求关系了。所以,童年时代,包括上了初中,我每次路过“大名鼎鼎”的“石英影剧院”,都是“望梅止渴”,干啥?看海报。不可能拿手机拍吧,看海报内容想象一下呀!所以记住了一些电影名,但从来没有买票进去过!从来没有。现在很想买张票进去找哈感觉,找点情怀。影剧院没有了。
那哪些人买票去看过呢?笔者不知道,只有引发乡友共同回忆补充了。以前有买票进“石英影剧院”看过电影的乡友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观影记忆[作揖]。村里阶层也有很多,村干部阶层,富农,普通农民,总有人去看的。关于这里的故事很多,半价票有没有我不了解。那时候这样的乡村民营电影院,全华容县七十万人口到1990年才有30家不到,全县三十几个乡镇,由镇上的集体公社办的电影院也就十几家。1985年全县在三封寺镇出现第一个私人承包的电影院,有400个座位,而1988年我们“石英影剧院”也有400个座位,当时在全镇只有三家,都是村里有在搞电影事业的人,中咀、石英、朝阳。

八十年代我镇乡村电影院分布图 1989
我们镇是人口大镇,全镇有4万多人,八十年代基本没有什么出去打工的,全在农村!除去镇里街道上公社集体办的电影院一千个座位,它是老大,其他三家公平竞争下,分别可以管一万群众!那我们计算一下,假设这一万群众一个月平均买票看一次电影,也就是拿出一天的劳动工资,就是120000人次,每年只放映三百场,400个座位就可以场场爆满!我相信还是有人会买票去的,例如家里来贵客了请客啊,过年过节啊,富户啊,干部子女啊。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嘛?反正简单一句话,那时候农村买票看电影,就是如同如今城里买票看演唱会一样!
这“石英影剧院”出了很多新闻,例如有两人联合搞鬼利用一人先买票进去,检票后先进去的趁机把缺角的废票从影院旁边的窗户塞给同伴,然后同伴在我说的那个检票通道附近地上捡到撕去的边角用胶糊得大致相同,趁检票口拥挤混乱蒙过检票的混进去,这样就达到“一票两人”能省一半的钱。也有所谓的八十年代的“社会青年”,就是我们那时候华容土话叫“水老倌”一样的人,在检票的时候,故意起哄故意挤前面的人,趁机搞出混乱局面溜进去,毕竟管理人员有限,也不可能像火车一样半路上一个一个复查票。还有在电影放映结束前最后几分钟,放电影的会提前开门疏散,于是那些趴在窗户外面听免费声音的就可以进去看一会儿,感受一下内部场景了。
我哥哥说只记得有我外婆姨外婆进去看过一次买票的电影,是什么花鼓老戏,我外婆当时也是离这不远的太仙村的时髦人,善于理财,谁请客我不知道,按现在讲就是肯定有人请客,一共去了四个人,我外婆和我妈,我姨外婆和我表舅。我这年轻表舅当时20岁左右,人高马大,相当于“保镖”身份,大概率是怕姑娘婆婆们在那场合不安全,他应该不喜欢看花鼓老戏吧。检票的时候,挤成一团,太热闹了,大家又不是那么礼让讲究秩序,我外婆姨外婆在前面拿着票,挤了半天进不去,拼实力,谁力气大谁先挤进去找位置。我表舅上前开路,年轻人就是厉害,冲在最前面,左边蹭两下右边推压两下,“杀开一条血路”,于是顺利带领姑娘婆婆们进了电影院大门。
讲了这么多,言归正传,之所以从石英影剧院说起,是为了理解露天电影在当时的重要性。我绝不是跪舔,确实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真实的场景。
价 值!
现在也偶有露天电影,扯上那白幕布,但时过境迁,那价值早已不同,从前若是盛宴、大餐,如今是一根冰棍!价值差了几十倍不止。于是,同样还是露天电影,再也吃不出从前的那种味道。可能我们已经自己忘了当初的细节,背景,也听不懂那首歌《父亲写的散文诗》里开头几句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 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 。不看就不看呗,有什么了不起,一场电影有什么稀奇?这个父亲没去看,是做出了较大的牺牲的。我也是直到最近认真总结,才彻底理解为何歌词的作者将这一段没有删除。既然要花钱买票的看不了,免费的可不能错过!错过了,那可是要十分遗憾的。
露天电影是当时社会背景下国家给农村的一项福利,开支由村里统一出,乡里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是领取正式工资上班的职工。农民要缴公粮,羊毛出在羊身上,说是公费,实际上摊人头户数还是由大家集资,只是由政府统一分配给集体享用。

上图就是80、90年代农民承担义务表格,哪里有真正“免费”的呢?傻瓜!你小时候记忆里村里统一组织放的电影,都是你老爸老妈买的单!除去那些红白喜事,做大寿,生崽,乔迁,户主们自己花钱请电影队放的。这只是那个年代集体生活的一种模式啊!
那时候放映员是一项热门职业,不仅仅是放映员,电影院把票的、站岗的都是很令人艳羡的“有身份的人”。很多小朋友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当电影放映员,每天有电影看,还到处走天涯,身边MM也自然少不了。电影放映员就如同如今跑场演出的小明星,走到哪里都是令人羡慕的眼光。以我们镇来举例,有4个电影队,每队2人,一个电影队管六七个村庄,接近万把人。基本上放映频率平均是每个村一个月一场。我记忆中的村部露天电影放映频率好像没有这么高,说是有时去队里放,队长有能力,把电影队忽悠到队里就在队里拉上幕布开始了,消息不灵通的可能就错过了。我童年记忆中村部大概是一年放四五场的样子,基本上我都没有错过,因为我们有“情报组织”。这是“公费”报销的,还有偶尔去打打“牙祭”的。那就是某某“时髦”家庭,接姑娘、做大寿等请电影队放的,那些年一共也就赶上个三五场。可能我信息不够灵通,信息灵通的还可以多赶几场。接到这样重要“情报”我们一群发小伙计们一般是会风雨无阻赶场的。打牙祭的记得比较深刻的,是我舅家在太仙大堤上放的《康熙大闹五台山》、《霹雳舞》。前面队里某家里放的一个《武林志》、《八卦莲花掌》。
在村部放过的露天电影有《八仙过海》《大上海1937》《江湖奇兵》《少林童子功》《侠女十三妹》《铜头铁罗汉》《恐怖夜》《武僧》《索命飞刀》《血溅加拉曼》《过江龙》《天下第一剑》《百变神偷》《东陵大盗》《闪电行动》《女子别动队》《湘西剿匪记》《草莽英雄》《金镖黄天霸》《霹雳行动》《少爷的磨难》《八百罗汉》《霸王花》《皇家师姐》。在小学操场上还放过一次《无敌鸳鸯腿》。还有一些没有记忆或者记的模糊内容但是找不到名字的电影,例如一个外国的蚂蚁吃人的电影,好像讲的是非洲,人掉进去就是骷髅提上来。外国电影少,还有一个《被绞死的人》。




镇上的中心电影院学校组织去看过一场《中华英雄》《游侠黑蝴蝶》,骑好远自行车,这一次的观影体验又不同。郑爽主演的《游侠黑蝴蝶》里面开头有一个半裸露的强奸的镜头,小时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年代电影尺度不大,这已经是突破。出片公映前都是审了又审,经常在电影某处出现男女主人公暧昧情节,咔嚓,镜头就跳走了。电影一般是2-4卷,根据电影胶带盒的厚薄可以猜测电影的放映时间,是大片还是普通片,而在换片子的时候又会停顿那么会,画面上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乱码,没有如今的电影这么顺畅,等到再接上,连接好的还好,连接不好的掉了一大截情节。
以下是操军镇砚溪村乡友提供收藏品

收藏品图片由操军镇砚溪村乡友 赵大胜 提供

图片由乡友 赵大胜提供

图片由乡友 赵大胜提供
露天电影观影,观众都是被动的,何处停顿换下一卷,你不知道;影片什么时候结束,你不知道;甚至“情报”工作不到家连今天放的片子是啥,你都不知道。但我们最关心的不是这些,是今晚有没有?毕竟一年才几次机会,又不用买票,只要有,就向前冲。正是因为上面的三个不知道,才弥足珍贵,充满了一切的未知性。那份神秘色彩,如同掀开红盖头前的少女。每场露天电影开演前,你都仿佛是参加电影首映式的嘉宾。一切的一切,你不知道,也别无选择。绝不是如同现在看电影可以提前百度剧情,可以选择影片,甚至可以在电脑、手机上拖动快进,提前知道了剧情和主人公的生死、爱情的结局。
从前的露天电影,那才是原创的感觉!如同是如今演唱会舞台上的活人或者剧院的活人在给你表演,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而现在观影,是拷贝的感觉,首映完铺天盖地的信息就到了你耳朵里,甚至剧情你已掌控。这就是如今电影价值大不如从前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分享的感觉,去村部或者其他地方打牙祭看电影的,都是你的亲人朋友,发小伙计死党,到村部广场会师后,又能招呼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这就是集体生活的味道。如今电影院,哪怕是偶尔遇见好片,爆满,例如《战狼》《芳华》,但你身边的观众不再是那么熟悉,人越多分享的气氛就越好。
既然其他未知我们不在乎,那今晚有没有电影总要关心。于是造谣、鬼把戏也就有了市场。偶尔会被人告知:“重要消息啊,今天晚上大队部有电影” ,片子名也编了一个。等搬好凳子走到大路中间,远远一看,村部的那块白幕布并没有挂起,于是苦等,等半个钟头天都黑了,还没有挂起来,才慢慢醒悟,是被人恶作剧了。上过一两次当,也就有“防骗”措施了,防火防盗防发小,于是成立了可靠的情报组织。乡下每个队里一群娃娃中间也是有两三个大哥的,一旦接到模糊的不知哪里传来的关于今晚电影的消息,大哥们就会派小弟去刺探“军情”。因为露天电影是公家按制度轮流放映的,不像石英影剧院的私人影剧院,它是不做广告的,不认识放映队的人也不处在这小社会的核心地带,怎么可能掌握第一手信息呢?都是你传我,我传你,通过面对面口头传递。我起初是队里的小弟,慢慢过渡,时间长了也就成了大哥。这一套流程还是很清楚的。小弟必须对大哥忠诚,不能报虚的,当小弟接到大哥通知后,去踩点核实信息的正确与否,跑十几二十户人家的禾场,趁天未黑到那马路中间远远的看大队部的主路上那块白幕布有没有挂起来。一看到确定幕布已经扯起来,马上快速奔袭向这边跑过来向大哥汇报,这时候大部队早就拿的拿小板凳,长条凳,手电筒,拿的拿报纸,还有的是拿稻草把子等候好了。出 发!快步前进,有时候路上还要祸害几个农户的草垛子,偷点草把子去前排占位置。
由于我们那队距离村部有两里路,地段稍差,反应不会是最快的。大部队开到大队部,广场上的好位置此时早已经霸占了一半。一般情况下格局排布是如下:小孩子们大多是占据前面五六排的地上,垫上报纸,稻草把子,废纸箱,个别讲究的有正经垫子。地上的正中间是好位置,先到的先得。中间排是一些离得近的村民,搬的道具,长板凳,矮凳,椅子,早已就位。大部分,就是站立观影了,后排和左右两侧拥抱着主角放映员。放映员就在广场核心正中间靠后一点点,一张四方桌子,放映机放上面,旁边是电影带盒子。

老式电影放映机-乡友赵大胜收藏
放映前,基本上现场已经是围得水泄不通。实在来晚了,挤不进去,没位置了,还可以看反面。发电机一开,轰轰轰的轻微的机器声,放映员把放映机打开,如同如今那投影仪,射出一道光,投在幕布上。幕布是两种,3*4米的,还有16:9尺寸的宽银幕,大概是四五米长,两三米宽。那道光一射在荧幕上,证明放映时间快到了。人们开始兴奋起来,有的按捺不住的会打听第一个电影片名,因为第二个一般会精彩一点。好确定观影的投入成本,认真劲头,例如要不要占位置,去不去厕所。有的会派一个人去放映员身边看装电影带的盒子上的名字,提前掌控观影节奏,例如是不是重复影片。
在放映员打开那柱射灯的时候,放映员在调试机器,剪片子,上带子。人们各种各样的表现和表演,在幕布上、人群中展现。孩子们会把脑袋放到射出的光上印出自己头,乐得不可开交,有的人会吹起口哨,有的会吆喝“哦哦,嗷嗷”,有的会喝倒彩说放映员太墨叽,有的会把手伸到那束光里用手和指头做各种动作,还有左右手配合的隐晦的淫秽动作。这一幕幕场景如今的电影再也无法展现。
突然,噌的一声!噔噔噔咚!背景音乐声响起,电影开始了!以上表演骤然停了。现场静悄悄,鸦雀无声,只有电影片头上出品人、**电影制片厂等的名字在翻动,再突然一个 咯噔咯噔又嗡的一声!****** 片名报出来了!然后欢呼声、尖叫声、啪啪的掌声都起来了。
盛 宴 开 始!!
观影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除去故事惊险之处,大家齐齐的叫喊,搞笑的时候哄堂的大笑,这些如今的电影院里你仍然可以体会。但有一些特有的那年代共性的情景就再难复古了。第一是打架的。那时候农村闲人多,年轻人多,大量的社会青年没有出门像今天这样去打工,吃饱了没事干,所谓无事生非。看着看着,后面几排又打起来了,荧幕上皇家警察在打黑社会,荧幕这边社会青年,土话叫“黄腿哥哥”,准流氓在斗狠。有时发生纠纷地点距离放映员较近怕推搡,影片半途中止。而且有几次是同样几个人,例如我们村有家弟兄多,老三老四老五,打了别人,别人复仇从邻村带帮人跑来寻仇,电影放映场成了斗殴场。第二是,剪片子。有的是系统分级自然跳过,有的是放映员根据职业要求中间裁掉一大截。这时候现场嘘声一片,起哄的开始叫。当时放映《妈妈再爱我一次》,台湾电影,创造了极高的观影记录,这部片子是免费在室内给小学生宣贯教育母爱,也是我们小学时在石英影剧院组织看过的唯一一部电影。它賺够了内地人的泪点。

据说是电影有几个尺度较大的暴露镜头,我没有记忆,可能放映员给小孩专场播放时剪过了。后来又在村部重新当露天电影放映,演到激情处,刚一分钟,咔 嚓,后面就剪了。现场一阵嘘声,一群堂客们还调侃放映员:“这有么子意思啦,就一分钟? 后面不要咔完额啊?!” 。电影队放映员蔡某某当时也是二十出头的帅小伙子,还未结婚,被这一怼,憋得脸通红通红。第三是,装 * 的。电影放映,剧情就如同是一个谜,谜底提前揭晓,你看前面的各类紧张,激动,替主人公担忧的心情马上变得不一样。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果每个人提前知道命运的结局,那一切过程就将变得麻木。通俗一点说法,不再刺激!偶尔观影,看到惊险处,这人死没死啊,男女谁跟了谁啊,大家都在自言自语,其实不是想知道答案,而是自然沉浸在剧情里。这时突然,后面有人直接大声说话讲答案,因为他可能昨天在别的村刚看过一遍,人群中刷了一把存在感。于是观众嘘嘘的责怪他,别显摆,闭嘴。这不是观众在和导演打牌你提前把导演的牌告诉对方吗,这牌打得就没味儿了。第四是 等片子。村部露天电影,一般是两个电影。某些时间段,观众积极性高,还会偶尔放第三个。某次,放第三个电影,电影名字是《天仙配》,原计划是晚上十二点以前到,因为电影带在镇中心电影院正在放映,要去镇里取带子,这叫“跑片”。这边放完两个,半夜了,大家都守在幕布前耐心等放映员去镇里取片子回来,路上衔接可能出了状况,直到凌晨三四点才拿来,观众硬是大部分没离场,躺地上瞌睡到三四点接上放看第三个片,结果放完一卷带子,天就亮了,幕布不管用了,看了个半截。
村部露天电影的过程讲完了,其他地方其他场合的场景大致基本相同。时代不同,价值不同,再寻找当初观看露天电影的味道,基本是找不到了。看看上面的细节,关于露天电影,在当时,放映员确实是主角,是小孩子的偶像。如跟他认识,可以知道第一手准确信息,还可以跟着去其他村、队多看几次不同的电影。如今的放映员,检票员,不再受人关注。我们村两个乡友曾经是乡镇公社的电影队的放映员,一个叫蔡三保,一个叫白祖文又叫白捡宝。一保,二宝,确实是当时两个宝贝级人物。因为一旦哪里出现他们的身影,那就说明,这估计有戏,有电影看了!唯有高高挂起的幕布和他们的身影,是最准确的消息。笔者感谢他们曾为乡镇电影放映事业做的贡献,让我们拥有这么多美好灿烂激动人心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露天电影的发展,从兴起到基本告别历史舞台,在时间轴上看是一个抛物线。1950-1970是兴起期,1971-1990年是高潮期,1991-2000年是低潮期、萎靡期。90年代末期笔者在大学集体看过一些露天电影,因为学生们人多且是集体观影,那味道和气氛还是不减当年。
各地经济水平不一,以我们镇为例,露天电影在1985年大概是发展到高潮期的高潮期!也就是香港和大陆合拍的电影《少林寺》最火的那几年,一两毛钱的票价,竟然创造了1.6亿的票房,相当于十几亿人次!如若折合按目前三四十的电影票价计算也是几百个亿,大大超过这些年宣传的几部大片的票房。而且笔者前面也分析了,那时的一张影票的实际价值远远大于如今的电影票价,按购买力计算就是千亿以上了。当时真是一票难求,买票还要托关系,黄牛价甚至炒到一元。城里的电影院放映火爆以后,农村露天电影又推了两年,笔者记忆里是1985年左右在砚溪村姨外婆家看的已经是录像带版的《少林寺》,那是人生的第一场录像,现场依然非常热闹,记得那晚上正放录像我还和同岁的老表两人打了一架,谁胜谁负至今不记得了!

1985年,我们家乡的露天电影发展到最高潮时,公社电影队(实际是我们村里电影队,因为主角都是我们村的乡友)曾经上过湖南电视台,甚至还可能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也出现过他们的镜头。那次是湖南电视台的记者下乡,特地来拍摄农村露天电影放映场景,当时放映队根据轮流规则,刚好在中咀村也就是上面乡村影院分布图的“中咀电影院”那块放电影,政府为了宣传效果,统一组织邻近几个村的群众都来观影,那次是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可惜那天的盛况没有相机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乡下集体活动多,1978年以前的各类政治运动游行批斗,通讯不发达时的经常性群众大会,后来80年代严打,经常开“万人大会”公审……在乡下如今再很难看到那样心齐,沸腾的场景了。
1984年(我们县的数据,我们生产队拥有第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慢慢兴起,1990年基本普及到两户一台电视机,然后录像带、VCD、DVD碟机兴起,后来网络的兴起,再到如今智能手机的兴起。随着时代的一步步发展变化,露天电影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露 天 电 影,那曾经的盛宴!
露 天 电 影,农村集体生活的最后一次疯狂!!
永别了,我记忆中的露天电影!请不要尝试在如今露天广场荧幕上找回当初的感觉。
如果我是导演,我要拍一部电影,电影剧情就是80年代农村人们如何看露天电影的真实场景,估计能火一把。我不是,就写了这篇文章。如果作者能带你找回当初那点回忆,就很欣慰。
浪子燕定 (严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