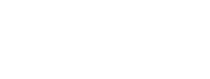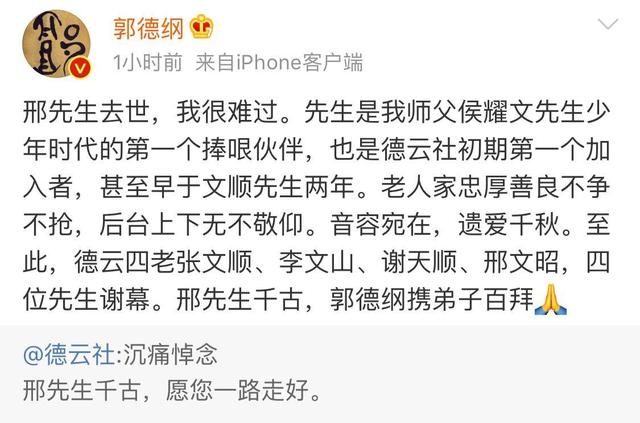文/马家骏
从上高小到读完高中(1940-1948),正是受戏剧熏陶印象最深的年代。读汉中圣水寺的沙沟坎小学五六年级时,凡是附近村庄以至汉江对岸的黄家坡、金华寺,只要有戏,不吃饭也会赶去看。有时下午放学,背着书包就老远赶到别处村子边临时搭的戏台那儿,看它个通夜,天亮再赶回学校。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常遭母亲训斥。那时我在农村看的戏有两种,一种是室内戏,一种是野台子戏。
室内戏并不是戏班子演的戏,只不过是戏的雏形。它又分两类,一是端公戏,一是花烛戏。端公戏通常叫跳端公。端公是通神禳鬼的祝觋,一般是道士打扮,戴瓦面方巾,穿八卦道袍,手持拂尘,有令牌在桌,会画符。富裕人家,老人病了,就请端公来驱病魔。当黄昏初降,人们拥进病家院子,端公捧一碗水,这里喷喷,那里喷喷;把画好的黄表朱砂符,贴在门窗上方。一般人家住一明两暗的上房(北房),中间的堂屋就是跳端公的场所。病人在卧房,有家人来往照应。堂屋正面墙上是神龛(有的有阁子),中间贴红色大字神镑,上书“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时代了,改为“天地国亲师”的也不多),榜下摆着观音或关帝等的瓷像,两侧贴的是三代宗亲或显考先妣的小神榜。神榜下是长条供桌(泥质固定的居多),上面放着供品和烛台香炉之类。端公的令牌什物就放在供桌上。堂屋正中是一张方桌,桌上供着刮得白白净净的全猪,桌下放一方升米,米中插香,升后有一个脸拧向后背拿大鼎的木偶,人说这叫申公豹(《封神榜》中的人物)。这时端公不停地挥动拂尘,围着猪转圈,身后跟着“童儿”(十三四岁男孩扮演)。堂屋的格子门全部开启,挤在廊檐槛的人们伸长脖子看端公的表演。我们十一二岁的小孩,钻进屋角,看得更为真切。端公与童儿对话、演唱,但内容却同驱鬼治病无丝毫关系。端公向童儿叫喊:小心要过河了!于是二人表演踏大石、跳过溪的动作。童儿喊师傅要翻坡啰!端公便作上坡下坡状。围着全猪转时,童儿问:猪为何大耳长嘴?端公作出解释。又问:为什么猪蹄子分成两瓣?端公说猪的家乡来了一位酷吏,下令捉本县的烧火(扒灰)老汉,于是全县成千上万的老公爹们,四散奔逃。有一群老头跑进死胡同,迎面高墙封死巷口,后有追兵,于是勇敢者翻墙跳下。不料墙内是大户人家的后花园,顺墙栽种的竹子,砍竹竿用了。墙下剩的全是锐利的竹桩。老汉从墙头跌进竹桩丛中,所以脚被划成两瓣。这大概就是猪蹄分成两瓣的由来吧!端公还拿一把刀,边割边唱:割猪头、猪蹄、猪尾……。那种端公调,我们还用来咏唱“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四时读书乐》)之类的诗句。端公割猪唱道:“割心子、割肝子,剩下一个猪鞭子(阳具),我们撖(读“喊”,拿也)到起没有用,你二娃子(指童儿)撖去做个帽绊子,初一十五耍牌子(摆阔气)……”。我当时纳闷:猪鞭子做帽绊子真能驱走病魔吗?

花烛戏又叫办花烛、耍花烛。青年男女结婚是家中大喜事,老表(表兄弟)们闹新房图个吉利红火。闹新房之前就是耍花烛。花烛戏一般在室内,大户人家则在天井搭上棚请客饮宴之后,黄昏棚下演戏。这种戏半真半假。真的是新婚夫妇二人,假的是亲戚朋友中的热闹人扮演的角色。在观众围出的场子中间,桌子上摞桌摆椅,中间坐着“土地爷” ,“演员” 两颊与下巴粘满棉花做的白胡须,穿戴整齐后,一动不动地高高坐着。他两旁各站一个“童儿” ,童儿粉黛化妆,怀中抱一个充填大米的枕头(我就演过童儿,抱着成十斤的枕头,在那儿站老半天,也是相当辛苦的)。这些“神像”下面,放一条长凳,凳上睡一个“和尚”。演和尚的,脸上画得五码六道的,黑眼圈,白鼻子,黑歪嘴。戴一顶大纸叠的船形僧帽,斜披一件用床单别成的袈裟。新婚夫妇来到“庙门” 前,叫不开门。和尚正睡觉打鼾,发出“Hou……shipi……Hou……shipi……”的声音。半晌后,和尚起身,挪开长凳,算是开门迎香客。他在前头一瘸一拐地引路,围着神桌转,还数着快板:“我,我,我和尚,没,没,没婆娘。有心出门接(娶)一个,又怕婆娘打死我;有心用纸画一个,睡到半夜要弄破……” 。领新婚夫妇到了神像前,要问新娘很多她难以启齿作答的问题,新人在观众哄闹声中又不得不答出含含糊糊的悄声细语。新婚夫妇还要给神上香点蜡,必须二人同时齐心做,动作调协不好,或被瘸和尚从背后碰撞一下破坏掉,那就还得在亲友们的哄笑声中重新来过。戏演到最后,神发话保佑新人将生几个儿女时,童子则用枕头使劲砸向新郎新娘,但常常却一齐砸向拐和尚。混乱中,有人偷偷划火柴点着了土地爷的白胡子,趁一片哄闹和混乱,新人躲进了新房,开始了老表们闹新房。

野台子戏一般在场院(打谷晾谷的地方)和村边(收割完的)田地里,是由职业演员演出的(也有村民的自乐班,但很少见)。这也有两种,一种是傀儡戏,一种是大戏(即人表演的戏)。傀儡戏又分两类,一类是布袋戏:一个艺人挑着担子来到集市或场院上,从箱里拿出大布袋,用竿撑着,艺人钻进布袋里,顶上側开着一尺半见方的、像舞台台面似的天窗。艺人两手套两个布做的小偶人,口含铁哨吹做人语声。偶人演出有情节的短剧,如王小打老虎、王小和人打架等。一出短剧演完,则由偶人向观众鞠躬,艺人的助手则向围在一圈的观众收钱。这种艺人,由河南逃难来汉中的居多。当地农民不干(也不会干)这种游乡乞讨的勾当。那些河南人里,还有耍猴把戏的。但那是杂耍,无情节人物,不算戏。另一种木偶戏演唱的同大戏别无二致,三国戏、水浒戏、才子佳人、神仙鬼怪,剧目齐全,所不同的是观众看到的只是偶人在动作。木偶戏通常叫“木脑壳” ,二尺多长的主竿上插一个略大于拳头的木制人头,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另撑两根弯头竿,上插人手(一般握拳,拳中可插入刀枪剑戟、笏扇杖旗之类道具)。给木脑壳穿衣戴帽挂须,俨然一个剧中人生成。精巧的木脑壳,眼睑、下巴还会动。演出时,用布或竹席围成边长一丈三四、高五六尺的围子,围子上方即偶人表演的“舞台”(有的高顶搭有苫篷)。艺人持木脑壳在围子里走动演唱,头上方的木脑壳在围子上做动作给观众看。小孩看入迷时,全以为是活的小人在表演哪。有的情节还让偶人打二踢脚,或跷起靴子来。木偶戏告诉了我很多历史知识和人情世故。不过在汉中,我没机会看提线木偶、皮影戏,十分遗憾。

由演员化妆演出的大戏,才是戏剧的正宗。过年、过节、谢神还愿、过庙会或农闲时,大户人家或团体的会首出面,请戏班子来唱戏。除了庙堂或镇子上有乐楼(舞台)的,一般在庙前阶台广场、村边场院或集市旁田地里临时搭起戏台。唱到夜晚,戏台两边前柱挂上灯;能点汽灯的不多,多的是铁丝圈套个老碗,装满桐油,用五六根灯草捻子,由剧务不时地站在凳上去挑灯。每当锣鼓一敲,四邻八乡的观众逐渐聚拢来了。台前,小伙子们挤挤搡搡,外圈是站在凳子上的妇女、老汉,场外是卖吃喝的摊子。远处、尤其是后台远处,是一堆堆押红宝、摸彩赌博的。开锣打三通,每通间隔15分钟左右。戏开了,头一出称“帽儿戏” ,观众多不去认真看。一般是一个老员外上场,在台中桌前椅子上一坐,半天才说一句。唱《三回头》的居多:“老汉……吕鸿儒……江南……人士……” 。半晌,旁边拉板胡的才吱吱呀呀膏弦子调音。台下人声鼎沸,卖醪糟的把风箱拉得啪啪响,小贩叫卖声不绝于耳,呼兄喊弟的,孩子哭的,吵架的,此起彼伏。剧务人员突然站到台口遮住演员大声向下喊:“狗娃哉!快给后台送开水嘛!” 真是乱七八糟!只是到“本戏” 开始,名角出场,大家这才认真看戏。可是,台口下小伙子像潮水漩涡一样,一会儿挤向东,一会儿挤向西。还有并不为看戏而来寻开心的大姑娘小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吃了很辣的凉粉、面皮子,染出了红嘴圈,汗冲刷了额头上扑的白粉,显出一道道黑皮肤,笑着喊着也向人群挤搡。农村唱的戏主要是桄桄子和汉调二簧。有好几个剧社游乡串村,到处唱戏。也有一些著名的角儿(当地叫角子):记得有一位唱大净(黑头、大花脸)的叫武德,武德声音洪亮,夜静时,几里地外都能听见他的唱声。他在摇曳灯光下唱《探阴山》里的包公,真像到了地狱。我特别佩服包公的胆略。另一位,能唱青衣又能唱花旦的叫小桃红,他年轻,扮相漂亮,身段婀娜柔美,声音很甜,表演起来,妩媚动人。但有一回,我去台后平场与同学划甘蔗,后台向下泼脏水,还有人揭开围子向外小便。我抬头一看:一个男人毫无顾忌地撒尿,而上身己妆扮成美女,原来是小桃红。这一下子破坏了我对他的美感。
上了中学,我家搬进汉中城里,再要看戏就得进戏园子了。剧院的戏,一种是专业剧社演的戏,一种是学生业余演的戏。县南中、省南中、平民中学等校,学生都有演出。这多半在校内礼堂,或操场舞台,或临时搭的台子。学生戏是余兴式的,不卖票。演出的多是话剧如《雷雨》之类,偶而有京剧折子戏如《捉放曹》或歌剧如《从军行》等。西北大学的学生有时从城固到汉中来演戏,则在剧院如后街的“汉中大戏院” 演出,观众买票看戏。大学生主要演的还是话剧如《雷雨》、《金指环》、《天字第一号》等。一位四年级学生赵伯毅与我家相识,他是西大话剧团负责人兼导演,每次来汉中演戏,就赠票给我们去看戏。西北大学还有京剧团,其中黄定、李冠军两位唱小生与青衣的男同学,与专业剧社人员一起唱《凤还巢》、《贩马记》之类。后来听说:李冠军下海当了专业演员,和一位女演员结了婚。黄定解放后是北京戏曲学校的老师。
职业剧社演的戏是中学阶段看戏的主要对象。但这也分两类:一类是落户本地长驻长演的,一类是外来演一段时间又走了的。本地剧社主要是京剧。因为抗日战争,外地(北方)人来汉中的日多,故京剧在汉中市民和知识界很流行。汉中城里的剧院,很少有乡下流行的桄桄子和汉调二簧演出,这些草台班子是无力去租正规戏园子的。东关后街的戏园原是唱京戏的,抗战胜利前后,东门里高家巷子新建剧院,京剧便迁入城里。而东关后街的戏园,一度由姜佐周领导的秦腔剧社演出。姜佐周,管子街(今青年路)人,能唱京剧,但为发展地方戏,故在东关后街唱起了秦腔。姜佐周的秦腔,我看过一回,但看得更多的还是京剧。京剧虽有各种剧社(如“汉声”等),而实力却在一些戏班子手中,有所谓刘家班子、高家班子、卫家班子等等。
刘家班子是由河北省逃难来汉中的,与我父母认河北老乡。1943-1944年间,刘家班子搭伙在东关后街戏园唱戏,我父母曾经包池座前排一长椅(五个座位)一个短时期,我们都能连着数夜去看戏。那时的演京戏,每天换新节目,头夜临散戏前便挂出次日戏牌:红漆木板,白水粉写上演员和剧目的名称,放置舞台口两侧,向观众预告,之后,次日挂于戏园子大门口。刘家班子主要靠他们的两个“女儿”:刘艳琴、刘艳芳。刘艳琴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嗓音甜美,会的戏很多。使我最难忘的一出戏是改编《红楼梦》的,戏名忘了,但我不记得《红楼梦》中有这一段故事。戏中说: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同水月庵的小尼姑妙玉恋爱,先是二人在大观园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秦钟从此得了相思病,妙玉拘于礼法,也陷入思念的痛苦。后来,秦钟病危,妙玉得知便借故去探望,但秦钟已奄奄一息。这出戏缠绵悱恻,尤其是生死诀别一场,让人撕心裂肺。已读初二的我,初解风情,着实感动得流了泪。
高家班子是落户汉中的戏班,不像刘家班子抗战胜利后就走了。高家班子的主要演员(角儿)是高小楼、筱小楼“父子” 二人。高小楼唱“铜锤” 、红生,声音高亢,黄钟大吕,令人振奋。《二进宫》、《九江口》、《古城会》是他的拿手好戏。张定边、关羽等等,在高小楼表演下,一股英雄气概,豪迈撼人。筱小楼唱须生,身材略高,脸上有几颗麻子,扮相英俊。他文武老生都唱得好。文生如《打棍出箱》、《乌盆记》唱腔悠扬,武老生如《庆顶珠》、《定军山》,身段利落,无论长靠短打都行。像萧恩、黄忠,连唱带打,令人心爽。高家父子的戏,我看的最多,从初中到高中,从抗战到内战,常看不辍。还有一位也住在东关,投靠在高家班子的女演员,叫龚雪娜,让我一生不忘。我是在高家巷戏院看“台票” 时认识她的。所谓“台票” ,是指在舞台上看戏。原来,我1945年秋读汉中联中高中一年级时有一位同班同学白介立,他不但是戏迷、会拉胡琴,而且认识各剧社的人。同学叫他“穿城过” 、“没遮拦” 。因此他虽没钱没势,却可以带我去戏院看戏,不但不买票(把门收票的还点头招呼他),而且领我去后台,并到前台两侧文武场的后面端个凳子看戏。别人问起买什么票看戏,则戏称看的是“台票” 。我坐的矮凳前有一位姑娘也看“台票” ,她一甩长辫子扫了我的脸,我揉眼时,她回头直低声道歉。我瞥她一眼,觉得面熟。事后她歉意点头走了。第二天看台票,不见了绰约的背影。忽然,台上唱起了《春秋配》,这才发现:唱姜秋莲的演员龚雪娜就是甩辫子的姑娘。姜秋莲受继母虐待,被赶到荒郊拾柴,她那么悲凄无靠,让龚雪娜唱得一阵阵心酸欲绝。我因“台票”离演员近,发现她真的在流着泪唱。我想也许她的身世与姜秋莲一样可怜吧。后来,共看“台票”,点头招呼而已,再后来,近半年没见过龚雪娜。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春游圣水寺回来,路过王仁桥,在道旁茶棚歇息,发现邻座是龚雪娜和她的“保姆” ,她认出了我,轻轻点了点头,含嫣浅笑。我无言回过礼后,扭头与同学说话,再转过身已见龚雪娜离去,她远处回头望了一下,轻摆婀娜背影渐渐隐去。我怅惘如失,同学呼唤,我才回过神来。此后,再也没见过龚雪娜。
卫家班子不像上述班子的人员住东关,而是住在周公巷子。白介立与卫家少爷卫瑜垣是汉兴中学(今汉中二中)同学,白介立家又住在周公巷南口府街(中山街)路南,所以我与白介立常从周公巷过,他带我去过卫家一次。卫家来客多,人们正在唱戏,我们停留片刻就退了出来。卫家的主角是卫丽芳、卫丽英“姐妹” 。卫丽英唱青衣,技艺一般,看过之后,印象不深。姐姐卫丽芳唱须生,唱做俱佳。她个子稍高,与女主人公很相配。尤其她唱文老生如诸葛亮、邹应龙、赵光义等等,非常典雅、沉稳。1970年因“战备疏散” 家属返乡事,我回到汉中(解放后第二次回汉中),在北街口东北角百货商店买糖果,见卫丽芳在当售货员。足见汉中京剧界在“文革” 中所受的摧残。除了上述汉中地方上的京剧班社,外地偶来汉中唱戏的也不少,有些是有名的演员。他们带着自己的剧团或班底,演出拿手好戏,使人耳目一新。不过,他们演一个短时期就走了。这些团社中,给我印象深的有:
刘魁童的麒派戏。他完全承袭周信芳(麒麟童)的唱法,演出的也都是麒派戏的剧目如《徐策跑城》、《追韩信》、《斩经堂》、《乌龙院》、《四进士》等等。刘的长相也颇似戏画中的麒麟童:中等身材,方脸,唱念起来,声音苍劲,略带沙哑,道白铿锵短促。看过他的戏,两遍就学会:“老徐策,站城楼……” 。
刘奎官的红生戏,动人心魄。他的《白马坡》、《古城会》、《水淹七军》、《单刀赴会》、《走麦城》让人至今难忘。他把关羽的英雄义气表演得十分雄壮、英武、神圣。所唱京腔、吹腔、昆腔都很嘹亮深沉。据说,唱“老爷戏” 的,在演唱前必净身洗手,向关老爷像焚香礼拜、不近女色,否则要遭劫。刘奎官与刘魁童在汉中时间不长,都在后街汉中大戏院唱。刘奎官后来去了云南,与名伶关鷫鸘结了婚,“文革” 中去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来汉中的有贾蕙芳的剧团。贾蕙芳在川主庙街(东大街西段)路北的剧院(原是庙堂)唱戏。贾蕙芳唱花旦戏,有的戏还不错,但有的格调不高,过份花梢。像《大劈棺》、《小上坟》都表现寡妇与人调情。她演《纺棉花》干脆就穿时装(旗袍、烫发、高跟鞋),演得富有性感和挑逗性。说好听是妩媚动人,说不好听是猥亵、卖弄色情。如她唱《红鬃烈马》里的代战公主,当俘虏了薛平贵,非得招他为驸马不可时,这个代战公主竟穿着袒胸露背的紧身衣和超短裙,这时台上洋鼓洋号代替了胡琴唢呐,她嘣嚓嘣嚓跳起了大腿舞。贾蕙芳住在后街东段路南钱家“华洋大药房”的隔壁后院。白介立领我去她住处,为汉中联中教育经费向她募捐,她颇不乐意地赏给了我们几个小钱,还要了收据。整个过程,她板着面孔,始终靠在躺椅上没动。我怎么也没法把她在台上的娇艳与这时的黑黄冷脸字联系起来。
董玉苓剧团一批人,实力很强,行当齐全:生(郭少衡)、旦(董玉苓)、净(朱玉良)、丑(冯玉增)个个拔尖,配合得珠联璧合。而单个人的戏也唱得突出:董玉苓,青衣、花旦、刀马旦均能唱;郭少衡,文武老生都不错;朱玉良,铜锤、架子花脸,唱打皆精;冯玉增,文丑雅致,武丑高妙,他演《时迁偷鸡》,从三叠桌子高处,一个空筋斗翻下,落地无声。这帮人住在管子街女子师范(今小学)对面。驻地白天琴声不断。同学白介立不知怎地认识了冯玉增,我同小白去剧团玩过。可是,剧团不久就走了。
读高中时,我深受京剧影响,也学唱几句,还学会拉胡琴。晚上,有时班主任晚自习点完名,我们二三人便溜出校门去看戏。戏散后回联中,校门关了,就绕到后操场土墙下,你推我拽地翻墙回校,悄悄钻进了宿舍。逢年过节,北校(jiao )场唱戏(有一年对着固定舞台还搭了南台来唱对台戏),我们总会挤进人海去看。同学们按数字编戏目:一捧雪、二进宫、三娘教子、四进士、五台会兄、六月雪、七星庙、八大锤、九江口、十道本、十一郎大战白水滩……。我从京剧里看到了真善美、也学到历史知识和文学语言。这种传统文化影响很大。不知现今汉中的中学生还能受到京剧的陶冶否?

抗日战争时期,外来汉中的剧团,除去京剧,还有其他剧种:
话剧:有戴涯、丁尼等率领的话剧团,来汉中演出《天国春秋》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汉中》里有纪逢春的一篇文章谈得很详细。
歌剧:有朝鲜歌剧《阿里朗》,我看过,这是朝鲜抗日力量所组织的,其领导人为金九(南韩奠基人之一)。他的歌剧在汉中演得很成功。朝鲜语的歌词,观众听不懂(那时没有打字幕的做法),然而,紧张的斗争故事,优秀抒情歌曲所表现的人物心情,绝妙的灯光布景,船在水中移动等,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一时,《阿里朗》主题曲(朝鲜民歌《桔梗谣》的调子)常在学生们嘴里哼哼。这是我平生观看的第一出歌剧。剧中游击队的八卦旗(今韩国国旗)也是第一次看到。
豫剧:常香玉剧团在汉中大戏院唱过一段时间。我随父母看过她的《红娘》、《花木兰》、《蝴蝶杯》,她吐字清晰、唱腔圆润,十分动人。她在汉中大戏院唱戏,而住处却在府街中段路南“世界书局” 的后院。我上初中时,傍晚放学回府街家中,她则去戏院开始化妆,在管子街常常遇见她。当时我家就住在世界书局隔壁。书店老板的儿子是低我一级的初中同学,他上赶着跟我们玩,在北教场骑我的“铁僧帽”(王冠牌自行车),为此,常偷出许多小说借给我看,带我去他家好奇地观察常香玉室内的动静。常家总有客人,听说其中还有大官,有时听见她们曼声长歌。我读高中时,听说常香玉去宝鸡唱戏并结了婚。解放初,我就读于西北大学,在“群众堂”(今人民大厦旧址)还看过一回她的《花木兰》。抗美援朝,她捐献了一架飞机,之后,回了河南。
在汉中看戏,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因为从高小到高中这个时期,是长知识、认识外界的重要阶段;所以至今,一幕幕情景与戏剧场面,仍历历在目,十分鲜活,于是把它记下来与读者共享。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