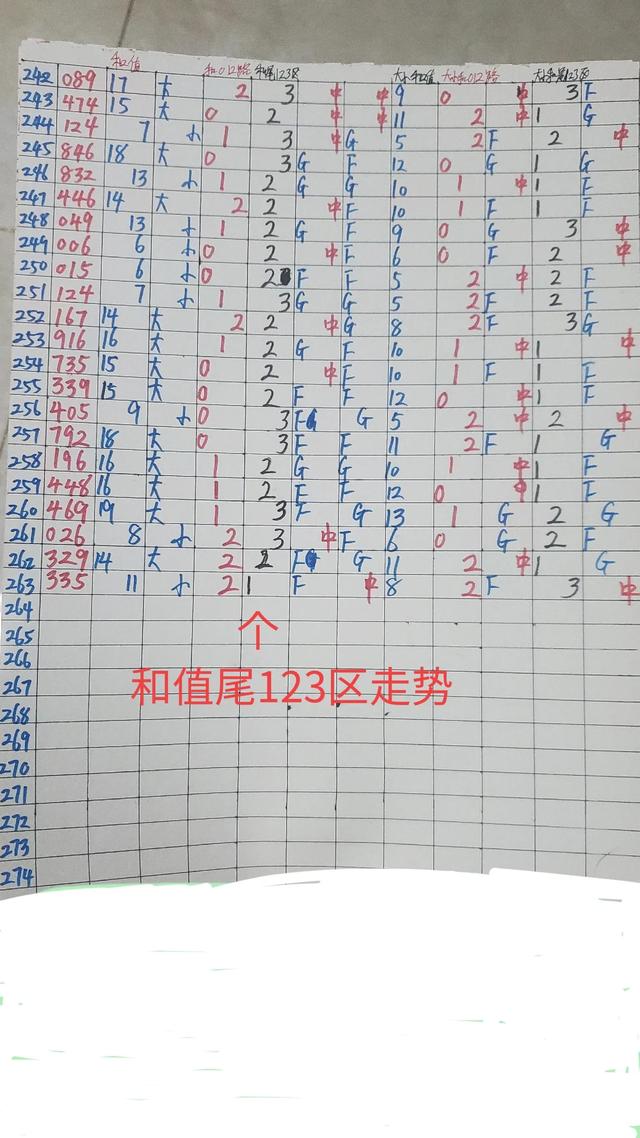作者 高鲁燕
1973年2月,我正式高中毕业了,开始了我在家待业的生活。
一个多月前,大院里的适龄孩子主要是应届毕业生都收到了当兵体检的通知,经过体检后,大部分人都如愿穿上了军装,个别的几个因身体原因落选,只好回学校继续最后一个月的高中学习和毕业考试,我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无聊、茫然的待业生活遥遥无期,不知何处是尽头。
这当然不是我期待的生活。每天按时起床,吃早饭。窗外传来一阵孩子们相邀上学的笑声,爸爸和叔叔们上班的脚步声,以及阿姨们出门自行车的铃铛声……上班上学的都走了,留下一片寂静。无聊的我开始做些简单的家务,洗碗、扫地、擦桌子、洗几件衣服、喂鸡……然后呢?爸爸每天中午下班带回的报纸,不到一小时就看完了,手边很少能看的书。最主要的,是我不愿出门,遇到的叔叔阿姨们总是送来关切和怜悯,我现在就是一个保姆或者那些暂时还没有工作的家属,不能自食其力,靠父母养活,寄生虫一样的存在。
班上的其他同学很快都在所居住的居委会挂了号,纷纷开始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可我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我不知道我的户口在哪里?18岁以前我都不知道户口簿长什么样!小时候我们的户口都在学校,集体户口。后来据说是在机关食堂,当然也是集体户口,每月到食堂领粮票、邮票、肉票、糖票等等,这些都是家长们的事儿,和我们没什么关系。现在我毕业了,去哪里找工作?我都不知道我属于哪个居委会,又怎么会知道居委会门朝哪儿开。按规定,毕业后的团组织关系要转到居委会,学校肯定是呆不了的。我把转组织关系的那张证明丢给老爸,让他去解决这个难题!
爸爸所在的单位叫福州军区国防工办,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存在。六十年代后期组建,1974年解散,头尾不足十年。我上高中那年(1971年初)才独立定居在省体工队的射击俱乐部原址上。这个单位所有的干部约50余人,战士、职工10余人,加上家属小孩,小院的常住人口也就100人左右。
我就在这远离市区、没有朋友、无人交谈的环境里孤寂地活着。
一、炊事班里的家属工
某天,我又在家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炊事班的战士小林。原来,我的组织关系被落在炊事班,现在他通知我去过组织生活。说不出什么理由不去,心中又分明非常排斥和这些兵们一起“学习”。我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前往。坐在那里听着炊事班长小董用浓重的北方某省口音结结巴巴地念了大半个小时的报纸,学习就结束了。我正想离开,只见小董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是团小组长,现在他分配我为他们这个团小组写一篇批林批孔的稿子上交。这有什么难的,我答应了就回家了。晚餐去食堂打饭时,我把稿子交给小董,只见他高兴的不得了,说是之前的学习他们总是挨批,搞得他这个班长加团小组长十分难堪,这下不会挨批了,他高兴的多打了半勺稀饭给我。(呵呵!貌似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哦。)
几天后,我的文章被抄在办公楼大堂的黑板报上,非常令我生气的是文章后的一行小字:炊事班高鲁燕。我怎么就是他们炊事班的人了?乘人不注意,我把我的名字悄悄地抹掉了。
没想到不久,我还真的被炊事班盯上了。食堂一个月至少要吃一次饺子。可食堂的师傅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福州人。兵们也有一半是南方人,包起饺子来明显人手不够。于是,几位没有工作的阿姨像金海的妈妈老孙阿姨、小香的妈妈张阿姨等就会去帮忙。再次吃饺子的时候,我也被叫去了,和老阿姨们一样成了家属工。
第一次去包饺子,班长递给我一盘肉馅,说是要包出100个饺子,我真的吃惊不小!这点馅儿,我在家最多包50个!当然了,食堂的东西是要计算成本的,我理解的开始工作。一会儿,一盘馅包完了,一数,啊!才83个。班长严肃地递过来第二盘馅,我包完后一数,85个!我挺愧疚的,想继续努力,争取扳本。班长笑着对我说,你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看着老阿姨们仍然在包着饺子,我突然明白了,我这是被人嫌弃了,我立马起身回家,还真有些因祸得福的感觉。
我以为他们从此不会再来叫我了!没想到炊事班并没有放弃我,我仍然要去参加学习,写各种学习心得和批判稿,还必须每次去包饺子。不过,我包少馅儿饺子的技术突飞猛进,几乎都能达标,最多的能包出105个饺子,真正成了炊事班的“自己人”!
二、暑期班的辅导员
要放暑假了。协理员王庚心叔叔和团支书刘正棠(一位年轻的参谋,我都不好意思叫他叔叔)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假期辅导班中学组的辅导员,还一本正经地说是团支部交给的任务。我有理由拒绝吗?
院子里的孩子都很熟悉了,平时大些的互相叫名字,小些的孩子叫我姐姐。和他们一起玩还可以,辅导员就有些可笑了。大人们都走了以后,我们大家笑成一团。之后,我又立马假装正经做严肃状,正想开口说些什么,只听一旁的爱民说:“嗯,有些像辅导员了!”哈哈哈……大家又狂笑了一阵。
真的有这么可笑么?
就这样开始当辅导员了。每天吃完早饭,到学习的地方,看他们做作业,也不知怎样辅导,闲着无事干脆就帮他们做起作业。帮小香(初二)写了一篇作文,帮金海做了三页数学题(初一),一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感觉还好,比到炊事班包饺子强。

当辅导员时和发小们登鼓山的留影
假期辅导班不光是做作业,还有许多活动。组织中学以上的孩子到鼓山、马尾等地游览,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真心地感谢负责这次活动的叔叔们,带了相机,还帮我们冲洗了照片。那个时候出游照相还是比较奢侈的事情。

当辅导员时和发小们登鼓山的留影
一年多以后,我们父亲所在的这个单位就撤销了,照片中的人都随父母迁往各地,从此杳无音信。那时我已经下乡,他们临走时也没见面告别。除跟爱民经常见面来往,和褔英见过一次外,其余的人这么多年竟一次也没有见过!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也不知他们现在都还好吗?真的有些想念啊!

当辅导员时和发小们登鼓山的留影
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爱民聪慧灵敏,小香腼腆安静,杨慧爱呵呵呵地笑,福彦、褔英兄妹淳朴勤劳,金海、志刚老实随和,陈鸥爱学习文质彬彬,小萌聪明活泼,乒乓球打得好……看来我还是有当辅导员的潜质的,大家的优点至今我如数家珍。
三、春节游园的执行人
热闹的暑假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开始了无聊的生活。做饭、养鸡、
整理家务。此时我已获准能到阅览室借书,只是阅览室除了《解放军文艺》也没有什么书好看。还好此时根据上级指示,老爸们可以购买四大名著和一些外国书籍,于是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书中。
很快,学校又放寒假了。
寒假时间很短,中间又加上过年,因此,这个假期没有辅导班。但是,团支部又给我派了一个任务。
(呵呵!团支部的任务还真不少啊!)
好像部队驻地都有这个传统,大年初一都会组织游园活动,让不能回家的干部战士聚在一起欢欢喜喜过个年。特别是这个单位即将解散,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过年了。于是,以团支部的名义,让我带领上中学的大孩子们来策划举办春节游园活动,可以报销少量经费。
大家兴高采烈地忙开了。
活动一,套圈。
买了5张白纸,(2角钱)。请机关秘书组擅长绘画的毛秘书画了几个美帝、苏修形象的漫画,然后我们找了几个旧纸箱,剪贴好,用砖头木棍固定,目标就成型了。褔英有个同学的爸爸是篾匠,住在我们的院子隔壁,请他用细竹篾编了几个竹圈儿,我们又缠上了一些彩纸,还挺像回事的。
活动二,点鞭炮。这个活动准备起来比较容易,买了一包小鞭炮(5角钱),拆开解散,再准备两根竹竿,绑上长线,末端系一节蚊香即可。
活动三、四、五、六……托乒乓球、定点投篮、吹蜡烛、猜谜语……,几乎不花钱。
最后,花了一元钱买了些水果糖(100多粒),炊事班贡献一杯黄豆,找爆米花的师傅爆出一脸盆。这两样是奖品。
1974年的大年初一上午,我们的游园会开始了。每个活动都有2到3个中学以上的孩子负责,发奖品由炊事班小董班长负责,他们个个一本正经,认真严肃。来参加活动的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小孩兴致勃勃,欢声笑语,这个春节还挺热闹。
我因此获得团支部领导口头表扬一次。
四、不想待业了
热闹过后是冷寂。
在所有的人高高兴兴过完年,又开始新的一年的忙碌时,我仍然是寂寞地、无所事事的。
我再一次开始思索。
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些小说,许多是文革后出版的,虽然充满“帮味”,但在找不到什么可以看的情况下,我还是把这些书看得津津有味,聊胜于无吧。其中有几本也印象颇深,也为我对前途的思索增加了许多推动。
《边疆晓歌》讲的是六十年代中期,一群青年人在云南橡胶园创业生活的故事。《征途》则是以上海知青金训华烈士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描述了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的生活。这一类的书看多了,让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过眼下的这种生活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想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难做到,只有一个选择是我可以自己做主的,那就是上山下乡。
旧时的同学中有许多都下乡了,我和其中几位还保持着通信,我还专门到了一个同学的下乡地点去“实地考察”了一番。结合自己13岁时到农场、上中学时到分校的体验,觉得上山下乡也没这么可怕,我应该还是可以坚持的,也可能还真的可以“大有作为”呢!
我不想待业了。与其这样碌碌无为、毫无目标的等待,不如走进广阔天地,到社会的最底层体验一下,青春年华可不能浪费了!
1974年5月4日,颇有仪式感地选择了青年节这一天,我登上了赴闽北的列车。
我的待业生活结束。
告别福州,告别家人,也告别惋惜和怜悯,我要踏上“征途”,唱一支我自己的“山区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