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中,许多老名词遇到了新问题,说着说着就变味了。譬如“干爹”、“大师”、“专家”,又比如“公知”。
为“公知”正名。“公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其含义原本是清楚的:
第一,要有学术修养和学术知识;
第二,要对公共事务积极发表意见;
第三,要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
但你看百度词条,对“公知”还有这么一段解释:
为什么“公知”会产生歧义呢?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公知”一词更是指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当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尤其在微博等网络环境中,第三方提到“公知”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是因为“伪公知”太多了,“劣币驱逐良币”,把“公知”这个名词也给污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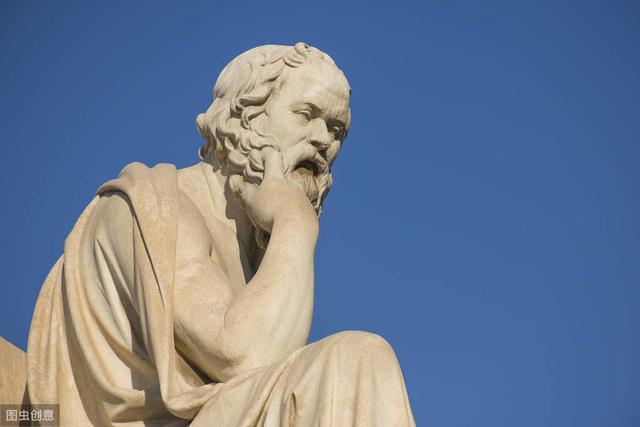
苏格拉底吸引了许多粉丝和学生,其中就有柏拉图。
如果苏格拉底他生活当今的网络时代,一定会成为超级大V。同时,他也招来很多人的讨厌与忌恨,这一点也与当代“公知”有些类似。
最终,苏格拉底被城邦公民大会以投票方式判处死刑,主要罪名是藐视宗教神灵和腐化青年。用现在的话该怎么说呢?就是“群众投票决定了一位‘公知’的生死”。
苏格拉底也真是个倔老头,他既不肯认错,也不肯以缴纳罚款来抵罪;朋友好心安排他逃走,也被他拒绝了。他选择喝下毒酒、从容就死。
与苏格拉底相比,孔子还算幸运,但他的人生也充满坎坷。
孔子生于没落贵族之家,因为父亲去世早,他不可能“拼爹”。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特别好学,常常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界。因此,孔子很快成为一个精通周礼、名声在外的学问家。

因为仕途不顺,孔子选择了开门办学。他有教无类,三千弟子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他教授学生“六艺”,并与弟子们讨论治学、修身、齐家、治国的各种问题。
大家知道,在孔子之前,中华文明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但知识只被少数贵族掌握。从孔子办学开始,这些知识才得以向社会普及。
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公知”。
与苏格拉底相比,孔子对现实政治更热心,他希望学以致用,为安顿天下做些实事。
但孔子始终不得志,不仅在鲁国难以施展,周游列国也是处处碰壁。甚至在奔走落魄之时,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狗”。
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孔子及其后继者(如孟子),在政治上都不得志。他们最大的成果还在于教书育人。
就传播知识而言,“诸子百家”中儒家最强。放眼整个“轴心时代”,也许只有印度的释迦牟尼能与孔子比肩,因为释迦牟尼也是不分种姓阶层,广受门徒,广传佛法。
与孔子相比,苏格拉底的学生不算多,但是,他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弟子——柏拉图。
柏拉图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还创办了一所延续千年的“柏拉图学园”,培养出另一位文化巨人——亚里士多德。
如此看来,东西方两大先哲——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在世时都不得志,甚至倍受现实打击,但都以“公知”的方式实现了传道的理想。
从历史的大尺度看,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影响深远的。但在思想家本人生活的年代,现实功利主义往往占据上风;而知识分子也因此产生分野。
最反感“公知”的思想学派——法家。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与墨家的学者是典型的“公知”。他们激烈辩论,相互批判,而且奔走游说,宣扬自家主张,积极参与时事政治。
道家学者不屑于做“公知”,他们追求逍遥自在,喜欢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人生。
最反感“公知”的知识分子来自于法家。
相对于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法家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当前统治者为服务对象,以“富国强兵”为实践目标。
对于儒家的仁义、道家的玄谈、墨家的“兼爱”、名家的辩论,法家学者统统看不顺眼。韩非子干脆把他们都归入“五蠹”,即扰乱君王统治的五种祸害。

法家思想的主体是统治之术,核心是“君主集权”。他们认为:法家的书只是给统治者看的,普通人绝不能看;生产用途以外的书籍都应该收缴、焚毁。
讲到这里,你很容易想到商鞅、想到秦国的严刑峻法,想到“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法家与儒家原本是针锋相对的,但在汉武帝之后,他们却如影随形两千年,被称为“儒表法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学,日益教条化,彻底丧失了批判精神。“儒表法里”,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最青睐的思想组合。
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陷于停滞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历代儒生中依然出现了一些杰出文人,譬如杨震、杜甫、苏东坡、于谦、王阳明、方孝孺等等。
他们也是当时的著名“公知”,但你看他们的命运遭际:或流亡、或流放、或被杀、或被灭族……真不如先师孔子幸运。
直到20世纪初,巨变的中国才看到“公知”再次涌现: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钱玄同……但这个争鸣时代是短暂的。

再次回望古希腊“三贤”,你不得不感叹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逻辑理性与批判精神。他们不愧为真正的“公知”。
亚里士多德尊重老师柏拉图,但对老师的观点并不全盘接受,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虽然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选择做官,而是像他的老师一样,创办了吕克昂学园。

反观孔孟之后的中国儒生,张口“圣人之言”,闭口“祖宗家法”,仿佛这些都是不可质疑、不可批判的真理。 这样的学术思想还能发展吗?还能培养出真正的“公知”吗?
历史告诉我们,“公知”未必代表正确,可贵处在于理性思辩。我们现在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会发现其中有很多谬误。但这丝毫不损于他们的伟大。
因为,求知的过程就是质疑的过程,哲学的精神也是批判的精神。
如果批判与被批判都消失了,一切都安静了,那就意味着文化“冬眠了”。
如果喊口号取代了理性思辩、谩骂取代了理性批判,苏格拉底的噩梦恐怕也就不远了。
(老铁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