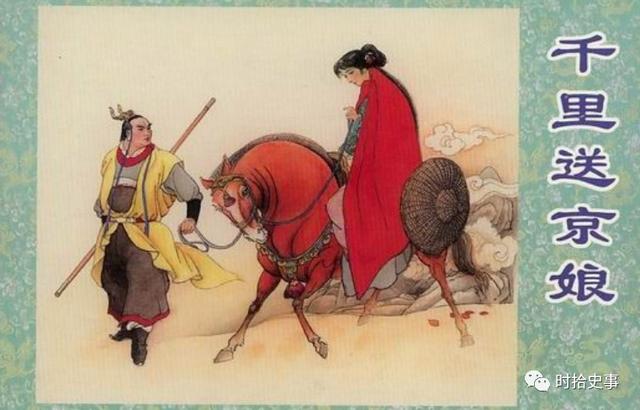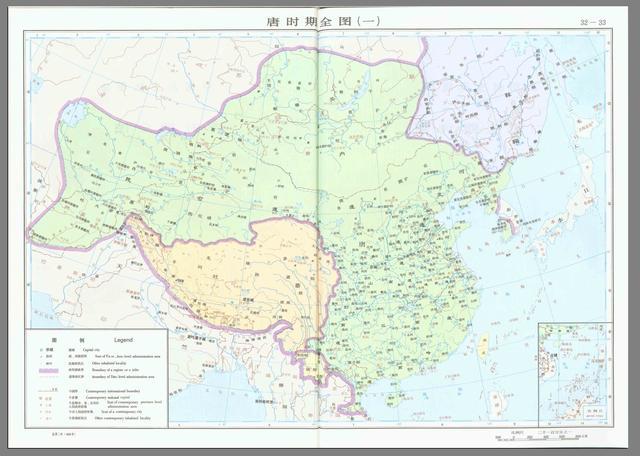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驾鹤西去,享年85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在推特上发布了史景迁辞世的消息,并称史景迁是“一位有着惊人创造力的历史学者和作家,同时还有一副热心肠。安娜·弗里曼写道:“感恩他在我初到耶鲁时让我感受到的热诚欢迎。”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6日),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历史学者,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曾任2004一2005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在西方汉学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以及《清代名人传》的作者房兆楹,并因其研究成果而得到老一辈学者如费正清等人的高度赞誉,在同辈学者当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人将其与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称为“三杰” 。

2014年史景迁访华留影 摄影:Muto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康熙》《太平天国》《胡若望的疑问》等。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观察与研究结果。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作为汉学家蜚声国际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著名历史学者、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今晨在朋友圈看到史景迁去世的消息,深感意外和遗憾。王笛向南都记者回忆,2016年左右,他刚到澳门时,还张罗着请史景迁到澳门大学去做讲座。当时安排史景迁和太太金安平同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结果因为老先生身体不好,未能成行。
王笛教授自己的治学方法和书写风格,都曾受到史景迁的影响。他多年来致力于微观历史的研究,用显微镜观察底层生活,呼吁“眼光向下”、为民众写史。史景迁早在1910年出版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是他频繁引用的学术著作。在他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微观史学可以说起源于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他评价道,史景迁总是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同时史景迁坚持一种特立独行的叙述策略,文笔活泼而富于细节,“找到一种为大众读者所喜欢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史景迁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王笛说。
以下是南都记者对王笛的专访。
他的书在许多大学里被用作教材
南都:您之前跟史景迁本人接触多吗?
王笛:接触不算多。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大约2005年左右,邀请过史景迁到我所在的得克萨斯A&M大学做讲座。当时他面向全校,讲的是后来出版的《前朝梦忆》那本书的内容。我记得我在2003-2005年担任过留美历史学会的主席。那个时候,我们学会有事情也跟他联系过几次。
但他对我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他的作品。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读他的书,一直到现在。每每报纸杂志要我向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图书,我都会推荐史景迁的书。
南都:他的作品里对您影响最深、启发最大的是哪几本?
王笛:其实我在美国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用过他的好些书作为教材。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教材就是他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那本书比一般的教科书写得活泼。一般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容易写得干巴巴,史景迁的那本书有细节,有框架,而且不仅仅是讲历史,也讲文化、文学,所以在美国的课堂上使用得非常普遍。其实我在课堂上也用过其他教材,包括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后来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但最后用起来最好的还是史景迁的这一本。
事实上,《追寻现代中国》刚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长期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不仅学历史的学生喜欢看,普罗大众也喜欢看。
另外,《王氏之死》也是我在课堂上经常用的。当年我在华东师大做紫江讲座教授,每年夏天给他们上课,用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在美国的课堂上也用过。还有《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也在课堂上用过,讲明清史的时候讲到利玛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阅读材料。《太平天国》我也用来当过教科书。
反正他的书,不仅仅是我在美国的课堂上经常用,据我所知,其他学校的其他老师也用他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写作的特点,有可读性。一般的教科书学生不爱读,读起来枯燥。史景迁的书总是能在讲历史的过程中间充满历史的细节,而且讲得生动,富于文学性。
其实我做研究也受到他的研究风格很大的影响。我记得我的《袍哥》学术论文送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外省的专家说,《袍哥》有史景迁的写作风格。其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是立意要有人物,要塑造人物,然后要有文学性,这些都应该是说受到史景迁历史写作的影响。

2014年史景迁访华留影 摄影:Muto
南都:《王氏之死》是史景迁非常看重的作品,这种对历史当中卑微的小人物关注、同情,以及通过小人物来反映社会历史图景,现在看来算不算也是一种微观史写作?
王笛:《王氏之死》英文版1910年就出版了,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还值得认真阅读。我们很少写小人物,他写《王氏之死》的时候,西方尚且没有微观历史的概念。
卡洛·金茨堡在写《奶酪与蛆虫》的时候,他也没有宣称这就是微观史。我想,“微观史”是这种风格形成以后,后来的人们给它下的定义。我认为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是微观史,但是他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一部微观史的著作。
微观史的写作主要是要靠详细、系统的档案资料,就像卡洛·金茨堡写《奶酪与蛆虫》,他要利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史景迁写《王氏之死》并没有这些资料,但他仍然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是他的眼光和研究手法独特的地方。他占有资料很少,在资料稀缺的情况下,怎样还原历史?现在好多人批评他的这本书,这是因为中国人对微观史不够了解,也不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情况。其实他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只有一个《郯城县志》,另一个《福惠全书》,王氏的故事也就是《福惠全书》里提到的一个案子。他要把它写成一本书,要加进很多背景资料,甚至使用聊斋故事。在清初的山东郯城,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遥远的乡村,这么卑微的一个农民妇女,现在我们尚且写不出来,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而且那个时候是金茨堡他们正在开始写微观史著作的时候,史景迁在同时进行。所以我认为,微观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起源于史景迁的中国历史研究。
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异曲同工,哪怕他们自己不称自己的研究为微观史。我认为微观史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是要写小人物,不是写帝王精英。第二是要有人,要以人为中心进行叙事。第三是要有历史的细节。《王氏之死》具备了这三方面。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好像比较单薄,但我们如果理解他当时写作的环境,对这本书应该是抱有非常高的敬意。我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基本上我的每本学术著作,不管是《袍哥》《街头文化》还是《茶馆》,都引用了《王氏之死》。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在西方也是一种异类
南都:史景迁的历史研究在东西方历史学界是否有很多追随者?比如您自己就是在微观史学的方面从他那里受益良多,那么其他学者的情况呢?
王笛:其实,中国历史学和史景迁的历史学的差距是蛮大的,我说的差距是指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
事实上,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放在西方也是一种异类。他的那种史学写作并非大部分历史学家会使用的。有特殊的情况,我在好几次演讲中也提到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写作的范式。这种范式就是要分析资料、数据,使得历史学成了一种科学式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干巴巴的了。它越来越远离文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而在中国,长期以来也把历史学划归为社会科学。
史景迁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以人为中心,将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他几乎每本书都是有故事的,而且都是有中心人物的。《王氏之死》写农妇王氏,《胡若望的疑问》写胡若望,《太平天国》写洪秀全,《前朝梦忆》写张岱,《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写曾静案,实际上是以曾静和雍正帝为中心人物,几乎每一本书都有人物,有故事,有细节,而且好多细节都是他自己从档案中间挖掘出来的,而非人人皆知的。这样的写作,在西方、在中国都不是主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在西方有了语言学的转向,越来越强调回归人文,开始注重文学的描述。于是这类的著作越来越多。在中国,史景迁的著作译介进来之后,受到许多读者欢迎,但是真正按照这种风格写作历史的也还是不多。但是我想,现在的年轻一代会逐渐地接受他的这种写作方式。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他的这种写作不适合学位论文,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因为学位论文有一套自己的体例要求。
对于非学位论文类的历史写作,我觉得史景迁这种风格倒是应该支持、提倡和探索的。找到一种为一般大众读者所喜欢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史景迁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南都:史景迁的著作里有很多描写和想象的成分,这种书写方式在历史写作里是允许的吗?怎么把握史料和想象的关系?
王笛:有的学者反对历史的想象,我持相反的观点。我觉得历史写作必须要有想象,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的任何论述,是根据历史的记载,还是你的推论和想象,一定要告诉读者。比如史景迁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王氏之死》里,他引用了一段《聊斋志异》的片段去描述王氏的梦境,他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这段文字的来源。他只是渲染一种气氛,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同时你知道这是来自小说里的描述。
因为历史本身的记载就是不完全的。今天我们要去重构历史,中间有很大的空白,要去填补空白,如果写历史一点想象力也没有,最后甚至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在没有历史记载的地方,历史学者得根据对已有资料的理解发挥想象力,但是你同时必须告诉读者,哪些是来自史料的记载,哪些是你合理的想象。
他总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史学观
南都:史景迁为什么持续对中国历史感兴趣?是跟他的师承有关系吗?
王笛:史景迁在耶鲁大学就是中国历史教授,他的老师芮玛丽是中国史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学术训练、研究兴趣,都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他的特长。因为一旦进入了一个研究领域,就需要这种语言的准备,那会花去很长的时间。同时,中国也有足够的魅力,无论是历史的悠久,还是可以发掘的课题,一个人一辈子都写不完,不断有新的课题展示给你,让你可以永远写下去。当然,他对中国的熟悉,对中国历史的迷恋,也是他一直研究中国的推动力。

史景迁和金安平
南都:史景迁在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和理论方面有没有独特的创建?
王笛:也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书,每一本的前面都没有理论阐述,他总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史学观,他并不试图去建立一种理论框架。但是,我认为也不能说他的史学研究没有回答理论的问题。
他的几乎所有著作都在研究晚清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他特别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写利玛窦,也特别注重中国人到了西方的经历。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1895—1980》,写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奋斗、思想和追求,这些背后都有很深的对中国历史的分析和理解。
他是通过人,通过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我认为,他的书甚至比很多用理论框架建构起来的著作更能解释中国的历史。我一直强调历史要有故事,要有细节,用理论框架来分析,理论先行,有时候会力不从心。史景迁是以历史事实来解释历史,而不是说教。你看他的《追寻现代中国》,实际上也建立了现代中国历史的框架,你要说它是理论框架,我觉得也行。所以,不能简单地看他使用了什么理论,而要看他能否回答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很多疑问,他能回答,这就是他的理论贡献。
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