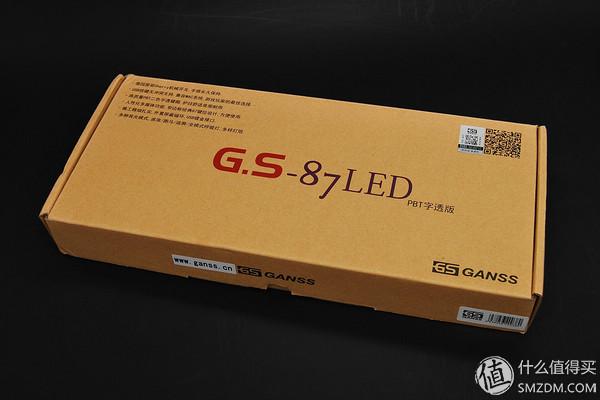“江西文旅发布”公众号自5月5日起,开设了【剧评专栏】评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至今已三个半月有余,推出了全国知名戏曲研究专家学者相关评论文章二十四篇,曾在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发表并引起热议。
江西文旅发布今日推出《一个人的长征》导演张曼君的访谈《张曼君:好风凭借力——践行戏曲舞台的现代综合》(节选),此文发表于《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7期,以飨读者,用导演的诉说来为此系列专栏作一个小结。目前,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正在角逐由中共中央倡导、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9月7日至9日,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还将代表江西省亮相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角逐“文华大奖”和“文华表演奖”,祝愿该剧旗开得胜,载誉而归。
好风凭借力——践行戏曲舞台的
现代综合(节选)
张曼君
我的经历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发展分不开,是时代造就了我。我一开始只不过是个爱唱歌的女孩,后来随着学校来到江西上犹这个小县城。那个时代需要文艺宣传,需要有歌舞天分的演员,因为我能说会唱就参加了宣传队。之后我脱颖而出,并被剧院老师发现,就被推荐到了当地赣州文工团成为了一名演员。
不过,我与大多数演员的不同,在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的专业拘束,我其实是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当时文工团里有很多大知识分子,而且是戏剧专业人士,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是他们告诉我怎么演话剧、怎么演歌剧、怎么练习声乐。可以说,我最开始接受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戏剧教育熏陶。
采茶戏是滋养我的一个土壤,但关于戏曲的一切,其实我是自学的。20世纪60年代,文工团内的艺术门类变得比较混杂,当时的我不仅要演话剧、歌剧、京剧,还要演三句半,还要跳舞,甚至还担任主持报幕员,这种“杂”又塑造了我,让我成为一名全能型演员。正是这种实践经历给予了我舞台经验,促发我来打量、观察、感受这个神奇而综合的舞台世界,或许今天我能够成为一名导演就得益于此吧。所以,在我的身上其实始终没有过多的羁绊,我也不讳言自己骨子里认同的艺术观念就是不同艺术是可以互相“串门”、跨界的。

我认可内容决定形式,但是在戏曲创作中,往往形式就是内容。戏曲是个相当依赖技术表现的艺术门类,在一定程度上,“赋形”几乎是囊括一切舞台呈现的。我的很多戏中,如:空灵舞台的设定;以几十把长凳椅子为流动支点;散文式的抒情歌舞风格;将皮影、偶杖引入戏曲舞台,人偶同台表演等等,其实都是在有了形式的想法后展现出来的,有的还是形式先于文本。比如:在创作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时,我想到了全剧的喜感和民间的活泼感可以通过木偶的憨拙和灵动来加强,用夸张装饰的形态与这部戏的喜剧气质相贴合,这样不仅不会破坏戏曲程式的指代性,也大大丰富了戏曲舞台的“赋形”效果。于是就有了骡子、有了马的偶操作,也有了星星、月亮、树木、红星的偶样态。

当然,在创作中还有个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讲故事的问题。就像前面说到的《一个人的长征》,这个作品的选材最初是冲着剧种特色和演员特点去的,所以民间性、小人物是表现的主要方向,又恰逢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背景大历史的命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几位主创交流后,提出了“以小见大”“以微见著”的风格走向。在宏大的史实底蕴里,凸显人物的“小”和民间的“细”与“喜”,幽默有喜感的人物个性主导着全剧风格,才有了鲜明的民间喜感叙事态度,才有了主人公骡子的“三句板”和“牡丹调”、邱排长这个“钢铁直男”的男高音声腔、花姑的赣南山歌、古小姐的洋腔洋调,等等。在这样的全剧风格样式下,表演也在民间的夸饰中放大了起来,这就是马和骡子的偶杖可以合理介入的动力。
其实对于新创戏曲作品来说,导演可以通过全方位的综合,将文本所传达的意味和戏曲载体本身进行恰到好处的融合,这时导演的“赋形”能力就很重要,而“赋形”需要导演以自己的发现能力、审美能力来缔造出自己心中“有意味的形式”。

程式是戏曲艺人在生活姿态基础上抽象化的提纯,而且这种提纯可以适用于各个不同的戏,它就好像模子。同时,程式的形成是与观众的互动分不开的,观众认可了,程式才能成立。现代戏想形成获得大家共同认同的模子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回到“歌舞演故事”,回到生活的源头,是我目前的一种创作方法。如《一个人的长征》,已经从完全虚拟走进了人偶幻觉虚拟,这些都是戏曲“歌舞演故事”的本体决定的。我相信,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道理。
在我看来戏曲就是一个以音乐为主体的艺术类别,因为戏曲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诗的韵律、诗的语汇,而音乐性就是抽象的诗格艺术,同时音乐又是戏曲身份的密码,是区分不同剧种特征最显著的标志。音乐在现代戏中毋庸置疑是最重要的,在充分原创的原则下,故事诗格、故事节奏、故事张力都需要音乐的统领。所以在我的剧目创作过程中,在结构剧目阶段就开始了音乐唱段的布局;之后就是不遗余力地去完成一个导演的音乐文本了,这是我最看重的过程。剧种的韵律、音乐的气韵、语言的魅力,都可以由音乐体现出来。在和作曲、音乐设计老师合作的过程中,我的音乐文本形成。它既是我排练的指南,也是让我的创作能够自如进行构思的源泉。

近年来,我的现代戏创作尤其注意这样的预先安排,从而使得形式可以带动内容,比如:为了把控舞台节奏,避免现代戏里过于生活化念白的尴尬,我基本把念白都用上了歌唱的方式,这是对歌剧宣叙调的运用,也是受戏曲韵白本身就是歌唱的特点的启发。同时,这也是可以让音乐自然进入诗格的一种状态。当然,音乐在戏曲中的作用不会仅仅靠唱段来表现,还有情感气氛音乐的推动,这常常是全剧的关键段落。比如,我的剧目里几乎都有一首贯穿始终且能够推动戏剧发展的主题歌,如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中的“大步走来喂是喂”。通过主题歌的推进、发展、变奏来串起剧情的冲突,形成戏曲所需要的诗的意蕴,有的时候它还是全剧最鼎沸的高潮。同时,音乐又是抽象的意会表达,在处理舞台时空的流转中是我最得力的“武器”,一节主题的变奏、一段乐曲、一首歌曲的传递,都赋予了我在假定性舞台中的自由。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
图片:江西图库
编辑:省文旅宣推中心(江西画报社) 王书玥
初审:邓高正、秦斯
复审:周琦、杨可
终审:宋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