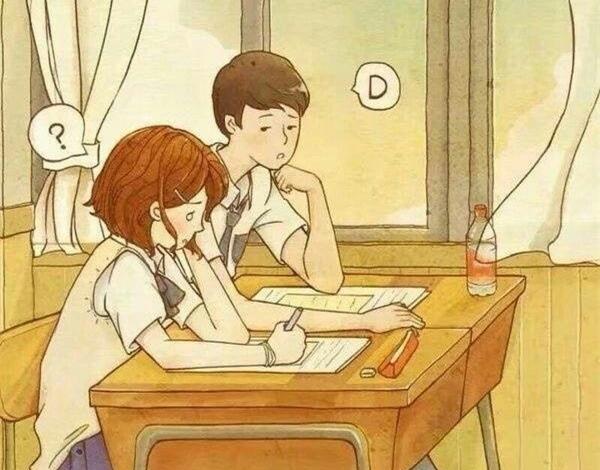本文约2904字,阅读需 10 min 左右。
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北宋政坛上掀起了一片大风浪,风浪中心的人物,名叫苏轼。这片风浪,名为“乌台诗案”。风浪打翻了苏轼的人生,也波及了许多官员。其中一位,名叫王巩,字定国。
王巩当时的官职是“秘书省正字”,他本人也是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巩与苏轼友情深厚,他们俩的交情好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在“乌台诗案”前一年,苏轼在徐州做着父母官,王巩到徐州找苏轼玩了几天,后来这事被载入《宋史》,成为文人雅士友情的典范。
《宋史》原文: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轼待之于黄楼上,谓巩日:“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然而,正因为两人如此要好,所以当苏轼被攻击时,王巩自然也被划入苏轼一派,受到攻讦。
“御史舒宣奏言:(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
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名叫舒宣的御史上奏,说苏轼与王巩交往甚密,而王巩私下里与苏轼聊起过他和宋神宗的谈话内容,泄露了国家机密等等。
罪名真假不得而知,但判罚之重有目共睹:“坐与苏轼交通,受谤讪文字不缴,又受王诜金,谪监宾州盐酒税。”
大意是,王巩与苏轼勾结,对苏轼诽谤皇帝的文字隐瞒不报,最后决定贬谪到广南滨州(今天的广西宾阳)。
从国都到广西,这在二十多位“乌台诗案”的案犯中,是被贬得最远、受责罚最重的。
这个判罚,使得苏轼很内疚,说:“兹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内疚很难过。
苏轼还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几病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

流放岭南的官员,如果最终能够“北归”,那可真是死里逃生。被贬岭南,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远离朝廷,意味着从此就没有了翻身的机会。
不但如此,岭南的生活条件艰苦,对于被贬到那里的人,要承受生理与心理双重打击。
而王巩,承受住了打击。
五年后,王巩遇赦回京,与苏轼重聚。苏轼惊讶地发现,王巩竟然不但没有落魄沧桑、意志消沉,反而面色红润、神采焕发,性格也更加乐观豁达。苏轼很是疑惑:王定国被贬到那种蛮荒之地,“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
重聚的宴会上,苏轼忍不住问了原因。王巩笑了笑,没说什么,只是喊出柔奴献唱一曲。柔奴献唱完毕,王巩告诉苏轼,在宾州多亏了柔奴的陪伴、照顾和安慰。苏轼试探询问:岭南的风土,大约是不太好的吧?柔奴淡淡地笑了笑,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这豁达的心胸,随遇而安的境界,令苏轼大为赞赏,当场填词一首,这就是千古名篇《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 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大意是:
常常羡慕这世间如玉雕琢般丰神俊朗的男子,就连上天也怜惜他,赠予他柔美聪慧的佳人相伴。人人都说美妙的歌声是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令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暑之地一变而为清凉之乡。 她从遥远的地方归来,更加容光焕发,更显年轻了,微微一笑,笑颜里好像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我试着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她却坦然答道:“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

这首词的上阙重点赞美了柔奴姑娘的美丽和美妙的歌喉。开头两句就称赞了这对伉俪,“常羡人间琢玉郎”形容王巩如玉雕琢般的俊朗形象。自古才子配佳人,像王巩这样的美男子,上天赐予美丽的女子与之相伴,这位女子就是柔奴姑娘。柔奴姑娘人美歌甜,人们都夸赞她的歌声。
苏轼没有直接描写柔奴的美貌和歌声,但请想象,在天气炎热的岭南,被贬的王巩苦闷烦躁,但柔奴一唱起歌,“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苏轼用如此夸张的手法,衬托柔奴姑娘的高超歌技。
只有美貌和歌喉,难免落下“以色侍人”的印象。然而柔奴并不是徒有其表的女子,她内心的力量温柔而坚韧。“万里归来颜愈少”,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条件贫瘠,缺衣少食的地方待了五年,归来不但没有憔悴衰老,反而更加年轻,不但如此,笑容里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香气。
梅花,自古是文人雅士歌颂的对象,它们都斗霜傲雪,品格高洁。此时的柔奴正如梅花一样,历经磨难的微笑,仍然自信、恬淡、从容,不忧不惧,安之若素。
那场劫难中,王巩是被贬最远、条件最艰苦的一位,王巩一生有六子一女,但被贬的这几年里,他失去了两个儿子,他本人也几次病重,差点客死异乡。苏轼为此自责多年,这一次重逢见面却见这两位伉俪容光焕发,心中纳闷,好奇地试探询问:岭南的生活应该不是很好吧?
柔奴姑娘淡然又平静的地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当年,王巩定案后,王巩家中的众仆人是如何人心惶惶。古代的南方,是蛮荒之地、流放之州,谈“岭南”而色变。以那时的医疗水平,南方的湿气、毒虫、沼泽瘴气,全都是致命的。如果跟随,必然凶多吉少。王巩心里也明白,因此他遣散了家中大部分仆人和歌女。
昔日门庭若市,一眨眼树倒猢狲散,让人感叹世事凉薄。
然而此时,一个柔柔弱弱的歌女不愿走,她静静地站在那里,说:“妾与同去。”
这个歌女,姓宇文,名曰柔奴,她也有着一段复杂的身世。
柔奴原本也是官家小姐,父亲是一名御医。御医和御厨,在宫廷剧中一向是背锅的高危职业。
当她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因罪入狱,然后死于狱中。父亲去世不久,母亲也撒手人寰,年幼的柔奴从此成为孤儿,无依无靠,被一个叔叔卖去了行院(行院卖艺不卖身)。
在行院,柔奴接受了琴棋书画的教育,出身良好的她一直想要离开行院。柔奴的父亲有一个好友陈太医,他一直在寻找好友女儿的下落。而柔奴为姐妹寻找医生治病时,终于被陈太医寻得。经过种种努力,她终于从行院脱身,跟随陈太医生活,学习医术。
嫁与王巩对柔奴来说一个不错的归宿,虽然王巩已有妻子,但他为人正直,品行良好,文采斐然,又是显要的高官。古代女子地位卑微,无论是歌女还是医女,被纳为妾这种小事不会出现在任何一部史书。对于王巩来说,当时的他也一定想不到,在人生最低谷时,陪他天涯海角,以温柔慰藉他的,是这个柔奴。
王巩在岭南几病欲死的时候,是柔奴为他治病、调理。善良的柔奴还为当地人看病,赢得“神医”的美称。

宾州的生活,气候潮热,毒虫瘴气,物质匮乏,加上精神压力巨大,王巩陷入了人生最低谷。是柔奴,照顾他生活起居,用歌声陪慰藉他的心灵,用医术为他治疗调理。在柔奴的陪伴慰藉下,王巩重新振作,写出了十卷《论语注》,还多次写信劝慰好友苏轼不必愧疚。他的身体越来越好,性格也越来越旷达。
而柔奴,面对故人的询问,只淡淡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含一丝幽怨,爱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诠释出岁月静好的爱情。
而苏轼自己,同样经历了牢狱、流放和贫困的生活,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听到了柔奴这句回答,大为感动,友人夫妻并没有被磨难打倒, “此心安处是吾乡”,既是对柔奴的歌颂,也是苏轼自己的人生感悟与处世之道。
本文系“文海杂览”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点赞” 的 永 远 18 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