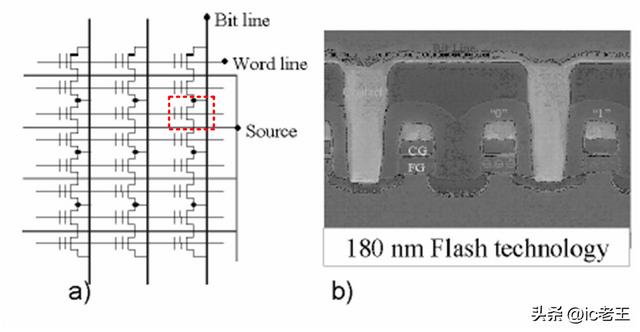《枕娇》
作者:鹊绿

简介:
首辅嫡女谭清音生得仙姿玉貌,美艳动人,只可惜实在身娇病弱,一口气吊着只差入了土。过了及笄之年,也无人上门求娶。一日,皇上下旨,赐婚谭清音与都督裴无,两人不日完婚。消息传出,京城一片哗然,众人私下皆笑,皇上这怕不是给谭氏女逆向冲喜。裴无其人,手握滔天权势,阴狠嗜杀,人人敬之畏之,世人称他为“活阎王”。众人纷纷猜测,这谭清音嫁给裴无怕是三朝回门都活不上。一朝皇权争斗,裴无扶年幼皇子登基,摄政独揽大权。所以人都认为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必会休掉病弱发妻。可谁曾想,此后一生,摄政王与王妃夫妻琴瑟和鸣,人人艳羡。【小剧场】是夜,少女眼泪汪汪地将男人摁在墙上。裴无重重一叹,闭上了眼睛,沉声,“谭清音,松开。”“我不!”谭清音扑在裴无怀中,耳畔是他一下下坚实有力的心跳声,她呢喃低声。“我不要写和离书。”“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知道啊,我喜欢裴无。”少女轻踮脚尖,芙蓉娇面眸光含泪,凑上去,唇轻轻碰吻。裴无这一生,无情无心,背负嗜杀之名,只盼着堕入魔障那天一起了结自己。万丈深渊处,少女如神明临世,向他伸出手——夫君,你有我啊。,sc,甜宠娇软怂包女主×心狠手辣男主情有独钟天作之合甜文一句话简介:枕畔娇妻立意: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精彩节选:
“进了诏狱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
“诏狱里有很多酷刑,凌迟、枭令、抽肠剥皮,还有挑筋去膝盖剁指的。”
“那吏部尚书之子就被凌迟处死了,零割碎剐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昨日都督裴大人派人将尸首送回了尚书府,据说血渍模糊,尸骨难辨……”
说罢,唐钰端起白瓷茶盏,轻抿了一口,正想继续往下说,却瞧见面前的美人面容一白,露出几分恐惧来。
“清音,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唐钰自小跟她那将军老爹在军营长大,见识过真刀实枪,说起那诏狱的血腥事,她都害怕,更何况谭清音这养着深闺里的娇人儿。
想到那些个画面,谭清音捏紧手中一方帕子,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泛上来的恶心,抿唇问道:“还、还好,阿钰,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
“我爹啊,我爹时常吓唬我,若我不听话,就将我送去诏狱。”唐钰说着,悄声凑到谭清音耳边,“那裴无有千万种杀人的残酷手段。”
裴无是当今圣上的左膀右臂,锦衣卫鹰犬出身。短短几年,便坐到了位高权重的都督之位,加之在西北藩王叛变中有保驾之功,更是深得皇上信任,除了统领京卫及外卫之兵外,锦衣卫也归他掌管。
裴无此人心机深沉,用刑手段疯狂而残忍,在朝中树敌很多,官员对他心怀不满的不在少数。
大晋官员百姓背地里称裴无是皇上养的“恶犬”,也是“活阎王”,招惹谁都别招惹他,进了他手里就是一堆尸骨。
……
谭清音在将军府待了半下午,临走前唐钰死活拉着不让她走。唐钰前阵子因与一官家公子打架,被她爹禁足了半个月,这会儿好不容易有个唠嗑解闷的,当然不肯放她走。
谭清音只得笑着安慰她,过几日去檀柘寺烧香拜佛,她去和唐将军求求情,顺带着把她也带上,唐钰听了这才放她离开。
将军府与首辅府之间隔了条街——青鱼街。
如今已是日入时分,天色将晚,家家升起炊烟,只有一些有铺面的店还开着门,道上寥寥行人。
马车轱辘轴慢慢转动,经过正要收摊的小吃摊,谭清音买了一袋蜜饯果子。
云秋眉一皱,想起上次小姐贪吃果子,半夜牙疼得一宿没睡,急切道:“小姐,夫人说不许您再吃这些糖果子了。”
“哎呀云秋,你不说我不说,娘亲怎么会知道呢。”
谭清音靠着车壁而坐,挑了一个放进嘴里,贝齿咬开蜜饯,甜腻腻的滋味瞬间在口中漾开。
夕阳余晖透过车帘,在她薄瓷一样的肌肤上镀上一层柔光,少女眉目乌灵,腮畔上的笑涡若隐若现,像是偷吃到糖的小狐狸,满眼欢喜。
谭清音不以为意,她凑到云秋身边,将糖袋子递给她:“唔,我们一起吃。”
云秋撇过脸:“小姐可别想贿赂我。”
“吃嘛。”
云秋终是没抵住那香甜气息,拿起一个放进嘴里,还不忘提醒道:“小姐可不许多食!”
没有哪个小姑娘不爱吃甜食。
谭清音正挑着自己喜欢的蜜饯,突然听见急促的马蹄声从街口方向急速驰来。
须臾间,车夫来不及勒马避让,直直撞上路边无人摊位。
马车厢内乱作一团。
谭清音的脑袋“咚”地一声撞在车壁上,疼得她眼前一阵发黑,再一看蜜饯果子撒了一马车,瞬间泪水涟涟。
云秋从地上爬起来,赶忙将小姐护在怀里,随即对车夫斥道:“车夫,你怎么驾的马车!”
车夫有苦说不出,那骑队好像没长眼睛似的,根本看不见路上行人,横冲直撞。一想到车厢里坐的是首辅千金,首辅怪罪下来,他可担不起。
可再一瞧马背上是些何人,到嘴的话硬生生停住,“小、小姐……”
风掀动车帘,马蹄声踏踏,激起一片灰尘。一群身着飞鱼服,佩戴绣春刀的锦衣卫缇骑正奔驰而来。
其中一位锦衣卫色厉内荏的吼道。
“都让开!”
“锦衣卫办事,速速避让!”
谭清音一听是锦衣卫,想到唐玉说得那些恐怖事,心头一跳,轻声对车夫说:“罢了,先回府吧。”
云秋扶着她坐起来,问着她除了头还有哪些地方疼。
谭清音咬唇,连连摇头。
她看着地上的蜜饯,闷闷道:“还没吃几个呢,真是晦气。”
“下次出来,将那摊上都买了,小姐吃个够。”云秋揉揉她的脑袋,心疼哄着说。
一回到府中,谭清音便径直回了自己的别院。
别院清幽,夕阳铺陈着水榭楼阁,屋檐檐角飞翅耸立。花廊下,少女纤腰束素,提裙快快走,衣袂飘飞。
入了闺房,她脱去绣鞋,钻进床榻里,扯过被子蒙头盖住。
谭清音咬唇缩在被子里,只觉得一股郁郁之气闷在心中无处发泄。
可转念一想,也是自己倒霉,为何非要走那条街市回家呢。
想着想着,也不知是磕了脑袋的缘故,谭清音的眼皮子开始上下打架,困意铺天盖地般压过来,于是她含含糊糊对云秋说道:“云秋,你去和娘亲说一声,晚饭我就不吃了。”
云秋站在床边,点上几盏灯烛,轻手轻脚放下帷幔。
“奴婢这就去。”
她是陪着谭清音长大的贴身丫鬟,云秋知道自家小姐这是受了委屈没处撒,自小到大,小姐受了委屈便是躲进被子里睡上一觉。
一美妇人坐在凉亭里,手中撒着鱼食,池中锦鲤争相夺食。
“小姐可回来了?”美妇人恹恹道,女儿出去半天了,夫君也不在家,她实在是无趣的很。
“回夫人,小姐已经回府了,一回来便进了自己的院子。”
林氏听后眉头紧锁,纳闷着这次怎么出去一趟回来没和她叽叽喳喳。
她放下手中鱼食,起身朝后院走去。
林氏推开房门,掀帘一迈步进去,正好与出来云秋撞上。
木檀色的帷幔从上缓缓垂下,床榻上鼓起一小团,跟只猫似的一动不动。
“这是怎么了?”林氏疑惑。
云秋将路上碰见锦衣卫的事情告诉了夫人。
林氏一听女儿撞到了脑袋,急忙吩咐去叫府医,她坐在床沿边,轻轻拍着那一小包,心疼得紧,“清音,给娘亲看看脑袋。”
见没有反应,谭夫人又轻轻掀开被子一角。
谭清音刚合上眼,昏昏沉沉要睡去,就被娘亲拍醒。她伸出白皙如玉的手臂,缩在被窝里掀开半边眼皮,娘亲担忧的面容映入眼帘。
“娘亲,我不疼了。”谭清音满头青丝松松堆至枕畔,柔声道,“我睡一觉便好了。”
林氏握住女儿一双细腻柔荑,目光落在她额头上,上下打量。见她长发略微凌乱地覆在脖颈一侧,细眉微蹙,羽睫低垂,眼皮泛着哭过的浅嫩粉色。
“那也得等大夫瞧过了再睡。”林氏检查女儿的头,一圈摸下来,没发现什么肿包,这才稍微放心。
大夫很快拎着药箱来了。
隔着床幔,谭清音把手放在脉枕上,大夫伸出手来,开始把脉。
片刻后,他放开手,转身对林氏恭敬地道:“小姐并无大碍,只是受了惊吓,心神不宁,会有些头晕恶心,老夫为小姐开几副安神的药便好。”
林氏闻言不禁松了口气,没事就好。
送走大夫后,谭夫人看着床榻上闭目熟睡的女儿,帮她掖好被角,又吩咐下人将错金香炉放上安神的檀香,这才将门带上出去。
官场上的事情她不懂,但锦衣卫的恶名她是有所耳闻的,加之夫君身在官场,还是不去招惹得好,只当是吃了哑巴亏。
月光如水,从轩窗中透入,夏日晚风习习,吹散一室浮热。
谭清音睡得很不安稳,梦里光怪陆离的什么都有,好不容易从梦中脱离出来,她口渴得不行,起身却发现云秋不在身边。
她披着外衫,趿着软鞋走到案前,端了茶水正要喝,却发现一方铜镜台里赫然映着一个男人的身影。
谭清音不禁怔住,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浸骨入髓。
男人背对着她坐在长窗之下,衣襟上洒满了清幽的月色。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那人似乎听见了谭清音下床的声音。
他平声道:“我饿了。”
夜深沉静谧,沉檀香袅。
谭清音想叫人,却发现她的声断在喉咙里,整个人像是陷进了泥潭里无法动弹。
为何她的闺房内会出现男人,像是鬼魅一般,无人知晓。
男人没有回头,“水煮肉片如何?”
在询问她。
流水一般的烟线不断从错金香炉中流淌出来,男人慢慢转过身来,脸隐藏在烟气里,一身暗色金纹玄服,手臂随意地搭着膝上,袖口挽折,腕骨裸露。
头顶笑了一声。
“那把你片了可好?”
谭清音骇然,烟气散去,那人脸逐渐清晰,没有五官,只有“裴无”二字。
谭清音惊醒,脸色苍白,罗衫浸汗。她虚撑着手肘坐起身,靠在床边,失神许久,几绺汗湿的黑发黏在白腻腮边,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谭清音胡思乱想着,她怕死,她最怕的就是死了。
她与那裴无素未谋面,也从未招惹过他,要说非要有些牵连,就是回来路上撞了办事的锦衣卫,可是那也是他们蛮横冲撞在先啊。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定是白天唐钰和她说的那些事太血腥了,才叫她做了那样的噩梦。
屋外鸟雀声声,她撩开帐子看了看日光,惊觉自己这一觉竟睡了那么久。
门没有上拴,云秋端着半铜盆热水往里间走,夫人让她叫小姐起床,今日皇后娘娘宫中设宴,邀请京中各家贵女参加。
小姐深居简出,往日京中各世家设宴,她都是借口病体沉重推辞了,可这次是宫里来的,断没有理由再不去了。
她放下盥洗的帕子,撩开垂落的床幔,径直走进去,
乌发凌乱的美人靠在檀香木床围,纤细皓腕垂在被子上,脸色苍白,眉眼间淡淡愁容,薄唇微抿,不知道在想什么。
云秋吓得不轻,她上前握住谭清音的手,冰凉又汗湿,她忙绞了帕子替她拭汗,担忧道:“小姐是做噩梦了?”
谭清音叹口气,点了点头,细指捏着潮潮的里衫对云秋说:“云秋,我想沐浴更衣。”
被汗浸湿的罗衫贴着身上有些发凉,更是黏腻的难受。
云秋道:“奴婢这就去备水,您盖着点薄被,别又着凉了。”
氤氲水汽,沐浴过后,谭清音长舒一口气,眉眼笑意浅浅,也暂时忘却了噩梦。
云秋从熏笼上取下叠得整齐轻软的衣裳,伺候谭清音换衣。
谭清音披着青丝坐在梳妆台前,抬手撑着脑袋,楚楚可怜地看向云秋:“不去不可以吗?”
那些个宴会她委实不想去,年前武昌侯夫人过寿,她跟着母亲一起去祝贺。席间,那些贵夫人打量着各家公子千金,话里话外有结亲之意,也包括她。她浑身不自在,活像被剥光了衣服站在那儿任人评头论足。
谭清音本就生得好看,巴掌大的小脸吹弹可破,因着刚沐浴后热意,凝脂般的肌肤透着嫣红。她抬脸看人时,目光盈盈如春水将生,像是要把人溺进去,美得不可方物。
云秋看得失神,差点说可以,幸好及时勒住,“不可以,夫人说这是宫里的,推脱不了。”
谭清音听后脑袋一耷,蹙着细眉。
她不想去,不过她大概也能猜到这宫宴去是干什么的。
云秋垂首替她挽着发髻,拿出梳妆盒里的白铅粉,安慰道:“小姐也别担心,奴婢有法子。”
谭清音疑惑回望,有些不解。
云秋蘸取些白铅粉,轻轻敷在谭清音脸颊上,遮住红润,又蘸了些涂在润泽的红唇,刚刚还明艳灵俏的少女瞬间病弱憔悴。
“小姐装着生病,应该能省去不少麻烦。”云秋说着,转念一想,“再说了,小姐不是一直‘病体欠恙’,旁人是知道的。”
谭清音愕了一下,眼波流转,“是啊,我本来就是个‘病秧子’。”
自她幼时落水,捡回一条命后,父亲就对外宣称她落了病疾,这些年鲜少出门。
这也是为何她到了及笄之年,上门求亲的人很少,谁家也不想娶个病秧子回家,哪怕她是首辅千金。
不过她不在乎这些,平日里她养尊处优惯了,只想懒散过一辈子,况且父亲母亲也允许她自己择婿。
听音苑小池花圃,林木葱葱,花架下蔓藤缠绕,有鸟儿在枝间扑翅欢叫,女儿家的小玩意挂在木檐下叮咚作响,处处透着精致。
谭清音立在院中,发饰轻便简单,青丝垂肩,一袭水雾白烟罗裙,衬得腰如约素,越发显得她整个人弱质纤纤。
云秋又给她披上一件银线雪色披帛,两人这才款款向正厅走去。
首辅府,正厅。
林氏有些坐立不安,她揪着手中的帕子,担心的望向坐于主位闭目养神的男人。
“夫君,我这眼皮一直跳,我担心清音……”
话还未说完,就被男人皱眉打断:“你别多想。”
说话的正是谭清音的父亲,首辅谭方颂。
话是这么说,可他也是在正厅等候多时,今日女儿一人进宫,他还是要叮嘱些。
太子年逾弱冠,资禀聪明,尚未有正室。此次皇后娘娘大设赏花宴,只邀请京中各世家重臣贵女前去,此举不言而喻。
他如今刚过不惑之年,在朝中内阁位列首辅,同僚中想与他家结亲的不在少数,可他都婉言谢绝了。
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小娇生惯养着,一点苦吃不得,也只想她自己寻个称心的郎君顺顺遂遂、无病无灾过一辈子。
谭清音撩帘而入,见父亲母亲在厅中伫立等候,她不禁弯起了眼睛,“爹爹,娘亲。”
“清音,你来。”谭方颂向女儿招手。
谭清音心里一紧,料想爹爹是要和自己说什么,莲步轻挪,走到父亲身边。
“怎么脸色这般苍白?”谭方颂的目光在她脸上略一停顿,眉头皱起。
谭清音立马摆手,解释道:“这是画的。”
林氏一扫忧容,她替谭清音整了整衣襟,又伸手捏捏她的耳垂,似是责怪:“鬼机灵。”
“清音,进宫后切勿多言,别沾酒。”谭方颂说,“宫里人多眼杂,旁人说的也莫要听信。”
“唐将军的女儿与你一同前行,也正好有个照应。”
谭清音望了一眼父亲,她点点头,应道:“爹爹,我知晓了。”
就在此时,门口的小厮高喊:“老爷,将军府的马车已经到了。”
谭清音不敢耽搁,只得和爹娘拜别,随了云秋及小厮一同而去。
谭府外车来人往,络绎不绝,一片喧嚣。
一辆精巧的马车停在谭府石狮前,车身彩绘雕漆,车帘被挑开,唐钰探出半个脑袋,看见小姐妹,眼底尽是欢喜笑意。
一袭罗裙的女子从府门里行出,袅袅娜娜,身形羸弱,一如误入人间的仙子,我见犹怜。唐钰想,应该把清音带到她爹的军营中,练上个日子,就不至于看着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倒。
“清音,快来。”
谭清音循声抬头,眼底骤然浮现欣喜,颊畔泛起很浅的酒窝,她扶着云秋的手坐上马车。
马车内装饰精致,四角挂着熏香笼,有两个卧榻,皆以锦缎铺垫,中间檀木小圆几,上面放着桂花糖蒸栗粉糕,车厢内足以坐下五六个人。
谭清音轻拢裙摆,坐了下去,接过唐钰递来的粉糕,打趣道:“今儿个唐将军怎么让你出来了。”
“哼。”唐钰轻嘁一声,“今日皇后娘娘宴请京中贵女,我爹再不让我出来就是抗旨不遵。”
说起这个,唐钰忽低声说道:“清音,你知道皇后娘娘为何突然设宴吗?”
谭清音将那糕点咽下去,又喝了口茶水,这才小声道:“选太子妃?”
“嗯,我爹也是那么说的。”
唐钰皱了皱眉,有些欲言又止。她不小心听到她爹和娘的谈话,今日设宴也就是先过个脸,看看各世家贵女的才学品行,皇后娘娘似乎更有意向谭首辅和周国公两家。
唐钰憋不住话,“清音,你可想当——”
谭清音惊呼,她一把捂住唐钰的嘴,慌言:“你可别说这话,让旁人听到指不定说成什么样。”
唐钰想了想,确实自己没把住嘴,幸好这车厢里只有她们二人。
沉默片刻,谭清音侧过脸,缓缓说道:“阿钰,其实我有心慕的人了。”
“谁?”
对上唐钰含笑探究的目光,谭清音的面上开始忍不住发烫起来。
唐钰第一反应是不敢置信,她与谭清音从小一起长大,最清楚不过,可是也从未见过她与哪个郎君挨得近过。
忽地,唐钰脑海里闪过,她不确定道:“幼时你落水,那个救你的少年郎?”
少女低着头,不说话,耳尖和面颊却一点点红了起来。
谭清音七岁那年,那时正是上元节花灯夜,河水冰冷刺骨,她不慎落水幸被一少年救起,可事后这少年像是消失了般,任谭家怎么寻也寻不到。
唐钰斟酌一下,“可……清音,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了,或许他早已成家了呢。”
其实也有这样想过,当唐钰说出来时,谭清音脸色还是微微白了下。
谭清音忽地情绪低落,低声:“是啊。”
或许娃娃都会走路了吧。
她不知道他的样貌、家室,只记得那时自己浑身冰冷,缩在他怀里瑟瑟发抖,昏昏沉沉间只看见他锁骨位置上的一颗小痣。可仅凭着一颗痣寻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
道道巍峨高墙四四方方的围着宫城,殿宇庄严宏伟,抬头便是明黄飞檐挑起的瓦蓝天空。
赏花宴地点设在御花园一处临水馆阁楼亭里,风渐起,纱幔重重叠叠,乐声琤琮,妙曲轻度。
皇后娘娘还未到场,只差了几位太监宫女在此。
楼阁里聚了许多盛装丽服的世家小姐,三五一群地低声浅语,真是人比花娇,一时热闹纷纷。
烈日骄阳下,谭清音擦了白铅粉的面容更显得苍白,她蹙着细眉,再是绢帕掩唇轻咳几声,一副已是半只脚进了棺材的模样。
唐钰自然是知道她身体什么情况,她憋住笑,还装样拍了拍谭清音的背。
谭清音一个嗔怪的眼刀飞过去。
角落里端坐的贵女们纷纷相看一眼,有蹙眉担忧的,也有压低了声音唏嘘——
“真是一次比一次病得厉害,也不知下次还能不能见着她了。”
“你也真是有胆子说,说实话,若不是她谭清音这些年病恹恹的,如今该是何等风光。”
有人附和,“是啊,不然这名满京城的美人也轮不到那个周云嫃啊。”
幼时,谭清音的容貌才学便是冠绝京城,又是首辅的掌上明珠,人人艳羡。哪成想天妒美人,一次落水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便深居闺阁再未露面。
直到半年前,首辅夫人携着这位出现在武昌候夫人寿宴上,众人惊叹,这首辅千金这些年生得是越发美了,即使一副病体恹恹模样,也难掩倾城之姿。
如此姿容,就连那京城第一美人——国公府嫡女周云嫃也难免逊色了几分。也正是如此,这半年京城上下隐隐有让她周云嫃让位的奚落声。
周云嫃被众人围在当中,她听见这边动静,目光落在谭清音身上细细打量,她面上不显,内心却是一阵冷笑。
不过是一个随时都能入土的病秧子罢了。
谭清音自是注意到了周云嫃的目光,她懒得理会。
暑热的天气,鼻尖已有薄汗沁出,谭清音擦了擦,内心只盼着日头小些,别叫人看出了端倪。
不知为何,她总觉得背后有难捱的目光在审视着她们,让她坐立不安,浑身不自在。
西南角处三重楼阁的宫殿上,一明黄身影立于高位睥睨着亭中众女子。
他身后站着一金缕袈裟的和尚,一玄色织金锦衣的青年。
晋帝神色淡淡:“这其中可有合适人选?”
国师道:“回皇上,依微臣看,周国公府的嫡女品行端庄,美如珠玉,确实是太子妃的不二人选。”
“那,谭首辅的女儿呢?”
“这首辅大人的女儿虽仙姿玉貌,但周身病气缠绕,微臣昨夜掐算卜卦,若是为太子妃,恐……”国师支支吾吾,显然不敢细说。
晋帝双目盯着国师,不怒自威,示意他继续说。
“恐有损皇室命格。”
晋帝闻言脸色大变,他本就子嗣绵薄,这些年修道服丹,以求万寿无疆来绵延大晋皇室气脉。
晋帝眼神闪烁了下,他侧身看向身旁年轻男子,迫切地问道:“裴卿如何看?”
他很信任裴无。
男人的眼睛宛若深渊,不带一丝情感,他只是安静的站在那里,却让人无法忽视他身上肃杀阴沉之气。
裴无薄唇微抿,平静的道:“臣认为,国师所言甚是。”
晋帝长出一口气,抬抬手吩咐太监:“那就立刻拟旨,去告诉皇后,此事已定。”
说罢,便拂袖摆驾回宫。
太监尊声道诺,应声而去。
等到了中午时,坤宁宫突然来了人,是皇后身边的宫女。
说是皇后娘娘凤体不适,今日赏花宴取消,来者皆有赏赐,随后将檀木托盘里珠宝饰物分给了各家小姐。
众人行礼道了声谢皇后娘娘赏赐后离开了皇宫,各回各府。
檀柘寺。
夏日炎炎的三伏天,骄阳似火,小和尚在庭阶前洒了水,水顺着坑洼缝隙流入或流出,裂缝里的青苔沾了水,显得格外绿。
与外头的炎热不同,禅房里则清凉舒适。
佛香飘缈,一慈眉善目的老和尚双眼微闭,左手伸掌,右手敲着木鱼,木鱼声与诵经声交织,声声入耳。
时间过了太久,谭清音有些坐不住,睁着杏眼左右瞧瞧,见娘亲正闭目凝神听着佛经,她有些羞愧,又坐直了身体。
还是没坚持太久,谭清音的脑袋又垂了下来,她很是苦恼,娘亲说了带着她来寺中祈福求求姻缘,怎么倒是听起了佛经。
谭清音捏了捏自己的手,怔怔地瞧着诵经的方丈,他眼眸低垂,嘴唇轻轻翕动,花白的胡子随着气息上下颤动。
笃笃木鱼声停止,空尘方丈放下手中经书,谭清音倏地回神,对上方丈大师了然一笑的目光,被人抓了包的谭清音脸微红,羞地低头抠着蒲团边边。
空尘方丈从蒲团上起身,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有劳林施主久等了。”
林氏却觉得没什么,她站起身,恭敬道:“哪里,是我们打搅方丈了。”
空尘方丈笑着看了看垂着头站在一边的谭清音,问道:“小施主近来身体可好?”
谭清音乖巧颔首,“谢谢方丈关心,清音身体好着呢。”
空尘方丈早年云游四方,行医救人,后便隐居檀柘寺,一心参悟佛经。自落水后,谭清音身体常年畏寒,哪怕是酷暑时日,手脚也如冰冻,这些年也幸得空尘方丈药方调理。
林氏微笑道:“方丈,此次前来,也是想给小女求个姻缘签,心里好求个安稳。”
“世间姻缘,皆有因果。”空尘方丈面上依旧是慈祥的笑容,“林施主且放心,小施主不会卷入尘世纷争中,日后会是齐福之人。”
“多谢方丈解惑。”
不管信与否,林氏至少现在安下心来。她虽然是个后宅妇人,但对朝堂之事也有所耳闻。如今圣上身体日渐衰退,几个皇子结党相争,她并不愿自己的女儿卷入这些。
临走时,空尘大师叫住谭清音,给了她句“万事随缘,得大自在”。
檀柘寺规模不小,依山而建,周围古木参天,绿树掩映,倒是十分幽静。
林氏去前头交些香火钱,交代了几句,谭清音便独自在院中回廊上闲逛着。
“万事随缘,得大自在,万事随缘……”谭清音拧着眉,垂着眼睑,口中低喃。
“我还是不懂啊……”
寺庙后院曲廊蜿蜒,殿宇相接。错落阴影光后,少女长裙曳地,背影清渺秀澈,抬手懊恼地拍着自己的额头,秀发贴着她的面颊,时而拂过她红润的唇瓣。
谭清音自顾着念叨空尘方丈的话,浑然忘了前方是回廊转角,不及多看两眼,“嘭”的一声,脸直直撞上来人胸膛。
胸膛坚硬,像是一堵铜墙,她只觉得眼前一花,鼻尖酸痛。
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横在她纤腰间,扶着她稳稳站住。
谭清音吃痛,惊呼出声,白嫩嫩的脸蛋皱成一团。
裴无步子一停,温香软玉的身子贴撞过来,萦绕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清甜香气。
然裴无最厌这种女子,任她无意亦或是又有意。
裴无浑身戾气毕露,面上依旧是清冷的,没什么表情,他抬手就要掐住怀中女子白皙的脖颈。
待看清女子眉眼,裴无目光微凝,抬起的手掌转而扣住少女手臂后撤两步。
压着的气息远去了,谭清音揉着鼻子与他拉开些距离,男人身量很高,她略略抬起头,恰好撞入男人的眼睛。
这人站在融融的太阳底下,清绝坚毅的面容镀上一层柔和的光,可谭清音周身却升起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在他低头的刹那,她分明看见了他眼底即逝的肃杀。
院子里一时安静下来,长廊院落都空荡荡的,连个小沙弥也见不着,只有风时不时吹过枝叶,沙沙的响。
谭清音眸光微动,戒备地看了一眼男人,垂眸低低说道:“抱、抱歉,方才是我走路没看清,冲撞了公子。”
少女低着头,盘领里隐约露出一小段雪白的脖颈,一颗朱砂痣点缀其中,如雪中红梅,有些晃人的眼。小巧的白玉耳坠轻轻摇着,一如主人小心翼翼的畏惧。
裴无淡淡地看了一眼,回了句:“无妨。”
说罢,他拂袖自她身侧走过,离开。
听到这人沉沉离开的脚步声,谭清音心口蓦地一松,徐徐吐出一口气。
她悄悄回头,瞧了一眼男人阴鹜冷漠的背影,内心默默流泪,前日撞了头,今日撞了鼻子,她果然还是该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她踢了踢脚边石子,心想道,罢了,今日来寺中她还有正事要办。
在檀柘寺的大殿里,中间供奉着佛菩萨像,谭清音跪在蒲团之上,双手合十,虔诚的膜拜,口中念念有词。
“佛祖在上,信女清音,先前方丈诵佛经,是信女心不诚走了神,还望佛祖与方丈莫计较。”
“信女还有一个小小请求,望佛祖保佑,有生之年能见上恩人一面。若他无婚配,我亦未嫁人,定以身相许;若他已有婚配,也绝不纠缠。”
“望佛祖成全。”
———
禅室岑寂。
空尘方丈坐于案前书写经文,察觉到身旁人时,他眉眼沉静,神情淡然道:“今日怎么想起来老衲这庙中了?”
“前些日子得了些经书孤本,放在我那占地方。”
裴无端然立在案前,他身姿英挺,面庞清隽俊逸,穿着玄色的交领直身,越发衬得宽肩窄腰,浑身散发着杀伐的寒意。与这普度众生的佛门格格不入。
“该是你留着自己翻阅。”
裴无漆黑的眸子落在几案的佛经上,定定看了少顷,也不知是自嘲还是其他,他轻轻一笑,眼底却还是覆着淡漠的冷,“我已经走到了今天,断没有、也不会有回头的路。”
“裴无。”空尘方丈摇头,“老衲从未叫你放下,只是最后切莫入了魔障。”
裴无沉默下来,沉香氤氲缭绕出来,他的一双眼藏在后面,让人看不清。
他无情无心,背负嗜杀之名,就算入了魔障又如何,难道要他怜悯这世人吗?
空尘方丈许久未闻话声,他笑了笑,搁下手中笔抬头看着裴无,忽地没由来问道:“你可是有喜欢的姑娘了?”
裴无抬眸,瞥他一眼,空尘看着他,眼底意味深长。
“没有。”裴无也不想与他多言,他语气冷冽,“你好好参你的佛经。”
“我先回了。”
空尘方丈但笑不语。
……
檀柘寺大门前,祁明抱臂靠在马车边,看见裴无他直起身抱拳道:“大人。”
裴无颔首。
祁明抬头,眼尖瞥见大人胸膛衣襟前沾着一块红色痕迹,不像是血迹,倒像是……倒像是女子的口脂。
祁明瞪大了眼睛,他飞快看一眼大人,见大人面如沉水,衣衫整齐,心里暗骂自己多想了。
大人向来不近女色,就连皇上赏的美人都不瞧一眼,再说这寺中哪来的女人。
裴无脚步停了停,侧头看了他一眼,见他神色里带着惊讶,问:“何事?”
祁明不知该不该说,最后横下心来。
“大人,您衣襟上沾着东西。”
裴无循他所指,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瞬间脸色阴沉,一抹嫣色赫然在上。
是方才她撞上去的。
裴无抬手拭去,却发现徒劳,指腹还蹭上了口脂香,他沉声:“回府。”
祁明抱拳:“是。”
这厢,谭清音母女俩拜完佛后便回府了,马车慢悠悠停在谭府前。
谭清音下了马车,她挽着林氏手臂撒娇,“娘亲,你让爹爹再派些人去找找,说不定就找着了呢。”
“你爹找了这么些年了,毫无音讯。”林氏叹了口气,“要么就是他根本不想被咱们找到。”
那少年当初救了她家清音,往后就销声匿迹了般,再找不着。
谭清音听了神色哀伤,难道她这辈子真的见不到了吗?
母女俩进了府,林氏轻拍女儿手安慰,若是有缘定是能相见的,无缘也强求不得。
前厅里云秋等得焦急,今日夫人小姐早早出府烧香拜佛,这会儿府里乱一团。见到夫人小姐身影,她飞快上前。
“夫人,小姐,不好了!”
“宫里来了圣旨,皇上给小姐和都督赐了婚——”
“谁?”林氏怔在原地,拔高声音打断云秋。
“都督裴无大人。”
空气仿佛凝固。
谭清音脑袋轰的一声,她狠狠愣住,滞在那儿,鸦羽轻颤的眼眸里闪过震惊、惶恐。
过了许久,她钝钝扭过脸,无措地看向林氏,“娘亲……”
林氏也是心慌神乱,握着女儿的手,指尖发白,“清音别怕啊,娘去找你爹问问清楚。”
说罢,林氏眉头紧锁,立刻转身往书房去,脚步声急促。
怎么就突然赐婚了呢,昨日明明已经赐旨周国公府的嫡女为太子妃了,为何今日又赐婚了自家女儿,还是和那恶名在外的都督裴无。
书房一角,长案上堆满书文案卷,一卷明黄置于上。谭方颂枯坐在书桌前,闭着目,眉头一片凝色,身上还穿着尚未脱下的官服。
书房门被推开,阳光照进来,他微微眯了眯眼。适应了这份光亮,他看见站着门前一脸焦容的妻子。
林氏注意到案上的圣旨,心下一凉,她上前打开,低眉看着手中明黄绢帛,颤颤问道:“夫君,这能退婚吗?”
谭方颂摇了摇头,圣旨既下,君无戏言。
礼部择了成亲吉日,下月十九便要完姻事。
圣旨是退朝时下来的,皇帝派总管太监到府中传达赐婚圣旨。妻女外出烧香不在府中,只得由他接旨,谭方颂接旨的时候还是懵的。
要知道在朝中,他与裴无素来无交集也无过节,说实话,他还有些佩服裴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作为。可裴无这人为人处世手段实在狠辣,暗处树敌很多,谁家舍得把女儿嫁过去,这无疑是入了狼口。
所说裴无如今圣眷正浓,可难保有一天,暗敌群起而攻之,到时候必会遭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