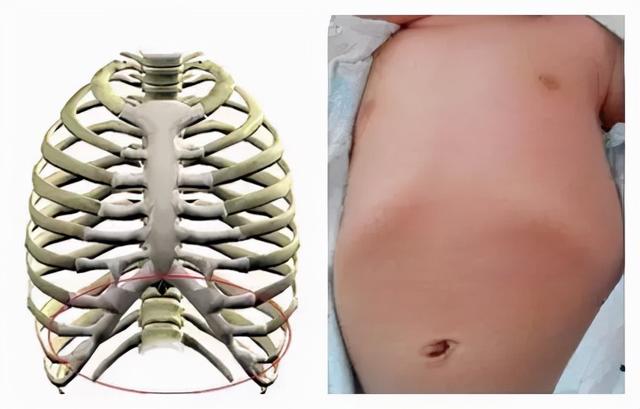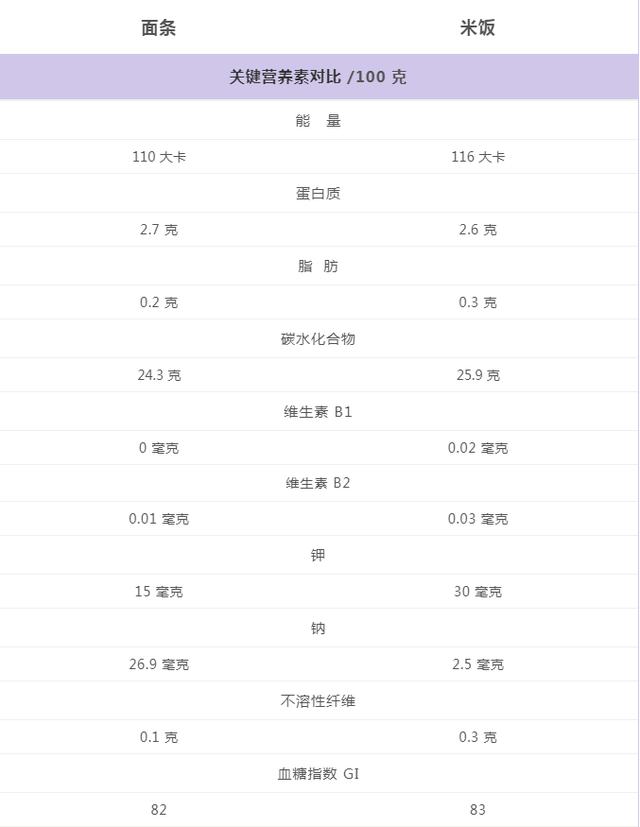公元988年,古格王拉喇嘛·益希沃全力弘法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开创了一个时代。
这个被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时代,绵延至今,影响力巨大。
这个时间节点上,藏传佛教还没有产生教派,无论是益西沃,还是大译师仁钦桑波,都没有教派之别的概念。
他们在引进翻译印度经典时,对印度各教派经典也一视同仁,精益求精的加以翻译。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以益西沃和仁钦桑波为代表的西藏历代高僧,都可算做人类文化卓越的保护者。
当阿底峡尊者从印度入藏,辗转到达桑耶寺时,发现桑耶寺内保存了大量印度梵文写本,其中很多是前弘期高僧从印度带回。
这些写在贝叶之上的典籍,这就是传说中的贝叶经。
尊者随便抽一卷,赫然发现是在印度早已失传的古卷,他马上整理衣冠,凛然叩拜,向这些保护文明的先贤们献上崇高的敬意。

经典本身就是被记录下来的个人领悟,当这些个人领悟被历代高僧学习后,又不出意外的,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理解。
随着传承的延续,这些不同的理解,又被一代代弟子不断固化。
随即,不同的参悟孕育出了不同的教派,甚至在大教派中,又细分出不同的支派。
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本不存在所谓好坏之分。
但宗教是种神奇的思想领域,能极大的改变信徒的生活方式。
它既能将众多身份迥异的人,迅速凝聚成一个整体,为同一个目标披荆斩棘。也能让各派间的信徒相互敌视,再加上狂热的原教旨思想作祟,在同一信仰体系中的各教派,常常是仇深似海,必欲除之而后快,比如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和逊尼派。
约于11世纪中叶,自然环境更优越、人口更多、经济也更发达的卫藏地区(前后藏),出现了教派分立的局面。
短短不到五十年,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二十多个教派,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其中,宁玛派(红教)、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和噶当派(后并入格鲁派)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发展壮大。
其余的教派,则因为没有政治势力做靠山,大多融于其他教派或被迫改宗,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卫藏地区的教派同时涌现,绝不是巧合,除了思想体系的百花齐放外,还隐藏着深厚的社会背景。
在经过了“一鸟凌空,众鸟飞从”的属民暴动后,旧的社会结构体系被彻底打碎,吐蕃王朝构建的垂直管理体系烟消云散。
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各种以领主、贵族为首的势力,形成了无数的小割据集团。
这一时期,有机会出国留学的僧人非富即贵,要么自己家有钱,要么是有钱人资助。
要知道,古代西藏学佛是要交学费的,而且交的是黄金,这可不是一般人家能够弄到的宝贝。
据统计,仅由藏赴印留学的150余名僧人,带走的黄金数量就达到了11万余两之多。
从花费的数量上看,出国留学的僧人可真不是去镀金的,个个都是足金,还都得是千足金。
昂贵的学费用成了一道高门槛,将贫寒人家的孩子,干净利索的挡在了门外。而学成归国的僧人们,很快就成了各大寺院的寺主。
成了寺主的僧人,也要为其背后的势力负责,毕竟没有这些势力的支持,也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尤其,生逢乱世本就命如草芥,再不服管教、乱说乱动,指不定哪天就人间蒸发了。
于是,在各势力范围内部,形成相对封闭的朋友圈,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格在经过益西沃和仁钦桑波的辉煌后,佛学发展变得滞缓,虽信众如云,但高端人才却出现了断层,再未涌现大师级人物。
反观卫藏却是高僧林立、教法鼎盛,强弱易势之下,卫藏佛教思想开始向阿里回流。
最早在阿里布局的是噶举派,准确的说是噶举派的一个著名分支止贡噶举派。
说起来噶举派和阿里也算颇有渊源,噶举初祖之一玛尔巴译师最著名的弟子米拉日巴尊者(1040~1123年)就是阿里芒域贡塘(吉隆县)人。
他修行得道后,在阿里广传佛法,现在阿里的神山圣湖间,还流传着很多他的传说。

米拉日巴尊者
不过,在玛尔巴和米拉日巴时代,噶举派教权比较松散,未形成教派集团,也没有和阿里诸国王发生过多少联系。
11世纪中叶,噶举派松散的口传心授、在家修行方式,已不能适应残酷的教派斗争。
1179年止贡巴·仁钦贝(1143-1217年)在止贡地方(今墨竹工卡县门巴乡)创建了著名的止贡梯寺,止贡梯寺也成了止贡噶举派的祖庭①。
止贡梯寺建立后,迅速成为教史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止贡巴·仁钦贝是位心思缜密、目光宏远的高僧,为了能让自己的教派受益,他甚至有些不择手段。
《止贡法嗣》曾记载,止贡梯寺建成后,大量信众慕名而来。这下止贡梯寺就有点揭不开锅了,为扭转被动的局面,仁钦贝联合达垅塘巴一起为丹萨替寺修建大殿。
可大殿建成后,他声称建筑结构不安全,可能要倒。便以保护寺产为借口,将大量的经书和财物运回了止贡梯寺。
在盛世,也许这种做法会令人不齿,但乱世之中,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枭雄人物。
止贡派在仁钦贝带领下,短时间内便在卫藏风生水起。到他晚年,止贡信众已达到了令人瞠目的十三万人之多。
枭雄的目光永远注视着远方,卫藏虽富庶繁华,但教派众多竞争激烈。
仁钦贝心中一直放不下遥远的阿里,阿里虽环境恶劣人口较少,但信仰基础很好,更重要的是其他教派涉足不多,是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
关注阿里的高僧并不止仁钦贝一人,老师(帕木竹巴)便拉着他和师弟的手反复叮嘱,交代一定要派修行者去冈仁波齐脚下修炼,并说这是祖师授记过的圣地,在此建寺修行,能得到祖师的护佑。
以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为标记的神山圣湖区,历来都弥漫着神秘的色彩,尤其是冈仁波齐刚猛无匹的气势,天然形成“卍”字型纹路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积雪,使其成为了教徒心中的圣地和世界的中心。本教、印度教、藏传佛教、尼泊尔耆那教,都认为冈仁波齐代表着无上的尊荣与幸福,在噶举派眼中冈仁波齐,更是祖师米拉日巴斗法击败过苯教大师的圣地。

为完成老师临终托付的心愿,也是为了将止贡派的势力拓展到阿里地区,仁钦贝在止贡梯寺走上正轨之后,亲率门徒二十四人,来到了冈仁波齐脚下。
从拉萨东面的墨竹工卡走到冈仁波齐的漫漫旅程,有着无数的艰难险阻。考虑到当时仁钦贝已年过四十,这段为了信仰的远征,也真是够豁得出去的。
这次朝圣之旅,据说获得了极大成功,《青史》中记载,神山的守护之神都为之发下了神谕。
但守护神(哀嘎窝)开口说话,也并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神肯定不会带着现金造访,仁钦贝还是不得不从神山脚下退了回来。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得到了当地领袖的接待或者在此建寺。
不过,坚韧不拔、百折不回是枭雄必备的品质之一。
这次不成功的经历,反倒激发了仁钦贝的信念,他已经可以确定,神山脚下的宗教势力依旧薄弱,这将是他的教派日后重要的发展方向。
考虑到教务缠身,自己又年事已高,仁钦贝开始命弟子不断带领信众造访神山。
此后,止贡派的神山探访之旅又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约在1191年左右。
但神山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这次探索因阿里爆发战乱无果而终,带队弟子连神山的影子都没看见。
1200年,不甘失败的仁钦贝,再次派弟子造访神山。
这次聂钦波和卡巴强多,参与朝圣的弟子人数多达900人②。
1208年,仁钦贝已走到了人生的晚期,所以这次朝圣探索的规模,也达到了之前人数的十倍。
就像是追求信仰,一定要经受考验一样,这次探索只是达成了在神山脚下修行的目的。
在寒风雨雪之中,众多僧侣栖身于山间的岩洞,苦苦追寻生命的意义。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僧人也要吃饭,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支持,神也坚持不了多久。
但这次探索却有个意外之喜,似乎佛祖对于止贡派的坚韧不拔,给予了褒奖。
在去往神山的途中,止贡教众路遇普兰和亚泽的王室成员,两位王子也恰巧去神山朝圣。
旅途中,仁钦贝弟子聂钦波和普兰王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普兰王子对止贡派不远千里的屡次朝圣非常敬佩,而当坐而论道时,卫藏领先的教法教义成了巨大优势。
在聂钦波口若悬河的宣讲下,两位王子被讲得张口结舌,目眩不已。普兰王子直接就拜服在聂钦波脚下,请他为自己灌顶。
在西藏历史上,请高僧为自己灌顶是很光彩的事情。高僧一般不会随便为人进行灌顶,它对施法者和受法者都有一些要求,仪式本身也有一些要求。
毕竟,灌顶是藏传佛教中一个等级颇高的宗教仪轨,不是烂大街的戏法,但聂钦波马上就接受王子的请求,就在途中为王子举行这个仪式。

得到了普兰、亚泽王室的支持,1215年(南宋,嘉定八年)生命几乎走到尽头的仁钦贝,发起了最后一次神山朝圣之旅。
这次止贡派几乎倾尽全力,带领着55525人名信徒踏上了神山之旅。这是一个令人炫目的队伍,估计称为史上人数最多朝圣队也不为过。
按演义小说里的桥段,“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五个无边无沿,铺天盖地而来。
这一路上信众的后勤工作,实在可以用噩梦来形容。估计沿途的城镇,都以为是别国军队打过来了。
要知道,即便几百年后的拉达克战争,卫臧政权也不过集合不到一万人进军阿里。这可倒好,一下子来了五万多人,这场面足够各级官吏夜不能寐的了。即便现在组织一个五万人参加的集会,都能把市长紧张得死去活来,又何况是当时。
这次神山朝圣,或者称之为进军,终于获得巨大成功,古雅冈巴•彭措加措带领下的止贡僧侣,在冈仁波齐附近的谢扎年日、达垅、拉垅、泽杰、列米、门、古格等地的众多山洞中长期驻守修行。
考虑到这次僧侣的数量,估计他们也只能栖身于山洞之中,不会有这么多房屋可以供给他们居住。
就连古雅冈巴•彭措加措也不列外,他名字前面的尊号,也是因为他最先住在一个叫“古雅冈”的山洞中而来。
人数众多也有好处,止贡派终于有机会在神山圣地建立寺院了。
在古雅冈巴的斡旋下,止贡噶举在冈仁波齐西边的达垅沟创立了远声寺(普兰县八嘎乡),这座寺院成了止贡噶举在阿里的大本营。
据说,在创立远声寺之前,冈仁波齐山神幻化成修道者,要献给古雅冈巴一块很大的黄金。
一开始被古雅冈巴拒绝了,但这时仁钦贝的神识,在他耳边告知应接受神山馈赠。

这故事其实在隐喻,止贡派必须要和当地势力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一开始古雅冈巴并没有理解此中三昧,不过好在仁钦贝及时给予了告诫。从之后止贡噶举在阿里的发展来看,古雅冈巴完美的实现了仁钦贝的愿望。
这次声势浩大的组团修炼,迅速引起了阿里政治势力的注意。止贡派得到了普兰王室的支持,别忘了之前王子可是接受过灌顶的。
《阿里王统记》记载普兰国王和止贡派非同一般的关系:“其子赤巴赞建科迎兄弟大佛像,以金汁造无数显密经集。敬信法主济登衷波,法主亲显空中,须庚之间,传语教诫。册立其子扎西俄朱衷为国君。父王遂出家为大喇嘛,号喇钦达查。是为月幢菩萨之化身。献顺缘于雪山三湖之山中修行者,呈供养于法主济登衷波及其徒众,号为噶举生命树。”
这段话的意思是普兰在大量布施后,法主济登衷波(止贡巴· 仁钦贝)的法相显示在空中“传语教诫”。在显示高深道法后,普兰国王皈依止贡派。止贡派也投桃报李赠与国王大喇嘛“喇钦达查”的尊号,标定其为月幢菩萨的化身,尊称为其为“噶举生命树”。
从此,普兰与止贡派间的关系,便成为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而止贡也借助普兰王室的世俗权力,顺利进入了阿里诸王国的权力中心。
普兰打开局面后,在拉达克传教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拉达克王统记》中记载止贡派在拉达克传播的情况,“此王之时,始遣僧徒赴卫藏,修缮先祖之诸寺。至殊胜法主三世恬主近前,献金、银、铜、珊瑚及珍珠等各百,造《甘珠尔》二,建密教坛城众。”
这段记载中“殊胜法主三世怙主”说的就是止贡巴·仁钦贝。仁钦贝的尊号为济登衮波,译为汉文便是“世间怙主”之意。
这就可以看出,仁钦贝晚年声势浩大的朝圣战略,迅速获得了收益。普兰和拉达克王室的使者均来到他座前,表明了合作的意向。而且拉达克显然对于止贡噶举更有兴趣,他们不但许可止贡噶举在其境内传教,而且还派人带着财物来到了卫藏地区,帮助止贡噶举修缮、扩建寺庙。
在古雅冈巴的辛苦经营之下,止贡噶举派成为了阿里地区最兴盛的教派,并与普兰、拉达克和古格三个王国均建立牢固的施主关系。

这种施主关系被记载在《冈底斯山志》中,原文太长,在此我就不引用了。不过,止贡噶举派在阿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之后涌现的森格益西、京俄·喜绕迥乃等高僧,屡次见诸于阿里史端,很多阿里的王室成员都接受了止贡派的“灌顶”或被传授“大手印”秘法,而成为了忠实的教徒。
同时,噶举派的寺院也在阿里各地纷纷兴建,例如拉达克著名的玉如寺,普兰王国则将科伽寺交于止贡派使用,并将周边大量土地赐予止贡派。
这种热络的政教关系持续了一百多年,14世纪末期,古格、拉达克和普兰几乎同时对止贡噶举派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寻找新的精神领袖。
在寻找思想寄托的道路上,这三个本来就关系不睦的国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继而在不同的道路上分道扬镳、越走越远!
参考书目:
①②④、生命之树_西藏阿里王朝与止贡噶举派早期政教关系研究_黄博;
③《土观宗派源流》_土观·罗桑却季尼玛;
⑤⑥、西部西藏的历史_伯戴克;
⑦、《班禅额尔德尼传》_牙含章;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欢迎关注“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