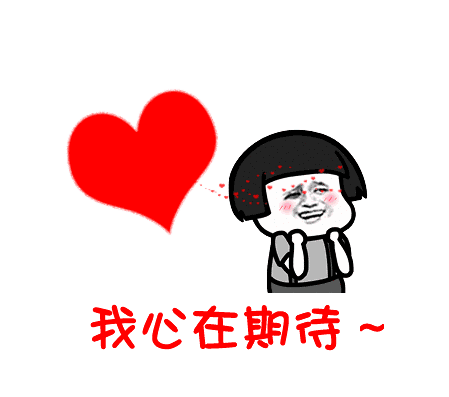“罗生门”现象似乎已然成为了公共舆论场中的一种常态。一旦私密生活中的纠纷涌入公共领域,涉事双方又各执一词,在事实水落石出之前,事态往往有往“罗生门”演变的倾向。在亲密关系中受到损害的女性该如何发声?事件的旁观者又应持有怎样的观察视角?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新作《最后的决斗》为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考。
这部电影讲述了中世纪法国最后一次司法决斗的历史和女性抗争的故事。也许是因为历史类题材不受年轻人的欢迎(据调查,《最后的决斗》一半以上的观众年龄超过了35岁),《最后的决斗》在北美上线后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北美票房首周末三天仅入账480万美元。尽管票房惨淡,《最后的决斗》却在观众中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烂番茄指数86%、爆米花指数79%,豆瓣评分也达到了8.4分。影片采用三幕式架构的叙事视角,每一部分都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观察和展现事件的真相,这种处理方式不由得会让人联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
在下文中,作者从多个维度分析比较了影史经典《罗生门》与《最后的决斗》的异同。作者认为,斯科特通过戏仿,反写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被简化后的名言;影片在形式、主题和时代还原上的成就极其平衡,仍不失为一位巨匠深耕多年后的大成之作。

《最后的决斗》电影海报。
除了大众熟知的《异形》等电影外,历史题材一直是好莱坞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所热衷的领域。从1970年代出道时的《决斗者们》,到西洋中古史爱好者视若珍馐的《天国王朝》,再到完全沦为炮灰的《罗宾汉》和《法老与众神》,雷老爷子从未放弃过他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却只有《角斗士》得过票房的垂青,其他作品都沦为历史爱好者小圈子把玩的孤品。

雷德利·斯科特,英国电影导演,以风格多变、题材广泛著称。曾以《角斗士》荣膺2000年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近年代表作为描述十字军东征的古代战争片《天国王朝》、描写美国对索马里军事行动的《黑鹰坠落》、由罗素·克劳及丹泽尔·华盛顿共同出演的《美国黑帮》等。
囿于雷导的高龄,这一次商业上折戟后,影迷们可能很难再看到下一次对历史题材如此极具野心的影像书写。然而,对雷德利·斯科特本人的艺术生涯而言,本片在形式、主题和时代还原上的成就极其平衡,仍不失为一位巨匠深耕多年后的大成之作。
《最后的决斗》剧本依据美国中世纪文学教授艾瑞克·雅格(Eric Jager)2004年的同名历史专著改编而来。其历史原型是1386年12月29日,诺曼骑士尚·德·卡鲁日(Jean de Carrouges)以妻子玛格丽特(Marguerite de Carrouges)遭乡绅雅克·勒格里斯(Jacques Le Gris)侵犯为由上诉,最终审讯无果,两人进行的法国史上记载的最后一场比武审判(judicial duel)。
因本片从三位当事人出发的章回体和审判庭辩,广大影迷首先想到的就是《罗生门》。这部影史的经典地位已经从影史溢出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那些所有悬案的代名词。同为一桩历史疑案,黑泽明无疑是斯科特的参照系之一。可如果观众仔细分析电影文本,却不难发现斯科特通过貌似粗略的戏仿,从形式到结论都反写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被简化后的胡适名言。
选择性记忆
众所周知,《罗生门》也是原案中的两男一女三位当事人从自己的角度回述了三个迥然不同的故事版本,从而引申出对人性论的探讨。然而,细究《最后的决斗》的细节,虽然片中三个事主的叙述角度迥异,在细节上不无出入(比如重归于好的台词到底出于谁口),但在内容上大体类似相同。尤其是在“强奸”这件司法上唯一重要的核心事件上,本片拍摄了两遍,可是除了特定镜头下受害人玛格丽特的反应和感受天差地别,大体流程并无差异。与此相比,《罗生门》里三个版本的故事是在角色的动作逻辑上彼此冲突,尤其是没有施害能力的武士妻子在后两个叙事中居然是误杀的施动者和唆使强盗谋害亲夫的始作俑者,在司法意义上是绝对的责任人(之一)。而在《最后的决斗》中,故事其实并不存在三个版本,而是三种其实并不冲突的选择性记忆。

《罗生门》剧照。

《最后的决斗》剧照。
“选择性记忆”的主题同样存在于《罗生门》之中,黑泽明曾通过乞丐之口说出过“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甚至都不能对自己诚实”。不过,因为案件三个版本差异过大,而且叙述者面对的是司法和镜头的双重审讯,“对自己撒谎”的选择性记忆远远低于向社会自证清白的利益使然,都是紧扣在树林里发生的奇案之上。在本片中,故事贯穿三个主角彼此三人关系形成的整个经历,连片段都不尽相同,有明显的遴选和剪辑,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选择性”记忆。以男性回忆的第一个场景为例,勒格里斯记忆中是根本不存在被卡鲁日救过一命这码事,反而是他为了掩护卡鲁日的鲁莽冲锋,才违抗军令全军尽出,以致阵线失守,进而导致卡鲁日和领主将帅离心。此外,卡鲁日在职守旁落和兵败述职时在领主面前两番当众咆哮在他本人记忆里只是一笔带过,却是勒格里斯眼中直接促成两人关系崩溃的羞辱。最直接和滑稽的证据莫过于在勒格里斯的篇章里,下一幕就是他精虫上脑地伙同下人杀到对方门外去找对方的妻子求欢,而在施害后立即接上了他虔诚忏悔的镜头。这种没有任何铺垫的粗暴剪辑仿佛是《密阳》的片段,告诉受害者和观众,其实施害者早就已经原谅他自己了。
为了强调“选择性记忆”而非为了逃脱司法制裁而扯谎,导演故意加入了一段勒格里斯向自己的领主兼密友坦诚的桥段,这样就给他脑中那段“两情相悦”赋予了“他眼中的”真实性。这个桥段在影片结构上极其重要,导致了观众和片中人物的视角错置。根据领主的现实建议,勒格里斯的角色为了洗脱嫌疑,两次向法庭陈述自己根本没有和玛格丽特发生过关系,而在他的脑海和观众眼前,他也只是在否认那次行为是一次侵犯。这需要一些台词上的巧思加以配合,所以直到决斗最后一刻,勒格里斯也只是在说,“不存在强奸”(只是一次通奸)。也就是说,司法意义上的“罗生门”是性行为是否发生,历史上的控辩双方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可这一事实对影像来说其实并无疑问,真正留待观众们裁决的是女性是否负有司法责任。
两个形象和一副躯体
那么如果说《罗生门》的人性论讨论用樵夫收养孤儿给了男盗女娼的社会现实一丝希望的话,那么《最后的决斗》的落点又在哪呢?解答的钥匙就存在于形式之中。严格意义上说,文本的三个篇章并不是三段闪回,因为片中并没有口述桥接戏中戏,而是直接用开拍板一样的字幕卡分成三章。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开篇决斗前两人披挂上阵的引子,作为标题的“决斗”本身实际上被整个容纳进了玛格丽特的章节中。如果整个案情居然还有真相的话,那也只能在决斗的旁观者玛格丽特那里。导演已经把疑问从是否发生转移到了是否犯罪上,一方面,她的命运完全不能由她本人主宰,另一方面,她的身体感受却是唯一的答案。

《罗生门》剧照。

《最后的决斗》剧照。
在两位男主角看来,这次事件始于二人兄弟反目,女性只是两人社会关系破裂的缩影;而在受害者玛格丽特看来,却只始于被动卷入的男性关系之中。在和卡鲁日的夫妻关系中,女性的角色只能在恐惧和逢迎中游离,从婚礼上丈夫当众索取嫁妆,到穿着低胸衣取悦伴侣却被斥为寡廉鲜耻,当然还有多年无后所遭受的冷言冷语。不过好感不是非此即彼的游戏,勒格里斯的形象也不见得高大。表面上他是文武双全的圣堂骑士,却也同时是一位拈花惹草的爪牙酷吏。剧情线索已经指出,正是他为平步青云而暴力执法,掠夺了玛格丽特的嫁妆,成为三人失和的导火索。这也让他在日后见面时指望通过卖弄文艺腔就讨好玛格丽特的行为显得尤为滑稽。《绣春刀》第一部里刘诗诗饰演的落难千金曾对张震饰演的锦衣卫说,当年抄我家的就是你们,现在你指望我还能爱上披着这身官服的你?如果我们算上卡鲁日为了生育“大力出奇迹”式的行房,两位男性都对女性完成了实质上的经济掠夺和肉体剥削,并没有高下。
在两位男性眼中,玛格丽特其实是男性社会中两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其一是妇唱夫随的贤妻良母,其二是心意相通的灵魂伴侣。两位男性的应对方式其实是两性关系中容易陷入的两种误区,一方是忠诚专一、默默付出,却也乾纲独断、不解风情;另一方是风流倜傥、手眼通天,不过附庸风雅,口蜜腹剑。前一种是婚姻体制和生育责任的制度性束缚,后一种则是欲望凝视和露水情缘的空口许诺,女性在形象和身体之外的具体存在始终被掩盖。导演为了女主角加上了识字这个中世纪罕见的技能,可在谈婚论嫁时重要的不过是能否生儿育女。可即便勒格里斯自诩文艺,实际上没有读出玛格丽特的冷淡,就像所有施害者永远读不懂对方的No一样。他一开始搭讪时列举的叙事诗《玫瑰传奇》包裹着浓浓的挑逗暗示,而玛格丽特回敬的圆桌骑士帕西瓦尔,却在寻找圣杯的过程中抵抗了色欲的诱惑。在中世纪典型的骑士与有夫之妇的爱情模式中,爱是单方面的追求,而女性只需要扮演缄默的欲望对象,所以勒格里斯并不在乎对方说了什么。他在霸王硬上弓前那句“如果你跑那么我会追”沿用的就是在酒后聚会上猎艳的说辞,足见在勒格里斯之流的文青眼中,“女神”只是妓女的别称。
当然,本片的女性主义表达并不难察觉,再迟钝的观众也不可能在决斗前夜玛格丽特怀抱幼子那段陈述女性生存现状的独白中略过这一点。然而,相对这样直来直去的宣教,本片真正高超的批判其实是在对案发现场的两次拍摄上。如前文所述,在两人各自的回述中,除了视角的变换,两人的形象甚至动作都并无二致,勒格里斯始终软硬兼施,玛格丽特也始终不卑不亢,不会像《罗生门》中的女性角色那样在纯洁和蛇蝎之间摆荡。从示爱、炫富到示威、施暴,整个过程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升级,因为弱者眼中的强暴可能就是强者眼中的默许。在影像上,一次侵略行为既没有春宫异梦般的浓烈色欲,也没有暗影或配乐去渲染女性的悲怆。突然、生硬、短促,不去渲染一次施暴的仪式感或侵入感,才能凸显出这种性犯罪在特定时空下的稀松平常。这不再是一桩中世纪的风流故事,平实的影像在表意上反而远胜于卡鲁日母亲画蛇添足地斥责女主角的“反向Me Too”(恶趣味的剧情设置,只要权力关系置换,Me Too完全可以用来弹压权利诉求)。

《最后的决斗》剧照。
在巴黎王室法庭,两位男性都只发表了看似铿锵有力的控辩,而所有问讯完全是围绕女性主角的私生活展开的,完全不符合教士那句“形式上这和她本人没关系”。如果真如教士所说,女性只是财产监护人的物品,那么物品的感受显然不应该在考虑范围内。更有意思的是,几位审讯者反复追问的是女主角对房事的态度。即使在男性集体进行荡妇羞辱的现场,诸位判官的道德审判也默认了以下逻辑前提:无论纠葛了多少社会关系,侵害犯罪中的事实基石只有被害者的身体感受。
女性反写下的历史针脚
需要强调的是,严格意义上说,原案只是法国历史上明文记载的最后一场有司法效力的决斗,这个定义并不涵盖典礼里的比武阅兵和民间各种的持械私斗。其戏剧性还在于双方从长枪对冲一直发展到下马肉搏,一如影片所展现的那样。想从这样两位铁甲人手中抢走戏剧核心,单靠过于被动的女性形象很难胜任。比如《龙纹身的女孩》表面上指控厌女仇外的暴行,实际上在动作中赋予女性远胜于男性的能动性。在这一点上,女主角的高光时刻仅限于得知自己可能遭受酷刑时,也能凛然站稳脚跟。勇敢固然是永恒的美德,不应被任何一种公义所忽视。但就像《华盛顿邮报》等近年的好莱坞主旋律一样,女性角色的高光其实在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创作者精心的放大上。
剧本的同名原著只在第六章最后一段提了一句,十四世纪的法国仍然存在如此这般的残酷法条,如果决斗结果证明了玛格丽特犯有伪证罪,她会被活活烧死。从庄园迢迢千里赶到巴黎高等法院的庭审现场才被告知作证的代价,还是被自己的文盲丈夫有意隐瞒,显然是编剧制造戏剧冲突的手段。此外,虽然比武审判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合法的仲裁途径,但本案几乎动员了法国所有贵胄才经过繁琐的批复和筹备。所以伪证罪是否真的会被一板一眼地执行,仍有待司法史方面专家的验证,至少不至于像片中那样直接锁在决斗现场,像妖怪洞里的唐僧一样随时等着下油锅。

小说《最后的决斗》(The Last Duel)英文版书封。
匠心独运的另一面也许是春秋笔法。剧本也对两人的前史做了更戏剧化的精简,比如勒格里斯其是卡鲁日早夭儿子的教父,再比如勒格里斯就任了埃克斯姆(Exmes)要塞的长官,而非卡鲁日被剥夺职务的贝莱姆(Bellême)要塞。这些都是枝节,只要表现出两人关系的轨迹和社会地位的落差即可。
不过庭审现场充满敌意的男性霸凌也是刻意制造的后果。首先是案发时法王查理六世还没有精神病发成为“疯王”,不但正常治国理政还颇有人望,并不是片中那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巨婴扮相。由于原告是前不久还在苏格兰远征中为他冲锋在前的贵族武士,他在收到申诉后对此案非常重视,并没有息事宁人,而是交由高等法院公审,也在最后的决斗前亲自指派王族担任侍从,确保装备上双方一碗水端平。在原案中,玛格丽特作为证人现身说法其实给了判官和舆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大大增加了申诉的可信度。法官也不太可能对一位鸣冤的贵族妇女单方面无根据加以刁难,更不至于放任在本案中没有立场的廷臣像刚目睹完贞德受难一样绘声绘色地威胁证人。反而是勒格里斯的证人,也就是片中那位敲开房门的帮凶仆人,不但没资格和当时王族老爷们并排坐在卡座包厢观战,反而是按照中世纪司法常规,遭受了多轮刑讯拷打,仍然一口咬定自己主人的清白。玛格丽特的婆婆质问“你和那些被士兵侵犯的农妇有何区别”时,显然忘了阶层壁垒才是中世纪封建的底色。
当然,围绕女权叙事改写这桩历史奇案,难免有不圆熟的地方。本案的另一个疑点其实是为什么勒格里斯会放弃他在教会的特权,不去诉诸宗教法庭。除了名誉之外,在相关学术研究中,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合法的决斗要求双方社会身份旗鼓相当。为了匹配卡鲁日的骑士身份,他也会在决斗前受到册封,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对于他这样一位家境殷实、深受重用的老年乡绅来说,骑士头衔几乎是他唯一的缺憾,也是唯一输给卡鲁日的社会硬件,可能触发他的赌徒性格。如果点明他的身份落差感,反而可以和为男性自尊而战的卡鲁日形成互补,凸显所有男性当事人的幼稚和虚荣。而缺乏这唯一的猜测,勒格里斯在片中的动机更加突兀。重复一遍,在影片的逻辑里,他上门求欢一事完全没有疑问,而历史上的司法材料还不能确证这一点。他在侵犯玛格丽特的下一幕就已经向上帝忏悔,可当他拒绝教廷介入时,已经义正严辞地自称无罪了,好像完全相信了自己的托词。亚当·德赖弗的表演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线索,让观众能理解到底他为何而战。

《最后的决斗》剧照。
那些反衬女性社会地位悲苦的台词,也都是氛围营造的必须,并不完全符合中世纪的史实。比如卡鲁日索取的嫁妆,其实应该由婚后的玛格丽特本人所支配。在中世纪更常见的礼仪性质的比武聚会中,很多出身寒门的年轻骑士囊中羞涩,全身甲胄都是要请贵妇解囊资助,这种包养关系就是“骑士之爱”的现实原型。片中卡鲁日在决斗前宣誓为妻子而战的画面,就是骑士们在比武前向异性恩主恃宠卖乖的惯用动作。如果说电影里,骑士要么是蛮壮的武夫,要么是伪善的浪子,那么在历史的维度上,他们也不过是一帮任人打扮的小白脸。
作者 | 孙一洲
编辑 | 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