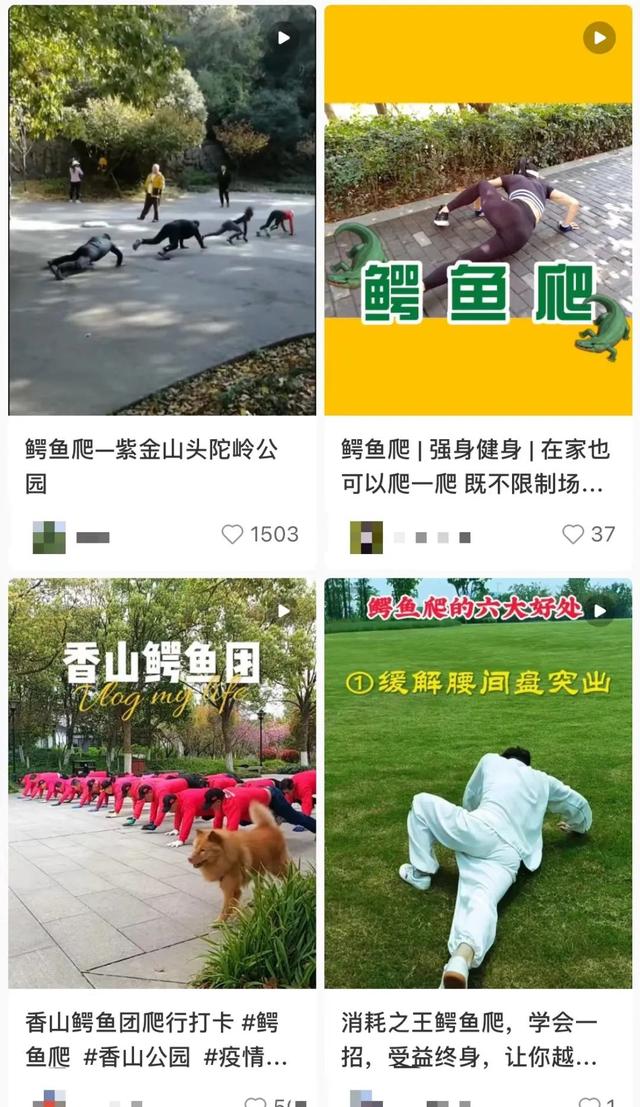我小时候经常爱往外奶奶家跑,因为吴家堡上庄和下庄之间也就三两里的路,有时候,在自己家吃罢第一碗饭,再跑到外奶奶家吃第二碗饭一点儿也不耽误。
那时候在外奶奶家经常会见到一位戴着油腻腻的瓜皮帽,满脸皱纹,留着山羊胡子的客人。
我在外奶奶家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喝茶就是喝茶,他端起茶盅哧溜喝一口茶,再放下茶盅,用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指头捋山羊胡子,边捋边和外奶奶说话,很多时候说白杨树的大哥,马莲川的姑姑等等。外爷是位木讷的人,很多时候在一旁吧嗒吧嗒的吃旱烟,偶尔插上那么一句半句的话。
稍微大点后,听我妈说,外奶奶家经常来的,外奶奶十分抬举的那位客人,是外奶奶的堂兄弟,我妈的舅舅,我的舅爷,他住在塬下的赵家油坊。他们说的白杨树,马莲川都是隔壁省的地名,解放前他们逃荒逃兵匪离开了那里,一直流落到现在的赵家油坊,当年逃难时外奶奶不到十岁,对故乡的记忆不是很深刻,她只记得庄里白杨树多得很,其他的人和事都在记忆力模糊了,解放后我的这位舅爷经常回去,而我外奶奶一次也没回去过,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听我这位舅爷说。

一起落脚到赵家油坊舅爷家族里的人,都勤恳拓荒,老实本份的务农。而我这位舅爷,这山望着那山高,下不了决心,吃不了大苦,仗着会吹拉弹唱,会阴阳风水,终日里东游西走,也没有过好个日子。
在特别困难的年月里,舅爷拖家带口回了白杨树,不久舅奶奶病亡于白杨树,他又带着两儿一女回到了赵家油坊。第二年舅爷带着娃娃去马莲川,在去马莲川的路上,大儿子又病又饿夭折,于是马莲川他干脆不去了,带着一儿一女折回到赵家油坊安分了下来,来来回回折腾得家破人亡舅爷也认命了。那时候饥饿的情况有所好转,舅爷为了拉扯一儿一女就老老实实参加劳动挣工分。这么说舅爷也是个苦肠的人。
但是这位舅爷终归是个胡日鬼的人,别说在赵家油坊,就是在他的家族、亲戚里,他的名声没那么好。
他曾经做了一件奇葩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至今被吴家堡、刘家岔和赵家油坊一带的人传为笑谈。
舅爷的女儿成人后嫁到刘家岔那边,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刘家岔婆家的光景比较好一点,在五月五过端阳的时候,女儿家烙了花馍馍,煮了甜培子,做了凉粉。面对这些丰盛的吃食,女儿想到了娘家的老父亲,自从她出嫁后,老父亲东混一顿,西混一顿,懒不说也不会做饭,最多就是搅拌汤。女儿思谋着给老父亲送点好吃得时,我这位舅爷假装路过刘家岔到了女儿的门上,女儿当然惊喜有加,侍候着老父亲吃好喝好,又给他装了一竹篾篮子吃喝,舅爷心满意足的带着女儿给的篮子回家了。
舅爷回到家,回味着女儿家花馍馍的酥软,甜培的甘甜,凉粉的滑嫩,换了旁人,会为女儿有个光景好的婆家,女儿吃穿不愁而感到高兴,而我这位舅爷却是不一样,他躺在炕上越想越嫉妒,一个坏计划在他脑海里产生了。

就在当夜,舅爷背了一个背篼,顺着赵家油坊连着刘家岔的河沟进了刘家岔,偷偷的翻墙潜入了女儿家的厨房,将油饼花馍馍,凉粉碗坨,一股脑的装进背篼里,他还发现了半袋在那个年代非常稀欠的白大米,也放到背篼里,他想着自己不会做饭,拿回去天天炖米汤喝。还有一个小罐里装满了蜂蜜,他连蜂蜜罐也装进了自己的背篼。舅爷在翻动女儿家的厨房声音,惊醒了女儿的婆婆,婆婆隔着窗子喊儿媳妇也就是舅爷的女儿,让她去看看厨房里怎么有响动是不是猫娃害人呢!懒儿使懒儿,使得懒儿挤眼儿,儿媳妇也是脱了个精光睡得挺香,不想起来到厨房看,就说吃的东西我都盖得好好的,猫娃害不了。舅爷听了婆媳的对话,灵机一动,学了几声猫叫,背了背篼,翻墙出来了。
舅爷感觉还拿得不过瘾,缺了点什么,于是沿着女儿家庄院转了一圈,手伸进鸡窝里抓了两只母鸡,夜里的母鸡受了惊吓也不出声,舅爷只消把鸡脖子一拧,提了两只母鸡才决定收手回府。
当他走到沟畔上时,回头望望熟睡中的刘家岔,偷了女儿家的吃喝,又偷女儿家的母鸡,这事只有他做得出来,他嘿嘿干笑两声,拿腔捏调的又学了几声野狐的叫唤,才不急不躁地下了河沟。
没有正能量,只说的确有这样一个人,好孬点个赞,明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