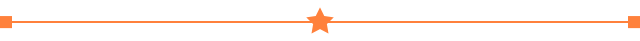《两宋萧山渔浦考》萧然客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读书可以任性,想不到写书也有这么任性的。眼前有一本《两宋萧山渔浦考》,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布面精装,定价五百,印数两百,分明赔本;作者署名萧然客,形同匿名,显然也不为赚吆喝。写什么呢?细考两宋时期临安钱塘江对岸萧山县渔浦镇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为什么要考辨这个呢?因为不忍其名之湮灭无闻或指称有误。因何不忍?因为作者卜居此间,未免有情。最直接的缘由是,他如此熟悉的一座小山,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座山,高十米,名半爿,在北纬30度8分35秒,东经120度8分45秒,于2014年被挖掘机掘平了。故此书扉页上题有一行字:“谨以此书纪念一座逝去的小山和一个时代”。
只为这一座已化为乌有的小山,作者凭乾嘉之学的本门功夫,借网络时代的潮人手段,狮子搏兔,牛刀杀鸡,利用专业文献数据库的快速检索之便,“坐拥书城,秒杀万卷”,先一网打尽历朝历代与渔浦有关的笔记、方志、宗谱、诗词、绘画、碑铭等历史文献,再细行甄别,剔除异地同名者,然后详考其方位、建置、设施、物产、人才,辑录其诗、词、画,再现了两宋萧山渔浦历史地理的真实面貌。
昔日渔浦所在的地标“半爿山”,就是《水浒》里的“半墦山”。容与堂本第九十六回,宋江征方腊,打到杭州。阮小七前来报命:
小弟和张横和侯健、段景住带领水手,海边觅得船只,行至海盐等处,指望便使入钱塘江来。不期风水不顺,打出大洋里去了。急使[驶]得回来,又被风打破了船,众人都落在水里。侯健、段景住不识水性,落下去淹死海中。众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了。小弟赴水到海口,进得赭山门,被潮直漾到半墦山。
“半墦山”,也如“半瓣山”“半边山”,都是“半爿山”一音之转。阮小七这段话,透露了作者施耐庵对浙江地形与水势的娴熟。由于近代围垦造田使江面变窄许多,钱塘江潮的势头大不如从前了。要知道,唐时潮头可达建德,宋时也可到桐庐,所以才那么猛,既能将船打出大洋去,又能将人荡到上水来。
读《两宋萧山渔浦考》,我们对浙江——更准确地说——之江的交通地理有了更亲切的了解。自元明以后,茅以升建钱塘江大桥之前,萧山西兴是必经的渡口。但从此书得知,杭越自江而济,原有东西二渡:浙江渡在候潮门外,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下,对渔浦。龙山-渔浦的东渡,在两宋时繁忙程度远逾西渡,正如苏东坡《乞相度开石门河状》所言:“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自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苏州、嘉兴运往衢州、睦州的米,富阳、桐庐运来杭州的柴,都经龙山渡中转。东坡描叙了龙山渡的险况,说他“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何以至此?却原来半爿山对岸,如今泯然于十里新沙地上的浮山,直到民国,都还是兀自突立在江心,与远盛于今日的潮水相摩相激,当然凶险万状。但避又不能避开,因为渔浦一边水浅沙多,航道深处乃在浮山一侧,通达须向险中求。南宋楼钥《北行日录》,记过龙山渡之艰辛与危殆甚详: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巳间晴,早作饭了,同周君行数里,三憩方到渡头。装载既毕,潮落舟胶,监渡厉君以小舟般剥,已又加一舟,荡兀波间,久之,大舟既前,复挈行李装载,劳扰良甚。又舣棹食顷,挽繂徐行。近庙山始用橹,潮上方急,篙橹努力欲进,为山石所激,进寸退尺,舟人失色。少纵复上,久方得过。又挽行十余里,雨霁风静,一波不兴,至六和塔下登岸,已薄暮矣。驱驰至嘉会门,闭关已久,宿俞家店。
我们今天驱车,从渔浦那个位置,只要不堵,过钱塘江大桥,或者绕一下走之江大桥,到六和塔都只需十来分钟。古人却要小船换大船,大船小船牵,扯篷拉纤地折腾一整天!
李白、杜甫都曾“一度浙江北”,“渡浙想秦皇”,当日过江想必也备尝辛劳,哪有他们留下来的诗句那样写意。其实就算到了一百年前,周作人仍然说:“过钱塘江是一件危险的事,恐怕要比渡黄河为危险。因为在钱塘江里特别有潮汛,在没有桥也没有轮渡的时候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周作人指的是西渡。《知堂回想录》写他1901年夏天去南京水师学堂,从西兴渡江,要心惊肉跳地走上很长的许多跳板,才能上船:“特别是沙滩浅而远,渡船不能靠近的时候,需要跳板接出来,而这跳板长而且软,前面有人走着,两条板一高一低,后面走的着实困难。差不多要被掀下水去的样子。等上了船,这才可以安心了。”可上了船之后,还得要像阮小七那时候一样看风水顺不顺。有风就挂帆,万事大吉;没有风的话,得摇橹。三四个船夫不够,乘客就得帮忙摇。穿长衫者可免,穿短打的不主动就会挨船夫的恶骂。这经验鲁迅当然也有过不止一回。可以说,从李白、杜甫到鲁迅,他们过钱塘江的方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其对于行旅,恐怕都有绳子勒到肉里去的经验,我们今天是再难体会和想象了。
楼钥过龙山渡写到监渡某某。北宋时江河要津设官渡,禁私渡。官渡设监官,钱塘江渔浦、西兴二渡,每天度人不止千百,管理是大事也是麻烦事。作者一一抄录了《宋会要辑稿》中有关渔浦渡的条目,可见从定都临安到开禧北伐,七十年间管理上张弛交替的情况。总是初时措置甚严,岁久复成玩习,但好在官员们能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打造船只,招聘水手,到完善交通秩序,落实安全责任,超载怎么罚,全年无事故怎么奖,都一一作了规定。特别讲到早先以出钱多少为渡客先后,显然缺乏社会公平。后来改为卖牌上船,船钱划一。船分五色,牌也分五色。客持某色牌,就上某色船。这简直是现代管理的一套了。宋代社会交通运输的进步,贸易流通的有序,商业运作的复杂,可见一斑,从微观上也说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不为无据。只是作者却从宝佑年间江上寇盗剽掠客船的事件,而发出“宋之不亡其可乎”的喟叹,实在是言重了。江上遇见船火儿张横,被逼做“你是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的选择题,是元朝人施耐庵虚构的故事,在宋朝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吧。
《两宋萧山渔浦考》复原了两宋浙江渡的情形之外,还提供了许多渔浦当地的生产与生活知识,如为何筑堰修塘,怎样淋卤煎盐,等等。渔浦离海有点远,却有许多利用海潮制盐的盐场,尽管潮水过了六和塔一带,所含盐分已经不高,但当时盐课居然也视海水之浓淡定税额之高低。而且煎盐需燃料,官谕盐场周围特留草场,不得偷牧,违者拘捕。这样细腻的管理措施,谁能说不是善治,如果执行比较到位的话?我一直觉得,历史如同新闻,也是报忧不报喜,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社会系统若是运转良好,就不用载在史册了,因为人之常情,只有来事儿,才会来劲儿。
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读罗庸的《习坎庸言》,开篇说古人之学重在为己,西人之学长于格物,于今我辈当认清为己与格物之为一;又说西方汉学家治学态度往往流于冷酷,而“国粹学者,动多故国之思,对中国之山川景物,小至一草一木、一花一叶者亦莫不寄以深厚爱护之情,发之于文章者,低回流连不能自已”,流弊却在不分好歹,照单全收,缺乏批判精神。我从《两宋萧山渔浦考》所得偏多,因为看到了为己与格物的统一,抒情气质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作者为山作传,为水作诔,伤逝惜别,情难自禁。而为乡邦文献考实存真,所给予作者智性的满足也自不待言。他在后记里说:“是稿爬梳剔抉,小心求证,必先惬于己心而后已。”如今有太多苦大仇深的学术民工,从写作中得不到一丁点快感。而读这本书,我们却见猎心喜,看作者怎样将心中疑团一一作定点清除:何以谢灵运诗中渔浦或为富阳渔浦,陆游诗中渔浦多为桐庐渔浦,而明清后所称渔浦乃许贤渔浦,等等。这些问题对别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对作者自己却十二分要紧。陆机《文赋》说“惬心者贵当”。要想“惬于己心”,非“绳其必当”不可。作者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书中使用了多幅Google Earth的卫星照片截图,最新的一幅是2014年。作者又利用汉字转化unicode编码技术,特地保留了所有引文的异体字、俗字甚至别字,如“富”作“冨”,“尝”作“甞”,“窗”作“窓”“窻”,诸如此类。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趣?你看作者署名,中文名萧然客之外,还有一英文名Blade Hsiao,估计是戏仿萧伯纳的Bernard Shaw。注意Hsiao是用韦氏拼音。而blade又有荡子的意思。胡兰成《今生今世》一开头就说:“我不但对于故乡是荡子,对于岁月亦是荡子。”山川易容,城市改观,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变成他乡,作者对此或许也有同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