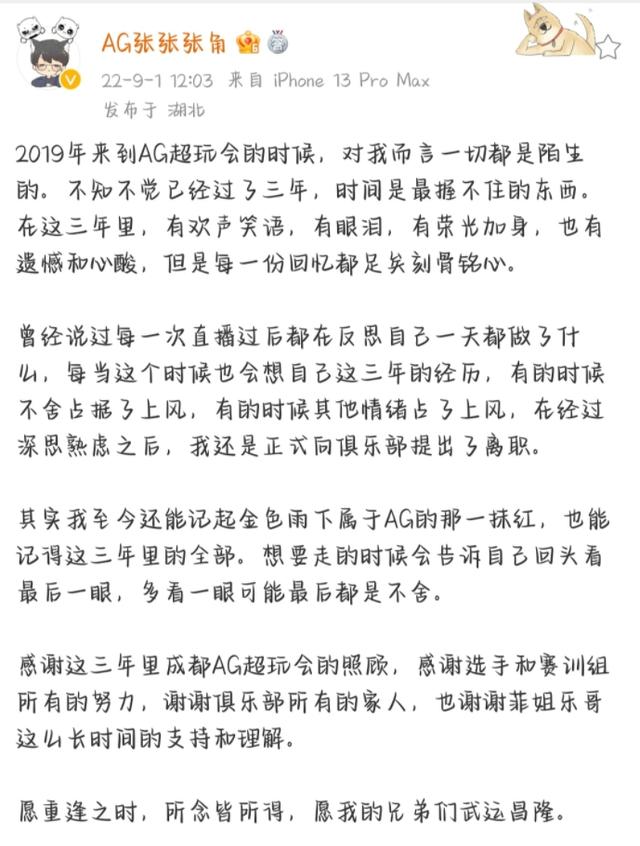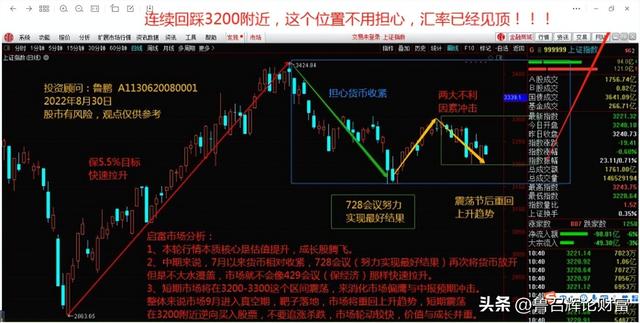作为一个台州人,你可能每天都在说着台州方言。但是,你能保证你念的都是准确的吗?你知道你正在说的方言是怎么写的吗?你又是否知道它是如何演变过来,中间有什么规律呢?5月7日晚,台州方言研究者程和平老师做客千禧读书会,为书友们打开一扇关于台州方言的新大门。
普通一个汉字,你用普通话去读它,这非常容易,但是方言就不一定了。打个比方:“携带”,你用方言读,是读“鞋带”还是“盐带”?再比如说“寂寞”,是读“鸡木”吗?“阿叔”为什么读“阿宋”?“万”的方言音同“饭”,要是有人说“万”的方言音也同“慢”,你信吗?所谓“青蟹”,台州人历来称“营”。你知道“营”的来历吗?你还知道这个“营”要写成“螾”吗?老话讲“铜钿丢水的蓬也弗会泛”,这个“蓬”字究竟怎么写?老话又说“连紧叫师傅,背脊洒大锣”。意思是关键时你找师傅帮助,但是晚了,你已经挨揍了,你的背像敲锣一样被人家敲了。敲锣,台州话叫“洒锣”,但是“洒”是白字,这个字真正写法是“筛”,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有一定规律的!
我们先来讲讲方言的读音。一个认识的词你可以很容易就用方言念出来,那么,如果碰到一个你不认识的词怎么办?一般的方言,我们可以查字典来解决,不是《新华字典》,而是《康熙字典》或者《辞源》(这两本工具书的语音系统与台州方言语音系统有密切联系)。怎么给一个汉字注音?最早的时候使用直音的办法,如“乐,音洛”。但是,这个方法不是所有时候都适用,某个字没有同音字就没办法注音。于是,有人发明了反切法:用两个汉字去给一个汉字注音。《康熙字典》里用的就是反切的注音方法。比如说冬天的“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d],“宗”的韵母[ong],拼出[dong],声调与第二个字声调相同。
这种注音的优点是用在方言拼读上也基本适合。如椒江方言可以切出椒江方言字,临海方言可以切出临海方言字。举个例子,“老婆”的发音,台州有些地区念[lǎo bó],有些地区念[lǎo bú]。我们如果利用方言字反切,拼出来的读音比普通话注音系统拼出来的读音更地道。在《康熙字典》里,“婆,蒲禾切”,我们用自己家乡话念出蒲扇的“蒲”和禾苗的“禾”两个字读音,然后根据上面的反切法,就能读出方言系统里的“老婆”的准确读音。
通过方言语音规律,我们还可以考证出许多平常只会念而不会写的方言字。比如“钞票[kāng]皮包里”的“[kāng]”字,大家都知道是“藏”的意思,但不知道对应的汉字怎么写。它的正确写法是“囥”,《集韵》解释为“口浪切,囥音亢,藏也”。
又如普通话“溅”字对应的台州方言我们大多也不清楚,其实是“灒[zàn]”字。《西游记》44回中就有出现:“烹的望里一捽[zuó],灒了半衣襟臭水。”
以此类推,“鱼刺卡喉咙里了”这句话,用台州方言来念是“鱼刺鲠喉咙里了”。“鲠”字在《广韵》里解释是“刺在喉,古杏切”,反切出来的读音与台州方言同。“鲠”又写作“骾”,因为鱼刺能卡住喉咙,骨头也能卡住喉咙,所以偏旁有所变化。与“鲠”同音的“哽”字,也是地道的台州方言字,“哽饭”即“吃饭”,不过“哽饭”语气较硬。
“养” ,一般人以为是“营养”的“养”。在方言里,有蓄发,留胡子,(植物)蓄留,成长的意思。比如一些男生赶时髦,留长发,家长经常批评道:“头发养来个长,好去剪短点了。”在《广韵》里,“养”有两个读音:“余两切,音痒。又余亮切,音样。”在以北京话为主的普通话里,“养”没有蓄发、蓄留等意思,但台州方言里保留了“养”的两种读音,两类含义。温岭方言俗语“养谷养米,养麦养皮”,意思是稻子留到晚几天收割,能使米粒更饱满;麦子留晚了割,只能使麦麸更厚(言外之意麦粒不会更饱满)。
“螾”这个字应该重点讲讲。青蟹为什么要读成“螾”?清朝《光绪黄岩县志》中有这样一句话:“蝤蛑,俗谓之螾。” 再往前,宋朝《嘉定赤城志》解释“螾”:“八足二螯,随潮退壳,一退一长。最大者曰青蟳(音寻),斑者为虎蟳。后二足扁阔,名拨棹。”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蟳”字,蟳就是蝤蛑,和我们说的螾是一个东西。在字典里,“螾”不是我们说的青蟹的意思,我们只是借助了它的音来指代青蟹。原来,蝤蛑本来读作“由牟”,快速连读时,两个字合成一个音,“蛑”字只保留鼻音[m]。根据方言语音系统的特点,[m]又变成了[n]或者[ng]。也就是说,“螾”是“蝤蛑”合音所致。那“蟳”这个读音又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蝤”还有一种读音,自秋切,念“咻”。蝤蛑快速连读时,两个字合成一个音,逐渐变成了“蟳”音。
我们再将方言的声调和普通话的声调作下比较。普通话的声调包括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另加一个轻声。这些都是从古代的声调里延续下来的,但是,古音里的“入声”在北京话里消失了,读入声的字在北京话被分到其他几个声调里去了。在台州方言里,存在保留着大量入声。
入声字的特点,就是比较短促。所以我们在用方言念古诗,特别是入声押韵的诗,读起来就非常有味道。我们方言的童谣,很多都是入声字,像“一二一,一二一,长枪擐背脊。操练全弗识,吃饭我第一”,押入声韵,用普通话根本念不出那感觉。
在台州方言中还存在着文白异读现象。书面的读法叫文读,白话的读法叫白读。比如说“大”,在“大学”里读[dá],属文读,在“大儿”里读[dú],属白读,因为大学这个词来自书面语,不能白读。比如“差”,在“温差、时差、差距等”词中文读为[cā],在“差弗多”中白读[cuō]。再比如“肥”,在书面语转化过来的“肥胖、化肥、肥皂”等词中都文读为[fí],在“肥桶、小肥、大肥、肥猪肉”等方言词里白读为[bí]。文白读不能混搭,它们都有固定搭配。
文白异读时,文读中的的[ü]音,在白读时往往读成[ei]音。比如“渠”,文读读[gǘ],例“渠道”;白读读[géi],就是你我他的“他”,例“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同理,“去年”中的“去”文读为[kü],白读为[kēi](有些地方进一步简化,[ei]读为[i],“去”就白读为[kī]);“拉锯战”中的“锯”文读为[gü],“锯末粉”中的“锯”白读为[gēi];“空虚”中的“虚”文读为[hü],“馒头虚起来了”中的“虚”白读为[héi]。
总之,台州方言里有许多规律可循,方言里也保留了大量古音古义。因此,真正深入了解台州方言,它还是挺高大上的。
来源:中国台州网
申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