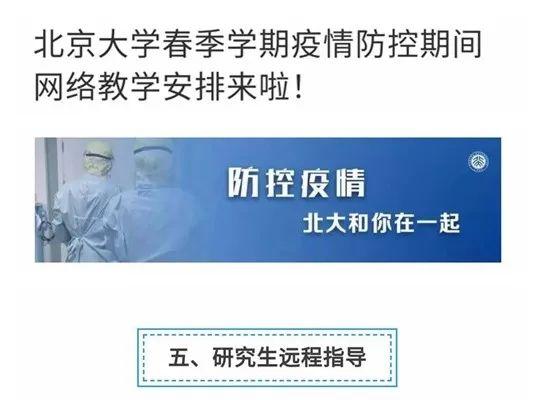【原创】求知若渴,虚心若愚【评分】⭐️⭐️⭐️,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苏菲的世界的读书心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苏菲的世界的读书心得
【原创】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评分】⭐️⭐️⭐️
为了您能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
欢迎关注漫游在云海的鲸鱼
致力于分享富有启发性的读书笔记和影视评论
---
要有批判性的思考态度。黑格尔称之为否定的思考。
又会有一次大爆炸,而宇宙也会再度开始扩张,因为到时同样的自然法则又会发生作用。所以会形成新的星球和新的银河系。那这些银河系会不会再度聚拢成一个紧密的核心呢?
各银河目前仍继续以极高的速度向宇宙的四面飞散。当这些物质碎片逐渐冷却后,就形成各个星球、银河系、卫星与行星。
宇宙间所有的物质都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由于物质密度极高,再加上重力的作用,使得这些物质温度高得吓人。温度日趋上升的结果,这一团紧密的物质终于爆炸了。我们称这个现象为‘宇宙大爆炸’。
如果你有一个气球,而你在它的表面画上许多黑点。然后你愈吹它,那些黑点就分得愈开。这就是宇宙间各银河系所发生的现象。我们说宇宙在扩张。
唯有清晰地意识到有一天她终将死去,她才能够体会活在世上是多么美好。
比起少校的重型大炮来,我们这一点点自主性当然只能算是极其微弱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顽强抵抗的能力,不管这种能力是多么微弱。
他们想要‘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他们认为人民之所以过着贫穷、备受压迫的生活,是由于他们无知、迷信所致。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教育儿童与一般大众上。所以,教育学这门学科创立于启蒙时代并非偶然。
当时所有知名的哲学家与文人都参与了编纂工作。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你在这套书中可以查到所有的知识,上自铸造大炮的方法,下至制针的技术。
卢梭相信大人应该让小孩子尽量停留在他们天真无邪的‘自然’状态里。
所谓‘自然神论’是指相信上帝在万古之前创造了世界,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现身。上帝成了一个‘至高的存在’,只透过大自然与自然法则向人类显现,绝不会透过任何‘超自然’的方式现身。
一种是不断找寻他对哲学问题的答案的人。另一种则是精通哲学史,但并不一定曾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的人。
如果他只是一个很好的哲学教授,通晓其他哲学家的理念,他就不会在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他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与洛克、柏克莱和休姆等人的经验主义都很精通。你应该还记得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的心灵是所有知识的基础,而经验主义者则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都是从感官而来的。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事物‘本来’的面貌。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我们眼中‘看到’的事物。
请携带保暖的毛衣与适于解开哲学之谜的高明主意。欢迎大家尽情燃亮想象力的火焰。此一宴会将不对外开放。新闻界人士也恕不招待。
最初是为了反对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过于强调理性的做法。在康德和他那冷静的知性主义成为过去式后,德国的青年仿佛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浪漫主义者便利用这点发展出几乎毫无限制的‘自我崇拜’,并且因此而歌颂艺术方面的天才。当他内心充满艺术的狂喜时,他可以跨越梦境与现实的藩篱。他们对神秘的东方等遥远的文化也怀有一份憧憬。有些浪漫主义者则受到夜晚、黄昏、古老的废墟与超自然事物的吸引。他们满脑子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生的‘黑暗面’,也就是一些阴暗、神秘、不可思议的事物。
那些浪漫主义者有点像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嬉皮。你是说那些留长发、漫不经心地弹吉他并且随地躺来躺去的人?
闲散是天才的理想,懒惰是浪漫主义者的美德。’浪漫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体验生活——或是成天做白日梦、浪费生命。至于日常的事务留给那些俗人做就行了。
拜伦和雪莱都是所谓的‘恶魔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更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偶像。所谓的‘拜伦式的英雄’就是指那些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都特立独行、多愁善感、叛逆成性的人。拜伦本人可能就是一个既任性又热情的人,再加上他外貌英俊、因此受到了许多时髦妇女包围。一般人认为,拜伦那些充满了浪漫奇遇的诗其实就是反映他个人的生活。
当你说‘浪漫主义’的时候,我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那些巨幅的风景画,上面有幽暗的森林、蛮荒崎岖的自然景观……还有,最好笼罩在一片缭绕的雾气中。
写一些灵感泉涌的诗歌和研究植物的生命或岩石的成分只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大自然不是一个死的机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精神。
除了民间故事之外,他们也采集各种民谣、整理挪威的语言,并挖掘异教时代各种古老的神话与传奇冒险故事。欧洲各地的作曲家也开始将民俗音乐写进他们的作品中。
童话故事是浪漫主义者理想中最完美的文学类型,就像剧场是巴洛克时期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一般。它使得诗人有充分的空间探索他自己的创造力。他可以在他虚构的世界中扮演上帝的角色。他在写作时也许是处于一种被催眠般的恍恍惚惚的状态。他会出面干涉,向读者说一些讽刺性的话,让他们至少在那一刹那间会想起他们所读的毕竟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就算艾伯特和苏菲只是他虚构的人物,可是他在展示他的力量时也应该有个限度呀。
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体系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试图为人们对世界的知识建立一套永恒的标准。笛卡尔、斯宾诺莎、休姆和康德等人都是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试图探索人类认知的基础。
你的思考方式乃是受到宛如河水般向前推进的传统思潮与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你永远无法宣称任何一种思想永远是对的。马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和它抵触的思想,于是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又会因为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融合了两种思想长处的思想而消除。黑格尔把这个现象称为一种辩证过程。
你可以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正’,那么与他正好相反的休姆的经验主义就是‘反’。但这两种思潮之间的矛盾或紧张状态后来被康德的‘合’给消除了。康德同意理性主义者的部分论点,但也同意经验主义者的部分论点。在争辩过程中,双方论点中最佳的部分通常都会显现出来。
本质上她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感情体系。如果由女人来领导政府,则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因为她们并不是依据整体的需求行动,而是随兴之所至而决定的。
显示一种辩证的紧张关系如何能够导致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并因此造成突然的改变。
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
如果基督教所诉求的是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另外一面,那它就不叫做信仰了。
他的笔锋犀利,讽刺起人来也很尖酸刻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厌烦的,就是不好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
我们通常说大哲学体系的时代到黑格尔为止。在他之后,哲学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不再有庞大的思考体系,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称的‘存在哲学’与‘行动哲学’。马克思曾说,直到现在为止,‘哲学家只诠释了世界,可是重点在于他们应该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显示了哲学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马克思将这些物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件称为社会的基础,并将社会思想、政治制度、法律规章、宗教、道德、艺术、哲学和科学等称为社会的上层构造。
当时马克思已经指出人类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基础的产物,达尔文则证明人类是生物逐渐演化的结果,而佛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则发现人们的行动多半是受到‘动物’本能驱策的结果。
那么我们还是将它付之一炬吧,因为这样的书内容纯粹是诡辩和幻象。
组成一幅想象图画的各个元素必然曾经在某一时刻以‘单一印象’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灵。否则一个从未见过黄金的人又怎能想象出黄金街道的模样?
这是笛卡尔哲学的基础,是他全部的哲学赖以建立的一个清晰判明的知觉。
真实启蒙之于人
如同阳光之于土
清净无为、退隐山林可以成为一种宗教理想。同样的,在古代的希腊,许多人也相信禁欲苦修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可以使灵魂得救。
对他们而言,生命的目的不在脱离轮回,而在于从罪恶与谴责中得救。此外,西方的宗教生活较偏重祈祷、布道和研究圣经,而不在于自省与打坐。
不仅将使以色列人挣脱异族的桎梏,并将拯救所有世人,使其免于罪孽与上帝的责罚,得到永生。
无怪乎他会被钉上十字架,因为他那些有关救赎的崭新信息已经威胁到当时许多人的利益与在位者的权势,因此他们非铲除他不可。
古代就像欧洲的童年,然后到了漫长的中世纪,这是欧洲的学生时期。最后终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此时,漫长的求学时期结束了。欧洲成年了,充满了旺盛的活力以及对生命的渴望。
生命本来就是悲伤而严肃的。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彼此相逢,彼此问候,并结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对方,并且莫名其妙就消失了。
当时有愈来愈多的人强调人们不能透过理性与天主沟通,因为天主绝对是不可知的。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事不是去了解神的奥秘,而是服从神的旨意。
它是指古代艺术与文化的再生。另外我们也说它是‘人道主义的复兴’,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从神的观点来解释,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切又重新以人为中心。
在文艺复兴时期,发掘古代的经卷典籍几乎成为一种大众休闲活动,学习希腊文也变成时髦的玩意。当时的人认为,修习希腊的人文主义有教导与启发的功能,它除了可以使人了解古代的思想文化之外,也可以发展他们所谓的‘人的特质’。
有了罗盘,航海就比较容易了,这为后来一些伟大的探险航程奠定了基础。火器也是一样,这种新式的武器使得欧洲军队的军力要比美洲和亚洲的军队强大。在欧洲内部,是否拥有火器也成为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因素。印刷术则在散布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理念方面有很重要的贡献,同时印刷术的发明也使得教会不再是唯一能够散播知识的机构。
这个时期人们的目标是要打破所有的藩篱与禁忌。从希腊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说,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因为古代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宁静、中庸与节制。
各个领域都有无可比拟的进展。无论艺术、建筑、文学、音乐、哲学与科学都以空前的速度蓬勃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审判女巫、烧死异教徒的风气非常盛行。魔法、迷信充斥,而且不时有人发动血腥的宗教战争。
愈来愈多思想家警告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权威,无论是宗教教条或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但也有人劝告大众不要相信纯粹凭思考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人们过度迷信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研究大自然现象必须以观察、经验与实验为基础。
如果你坐在火车里,把一个苹果丢在地上。苹果并不会因为火车正在移动而向后掉落,而是垂直落地。这是由于‘惯性定律’作用所致。苹果维持在你将它丢下以前同样的速度。那是因为有其他外力迫使它停下来。第一种力来自于地板,尤其是那种粗糙不平的木头地板。然后则是重力。在重力的作用下,球迟早会停下来。
我们都可以看到夸张华丽的自我表达形式,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股退隐避世的潮流逐渐兴起。在艺术方面,当时的绘画可能一方面描绘极其繁华奢靡的生活,但在角落里却画了一个骷髅头。从很多方面来说,巴洛克时期的特色是浮华而矫饰的。但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人意识到世事无常,明白我们周遭的美好事物终有一天会消殒凋零。巴洛克时期的建筑特色在于屋角与隙缝有许多细部装饰。同样的,当时政治情势的特色就是各种阴谋与暗杀充斥。
脑外科医生是个基督徒,那位太空人不是。太空人说:‘我到过太空许多次,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上帝或天使。’脑外科医生答道:‘我开过很多聪明的脑袋,也没有看过一个思想呀!’”
他在年轻时就已经有强烈的欲望要洞悉人与宇宙的本质。但在研习哲学之后,他逐渐体会到自己的无知。
他像苏格拉底一样,相信唯有透过理性才能获得确实的知识。他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古籍的记载,也不能完全信任感官的知觉。
而第一个创立一套重要的哲学体系的人正是笛卡尔。在他之后,又有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洛克、柏克莱、休姆和康德等人。
古代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几位伟大的哲学体系创立者。中世纪则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的神学搭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有关自然与科学、上帝与人等问题的思潮汹涌起伏,新旧杂陈。一直到十七世纪,哲学家们才开始尝试整理各种新思想,以综合成一个条理分明的哲学体系。第一位做这种尝试的人就是笛卡尔。他的努力成为后世各种重要哲学研究课题的先驱。他最感兴趣的题目,是我们所拥有的确实知识以及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这两大问题成为后来一百五十年间哲学家争论的主要内容。
我决定要跑步赶公车,下一秒钟我的两腿就像发条一样跑起来了。有时我坐在那儿想某件令我伤心的事,突然间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因此,肉体与意识之间一定有某种神秘的关联。
笛卡尔希望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哲学性的思考。他用一般人证明数学定理的方式来证明哲学上的真理。
在兴建一栋属于自己的新房子以前,他想清除房屋地基上的所有旧瓦砾。
有一件事情必定是真实的,那就是他怀疑。当他怀疑时,他必然是在思考,而由于他在思考,那么他必定是个会思考的存在者。
灵魂也能够挣脱这种‘原始’冲动的控制,而独立于身体之运作。它的目标是使理性获得掌控权。
镜中的女孩却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无论苏菲做什么,她都依样画葫芦。苏菲飞快地做了一个动作,想使镜中的影像追赶不及,但那个女孩却和她一般的敏捷。
小小玛莉来到人间,惊鸿一瞥魂归高天。
是谁给苏菲这样一记当头棒喝,使她突然脱离了日常生活,面对这样一个宇宙的大谜题?
她生平第一次开始觉得无论在学校或其他地方,人们关心的都只是一些芝麻琐事罢了。世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有待解答,这些事比学校所上的任何科目都更重要。
人的嗜好各有不同。有些人搜集古钱或外国邮票,有些人喜欢刺绣,有些人则利用大部分的时间从事某种运动。
另外许多人以阅读为乐,但阅读的品位人各不同。有些人只看报纸或漫画,有些人喜欢看小说,有些人则偏好某些特殊题材的书籍,如天文学、自然生物或科技新知等。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问某一个正生活在饥饿边缘的人,他的答案一定是“食物”。如果我们问一个快要冻死的人,答案一定是“温暖”。如果我们拿同样的问题问一个寂寞孤独的人,那答案可能是“他人的陪伴”了。读一读别人的意见倒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己对生命的看法。
在娘胎里短短几个月后,他们便掉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过当他们慢慢成长时,这种好奇心似乎也逐渐减少。如果一个初生的婴儿会说话,他可能会说他来到的世界是多么奇特。因为,尽管他不能说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左顾右盼并好奇地伸手想碰触他身边的每一样东西。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比较见多识广的人可能会觉得小孩子这种兴奋之情洋溢的样子很累人。大多数人都忙于日常生活的琐事,因此他们对于这世界的好奇心都受到压抑。我希望你有一个好奇、充满求知欲的心灵。你会不会试着为突然下雨的现象找出某种解释?你会不会编造出某种神话来解释雪到哪儿去了,及为何太阳会升起?你是否会惊叹水中如何会有活鱼、瘠土里如何会长出高大的树木与色彩鲜丽的花朵,女人的子宫居然会生出婴儿?
每天爸爸都用一个很滑稽的机器刮胡子,有时他会爬到屋顶上调整电视的天线。或者,他偶尔也会把头伸进汽车的引擎盖里,出来时脸都是黑的。
这个世界一直都有一些不合理,甚至有些复杂难解、神秘莫测。哲学家终其一生都像个孩子一般敏感。
毫无疑问,这位哲学家救了她。写信给她的无名氏将她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拯救出来了。
这些宗教上的解释透过神话的形式代代流传下来。所谓神话就是有关诸神的故事,其目的在解释为何生命是这番面貌。
可能有的哲学家想探索植物与动物是如何产生的,有的则想研究世间是否有上帝或人的灵魂是否不朽等问题。知道了每一位哲学家的“课题”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他的思想的脉络,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会企图探讨哲学的所有领域。
原来是属于物质的东西何以会变为有生命的物体?
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所提的问题与他们在物质世界观察到的变化有关。他们想寻求其中隐含的自然法则。他们想要从古代神话以外的观点来了解周遭发生的事。最重要的是,他们想要透过对大自然本身的研究来了解实际的变化过程。这与借神话故事来解释雷鸣、闪电或春去冬来的现象大不相同。
泰利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我们并不很清楚这话的意思。或许他相信所有的生命源自于水,而所有的生命在消融后也仍旧变成水。他在埃及旅游时,必定看过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洪水退去后,陆地上的作物立刻开始生长的现象。他可能也注意到凡是刚下雨的地方一定会出现青蛙与虫子。更可能的是,泰利斯想到了水结成冰或化为蒸气后又变回水的现象。
赫拉克里特斯说:“所有事物都是流动的。”每一件事物都在不停变化、移动,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变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条河流中涉水两次”。当我第二次涉水时,无论是我还是河流都已经与从前不同了。
赫拉克里特斯指出,世间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从未生病,就不会知道健康的滋味。如果我们从未尝过饥饿的痛苦,我们在饱足时就不会感到愉悦。如果世上从未有过战争,我们就不会珍惜和平。如果没有冬天,春天也不会来临。
我们身体的构造也是一样。假如我的指头上掉落了一个皮肤细胞,此一细胞核不仅会包含我皮肤的特征,也会显示我有什么样的眼睛、什么颜色的头发、有几根指头等等。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带有决定所有其他细胞构造方式的蓝图。
当一个物体——如一棵树或一只动物——死亡并分解时,原子就分散各处并可用来组成新的物体。这些原子在空间中到处移动,但因为它们有“钩”与“刺”,因此可以组成我们周遭所见的事物。
积木的性质多少与德谟克里特斯所说的原子相似,这也是为何积木如此好玩的原因。首先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其次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形状与尺寸,它们是硬而且不可渗透的。它们也有“钩”与“刺”,使得它们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任何你想象得到的形状。组合完成后,你也可以将它们拆掉,用同一批积木再组成新的东西。
我鼻头细胞里的一个氢原子以前可能属于某只大象的鼻子;我心脏肌肉里的一个碳原子从前可能在恐龙的尾巴上。
德谟克里特斯并不相信有任何“力量”或“灵魂”介入大自然的变化过程。他认为世间唯一存在的东西就只有原子与虚空。由于只相信物质的东西,因此我们称他为唯物论者。
现代仍有许多人相信纸牌算命、看手相或观察星座以预知未来等。挪威人有一个用咖啡杯来算命的特别方法。当咖啡喝完后,杯底通常会有一些咖啡粉的残渣。这些渣子可能会形成某种图案——如果我们运用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话。假使杯底的渣子看来像是一辆车子,那也许就表示喝这杯咖啡的人将驾车远行。
当我们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时,我们只能看到许多呈不规则分布状的闪亮小点。尽管如此,千百年来仍有不少人相信可以从星星里看出人类的命运。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政治领袖在做重要决策前会征求占星学家的意见。
裂缝中会冒出一股催眠般的蒸气,使她进入恍惚的状态,而成为阿波罗的代言人。而她的回答往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因此必须由祭司加以解释。有许多国家元首要等到求教于神谕后,才敢打仗或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因此阿波罗的祭司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外交家的功能,也可以说他们是熟悉人民与国家事务的顾问。
古希腊人相信疾病可能是神降的灾祸,也相信只要人以适当的方式向神献祭,神就可能使生病的人痊愈。
当时的雅典人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精通演说术,也就是说要能够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教师和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老师自认为懂得很多,并且强迫我们吸收。哲学家则是与学生一起寻求答案。
我们对于感官所感受到的事物,只能有模糊、不精确的观念,但是我们却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用理智所理解的事物。三角形内的各内角总和一定是一百八十度,这是亘古不变的。而同样的,即使感官世界中所有的马都瘸了,“理型”马还会是四肢健全的。
理性追求智慧,意志追求勇气,欲望则必须加以遏阻,以做到“自制”。唯有人体的这三部分协调运作时,个人才会达到“和谐”或“美德”的境界。在学校时,儿童首先必须学习如何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后再培养自己的勇气,最后运用理性来达到智慧。
苏菲心想:“我看过这只松鼠!”然后又悟到也许这只松鼠并非她从前看到的那只,但她看过同样的“形式”。在她看来,柏拉图可能说得没错。也许她过去真的见过永恒的“松鼠”——在理型世界中,在她的灵魂还没有栖息在她的身体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