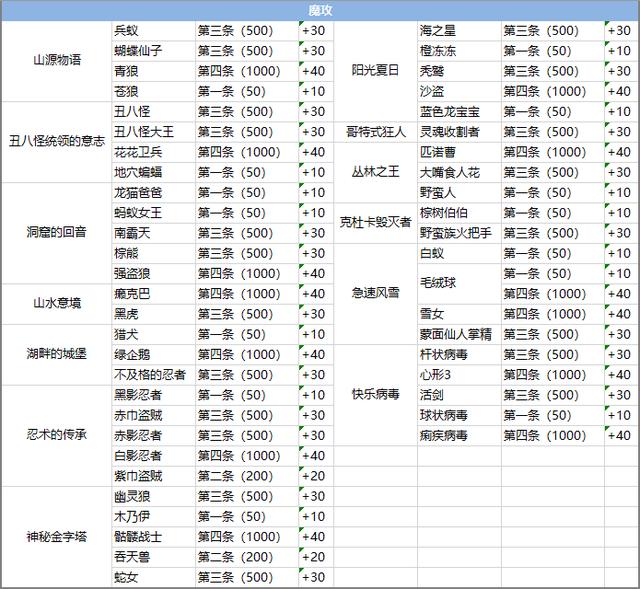昨夜,下了场透雨。雨过日出,干旱的土地足足地喝饱了水,原野上散发着清新、潮湿的泥土气息。山上山下绿油油的。草叶和树枝上挂满了颗颗水珠,被阳光一照,宛如串串银珠,闪闪发光。也许,这便是我的一生中只有在江永菜鸟看到最美的景象了。这种真正的动人的自然之美,常使我不有自主地像孩子一般淌下泪来。
这种天气,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吃过早饭,人们惊奇地听到,队长扯着嗓子喊出工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去打野猪喽!去打野猪喽!”于是,全村人脸上的表情,都被队长的决定,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嘴巴都快咧到耳朵上。那时,白天出工要“政治挂帅”,晚上开会讲“阶级斗争。”作为人,已经完完全全被一种政治高压剥夺了自由。那么,今天队长善解人意,大家是没有理由不高兴的。
男人们把闲置了很久的铁铳拿出来,用布擦了又擦,往里面装填铁沙火药。女人们忙着为男人准备午饭,心里默默地祈祷丈夫今天能打“头炮”。
大家在村头集合出发,于是,一支背着土枪土铳,衣着各
异散兵游勇的队伍,在范星的率领下往大山里走去。对我的前后,奔跑着十来条清瘦凶悍的赶山狗。我没有枪背,拿了两根牛绳,背根杂木棍跟在队伍后面,我的任务是抬野猪。

队伍来到一座宛如一个馒头的山下,这样的山,边沿没有与大山接壤,四周是大片开阔地,种满高粱红薯等旱土作物,如果断定山上有野猪,猎手们可以隔三五十步将山团团围住。
打野猪范星是寻脚印的专家。平常他个子小不起眼,可是打野猪,大家都得听他的。他在山上跑起来比狗快,爬起树来比猴快,他还可以从这棵树跃到另一棵树上。山里人除了会种地外,往往还身怀绝技,仅就打猎而言,同是神枪手,有的就善打飞的野鸡,有的就善打跑的兔子。年长一点的,几乎都有一门奇才异能。
提起打野猪,山里人个个摩拳擦掌。兴奋的原因是能够同仇敌忾地举起枪去消灭公认的害兽。平常,野猪夜出掘食农作物,它们的破坏力可以使大片土地颗粒无收,而且来无影去无踪,如果不靠群力围杀,个人只能扼腕兴叹。
在潮湿的土地上,野猪的活动都会留下鲜明的脚印,范星根据脚印,能判断出是公猪还是母猪,是一条还是数条。然后沿着脚印,带着经过训练的赶山狗跟踪,直到发现野猪,用狗围攻野猪,把野猪从山上赶下来,进入猎手们的射程。
范星和猎手们沿着山边熏野猪脚印去了。突然有人惊呼:“是从这里上山的!”范星确认后,便对大家说:“赶快选高位站好,有四条野猪。”说完,范星带着狗上山去了。这座山,是经过封山育林而成的天然次生林,在人的保护下,这里成了飞禽走兽的乐园。
范星手举利刀,一边沿着脚印挥刀开路前进,一边打着唿哨喔嗬,十来条狗用鼻子嗅着地面汪汪叫着。人喊声,犬叫声,使寂静的山林顿时笼罩着一片少有的恐怖。林中惊鸟四飞,野鸡野兔没命地奔逃。
突然,范星发现了野猪。前面不远,四条野猪立定着,竖着长耳,张着巨嘴,露出巨牙,满口白沫,嘶嘶吼叫。范星用食指和拇指在口中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唆使所有的狗向野猪发起进攻。野猪性凶暴,面对狗的进攻,黑乎乎地像重型坦克一样向狗猛冲过来。前面的几条狗后退着向两旁闪开,后面的几条狗又猛扑上去,咬野猪的屁股和尾巴,野猪掉头顾脚,前面的狗又跳跃着猛扑上去,就这样反反复复,野猪在狗的轮番攻击下,累得呲牙咧嘴,呼呼喘粗气。狗却越叫越凶,越战越勇。瞧!一条野猪的尾巴给狗咬断了一截!这时,范星从怀里拿出一面小铜锣,使劲镗、镗、镗地敲起来,给狗助威。野猪听见锣声便开始奔逃。那条背面混生着白毛的野猪,被一群黑色的狗追赶得没命地朝山下奔跑过去。砰!一声巨响,野猪被牛崽打了“头炮”,我和牛崽站在一起,受了伤的野猪呼呼地向我们冲过来,我没有枪,手中拿根抬野猪的杂木棒,正憋着一肚子窝囊气没处发泄。危急之中,便使出吃奶之力冲上去朝那家伙当头一棒,嗬!那根杂木棒被我打断飞出一截。没想到那家伙重重挨了一棒后直起后蹄,向我扑来,我就势侧身一蹲才避开了它的獠牙。我的乖乖,差点被它咬了一口!这时,牛崽由装好了火药,大声喊道:“广生快跑!快跑!”待我跑开,牛崽又对准它的头“砰”地补了一枪,那家伙才倒地。我又转回身去,用手中那半截木棒使劲猛打猪头。一边打一边恶狠狠地用江永粗痞话骂,似乎打了不骂还不解恨。牛崽吓得哆哆嗦嗦地对我说:“广生,你怎么那样猛呢?受了伤的野猪比老虎更凶,如果被它獠牙一咬,人身上的肉都会被整块撕下来。”此时我脸色苍白,吓出了一身冷汗。
狗还在山上狂叫着,范星还在打着唿哨喔嗬,敲着铜锣。“嗬……嗬……嗬,镗……镗……镗,从这边下来了!从这边下来了!”猎手们都奔跑过去,又一条野猪像滚木檑石俯冲下来 。砰!砰!砰几杆铁铳同时开火,野猪当场被打死。其余两条,突出重围看着跑进大山李去了。
吃午饭时,大家都夸我够胆,不怕死,是个好样的。我用牛绳把两头野猪捆好,我和牛崽抬着他打“头炮”的那条大的,另外两人抬着那条小一点的,在回家的路上,这支散兵游勇的队伍,仿佛不是打了两头野猪,而是攻下了两座城池。人人都兴犹未尽 人人都在讲味道,人人都俨然成了英雄。抬着两条野猪进村 全村都沸腾起来了。按当地习俗,范星和牛崽不但成了英雄,而且还发了大财。范星寻脚印,两条野猪的脚从关节处割下来全归他。牛崽打“头炮”,把猪耳朵往后拉,用刀在耳尖部分割下来全归他。其余参与者,人人一份。内脏按参与的狗分,每条狗一份。女人们忙着烧火蒸酒,男人们忙着净毛,煮肉。村子里像过年一样欢乐。
牛崽分的那颗猪头重二三十斤,他请我吃饭,大块的野猪肉质虽然很粗糙,还略带泥味,多香啊!好久都没有这么享受了。我不胜酒力,盛情难却也喝下了两杯。月光朦胧,我迈着醉后的步履 想到野猪肉同样给久违了荤腥的妻子和孩子带来的欢乐。一切像蛇一样地缠绕在我们身上那么多的规矩、限制、禁锢、忌讳、恐惧、条条框框、流言蜚语都忘却得干干净净。我哼着曲儿,陶醉在美好的遐想中往家里走去,高一脚,低一脚,摇摇晃晃,跌跌爬爬,今夜,我好快活。
第二天,牛崽耳语告诉我:昨夜吃了野猪肉,来了精神,他和婆娘幸福了一次。他问:“你呢?”我点了点头。的确,借着吃了野猪肉后的“野”性,我和妻幸福地“野”了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