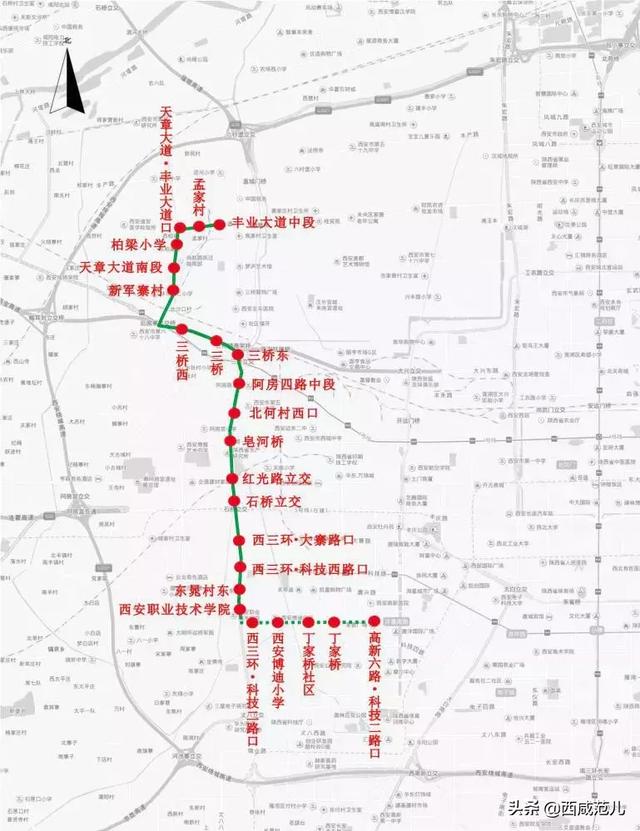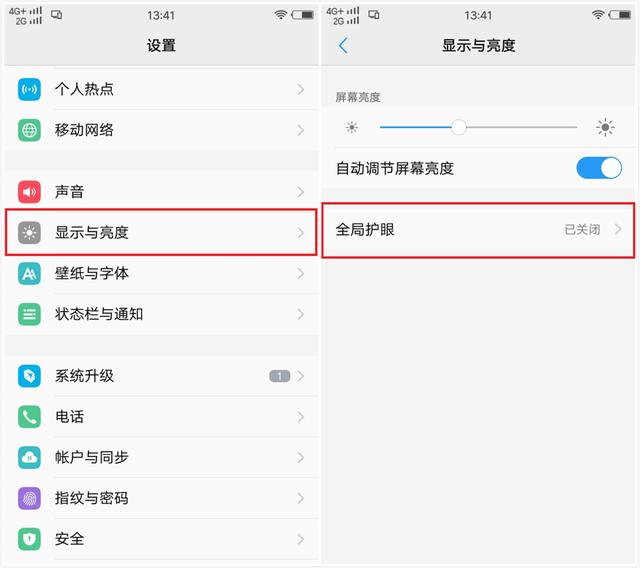原创 邓自华 刑事法譚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01问题由来
在当下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常能遇到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收受其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财物,但没有实际(承诺)为该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谋取利益的情形。对于该类案件的处理,实践中多援引2016年4月18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规定,以上述所称情形属于“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对该起事实成立受贿罪。即便是上述行为发生在2016年4月18日司法解释生效之前,也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1条、第2条规定,因司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法律施行期间,且在2016年4月18日司法解释生效之前,对“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没有司法解释予以规定,故《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适用于该司法解释生效之前的行为。
但是,不同意见认为,在《贪污贿赂解释》生效之前,对于“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1月13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中已有规定,即“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所规定情形,未被规定在《会议纪要》之中。上述《会议纪要》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且在实践中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实质上相当于司法解释,在其与《贪污贿赂解释》规定不同时,应当根据《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3条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02争议焦点
根据第一部分所述可以看出,对于这一问题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对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司法解释规定存在不同时,能否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03法理分析
刑法作为基本法律,在面临新旧法更迭时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以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被明确规定在《刑法》第12条之中。司法解释作为最高司法机关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在新旧规定存在冲突时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也已被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3条之中。
据此,主流观点及实务中的普遍做法认为,《会议纪要》仅系最高司法机关印发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虽同属刑法的法律渊源,但其在法理意义和规范意义上均不属于“司法解释”。对于“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在“司法解释”这一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只有《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予以了规定,因此依照《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1条、第2条、第3条规定,该种情形不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的前提,应当认为《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规定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在实质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对于在2016年4月18日之前,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收受其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财物,但没有实际(承诺)为该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谋取利益的情形,不能依据《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规定认定“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刑法看实质”是在对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虽然从法理和规范意义上而言,《会议纪要》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但就我国当下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而言,《会议纪要》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针对若干具体法律适用问题的细化规定,在实践中具有普遍的强制适用效力,在实质上显然具有“司法解释”的作用。如果按照主流观点,在定罪时,《会议纪要》可以被作为实质的追诉和裁判依据,在出罪时,又否认其“司法解释”的地位,这显然对被追诉人是不公平的。因此,从实质意义上而言,《会议纪要》已经具有“司法解释”的功能和地位,在其与《贪污贿赂解释》有关条款规定不一致的,理应可以将其解释为《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3条中所称的“司法解释”,从而适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其次,《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4条规定,“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如果不承认《会议纪要》实质上的“司法解释”地位,则对于2016年4月18日《贪污贿赂解释》生效之前已经处理完毕(未按照犯罪处理)的类似案件,也应以法律适用有误为由予以再审。原因在于,按照主流观点,《会议纪要》并非司法解释,《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对于“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不仅适用于2016年4月18日该解释生效之后,同样适用于刑法生效之后、该解释生效之前的期间。因此对于刑法生效之后、该解释生效之前未按照《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二款处理的案件,均应认定存在法律适用错误。这一逻辑推演下的结论显然是较为荒唐的。
再次,我们注意到,由最高人民法院王尚明、柳杨两位同志在《操纵期货市场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一文(刊载于《人民司法(案例)》2022年第8期,第8-10页)中提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证券期货案件解释》)的追诉、定罪规定存在不同时,应当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该文中论述称:《立案追诉标准(二)》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但它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也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参照适用,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当二者的规定存在冲突时,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其法理基础除了保障人权、有利于被告人外,还包括“不知不为罪”、“处理同时期发生的行为应用同样处理标准”等正义观念。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上述论述,也支持将最高司法机关针对具体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视为实质上的“司法解释”,当其与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不同时,按照“从轻兼从轻”的原则予以适用。
最后,在探讨法理之前,我们应当承认的事实上,尽管刑法学者将法律渊源分为法律、司法解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等,但对于社会一般公众而言,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会议纪要》中仅规定了“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仍收受财物”的,属于“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行为,但没有规定“收受无具体请托事项但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对象3万元以上”的行为也属于“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行为。因此,在2016年4月18日之前,社会一般公众也有理由认为,只有在“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仍收受财物”的情形下,才能被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如果以后生效之《贪污贿赂解释》而规制此前的行为,会破坏法(司法解释之下的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所具有的指引和教育作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罪刑法定的原则。
因此,对于文章开篇所提到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肯定《会议纪要》具有实质意义上司法解释功能和地位的基础之上,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于2016年4月18日之前,国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收受无具体请托事项但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对象3万元以上”的行为,不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而阻却相关事实受贿罪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