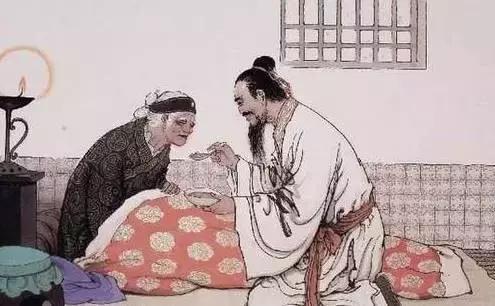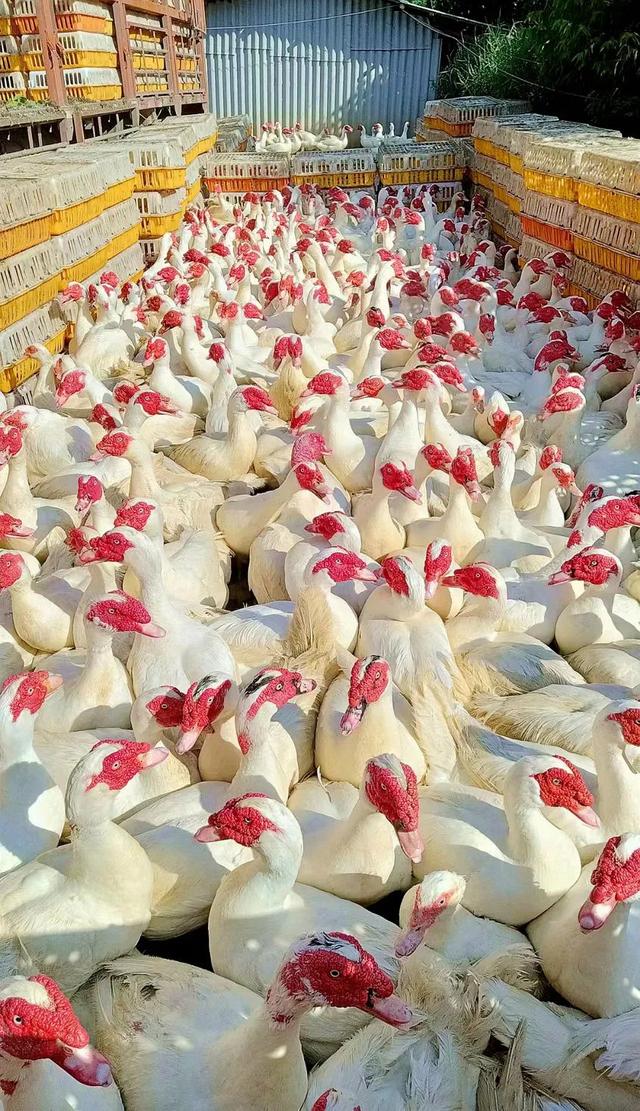建国后,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变了,由“说相声的生意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可这些“文艺工作者”呢,还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里边夹杂着不少的侮辱劳动人民、羡慕富贵权势的内容,演出中陈旧低俗的气味浓重,演员呢,口沫横飞、五官挪位,这个江湖气也没有改变,社会舆论呢,也不断的批评相声低级庸俗,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相声就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那时候,谢纯一呀,在《我对于“相声”前途的展望》一文中,是这么说的:“由于各个段子的胡说八道,相沿的相声流品日下,多半是演员们为迎合一般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于是形成了撒村、骂大街,父子玩笑,甚至于祖宗奶奶胡骂一气,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成了社会上的垢病,倘若有人说‘听相声去!’就有人批评他‘低级’,尤其是演员们自己还常说‘相声啊就是无招对的瞎话儿’。有个学校里头对学生有过禁听相声的告诫, 那时候相声这门玩意儿,简直成了洪水猛兽了,是我本人原是曲词编作者,可是我也瞧不起相声。”
下面呢我再读读我师哥于世德在回忆录《我这半辈子》中提到刚建国的时候,相声演员出丑的情况:
“一次,演唱“拆唱八角鼓”的两位演员在白纸坊印刷厂礼堂,”这是北京,白纸坊是个地名,“演出前使用相声 “垫话”《反正话》垫场,用谩骂博取笑料。如: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等,”我在这儿再解释一下,这是传统相声《反正话》的老底,“西游记”,这一点儿,应该是前边的原词儿是这样的:“——我看西游——我西游看——我唐三藏——我藏唐三——我沙和尚——我和尚沙——我猪八戒——我戒八猪——我孙猴子——我猴孙子。”底下是“瞧西汉”,张良、韩信,最后是楚霸王。那个时代说这个,都出丑了,你怎么还说呀?我要不说怕您笑话,笑话我不会啊,“王八杵”后边儿还有啦!这可不能说了。你怎么不怕笑话了?爱怎么笑话怎么笑话吧。咱们接着说这个怎么出丑,“结果被观众轰下台去。自轻自贱,咎由自取。”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可笑,可在当时,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这回事儿,在回忆录中还描写了一九四九年末相声受指责的情况:
“十一月的某天,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在散会做小结说:“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鼓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捧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演员认为她是政府干部,是代表政府的,这个“唉”声对大家震动很大。摆脱危机,推陈出新,是相声的唯一出路。”
面对这上述的情况,演员的情绪也低落了,对自己的艺术也失去信心了,有的人甚至于要改行,也有一部分演员不甘心,他们参加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开办的北京市戏曲演员讲习班,通过学习那些有觉悟的相声演员,有了以相声为社会服务的信心,其实解放前哪,也有创作、改编和积极因素,相声的传统从穷不怕、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张杰尧,到常宝堃、侯宝林,都搞过,只是在解放前没有正确方向,也没组织起来,为了彻底改变相声被冷落的这个状况,他们从一九四九年冬季开始酝酿,把这个相声演员组织起来,成立改进相声的团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著名的作家老舍由美国回到北京,相声演员侯一尘、侯宝林得知,马上到他居住的北京饭店找他,他们知道老舍熟悉民间的说唱艺术,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还自己创作过、表演过抗日相声,这几位也深信,老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出主意,改变相声的现状,老舍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答应他们改编传统相声。
老舍呢,就是作家舒庆春的笔名,北京市人,满族正红旗,著名的作品有《骆驼祥子》、《茶馆》、《月牙儿》、《方珍珠》、《鼓书艺人》等经典之作,五十年代晚期他曾给我老师张寿臣先生寄过信,先生对于他的作品中老有说相声的有误解,所以没回信,老师呢跟我提到过这个事情,当时我对于老舍也不太了解,只是在文化局安排下跟老舍先生见过一回面儿,后来我看的资料多了,我了解老舍先生对相声这门艺术他是非常喜欢,同时他的作品也融进了相声的因素,像《茶馆》,王掌柜跟唐铁嘴有一点儿对话,就是说相声的东西,算卦的唐铁嘴说:“我最近呐,把大烟戒了。”大烟就是鸦片烟哪,王掌柜说“您长出息了!”这唐铁嘴儿说“我改白面儿了。”这一铺一垫,整是相声东西,白面儿就是海洛因哪,白粉。完全是相声,后边呢,唐铁嘴坐下了,说“您瞅见没有王掌柜?英国人的烟卷儿,一蹾空大半截,正好装日本人的白面儿,您瞧,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儿”就这段台词,帝国主义用毒品掠夺中国人的财富、残害中国人,唐铁嘴呢还引以自豪,这个自嘲的包袱儿揭示了列强的侵略、掠夺和唐铁嘴那样的人的愚昧、无知、没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心理,这个包袱儿是苦涩的包袱儿,比相声包袱儿深刻多了。打住,咱们接着还说老舍。
老舍先生答应了,改编传统相声,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一文中,描写了他们访问老舍先生的情况,关于介绍北京市相声改进小组的过程呢,我引用了王决等几位同志撰写的《中国相声》[注]的第三编第一章,就是“1949年到1956年”,第一节。
[注]书名应为“中国相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