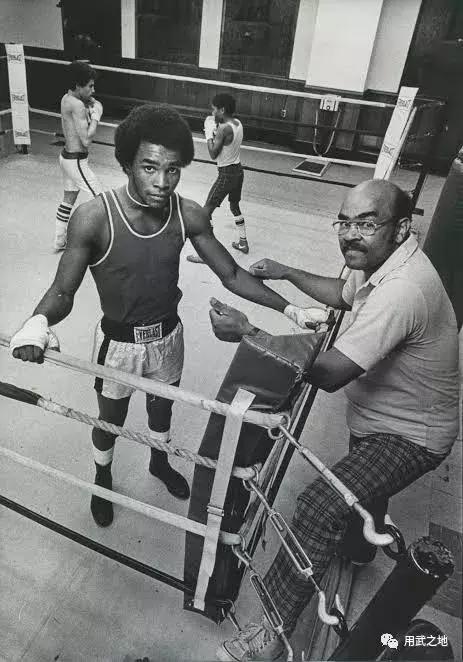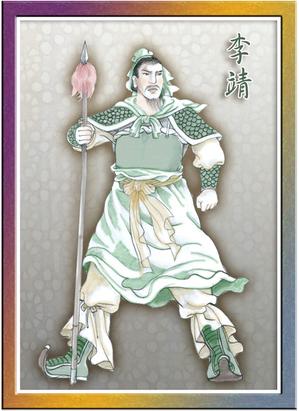□ 周华诚
1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居然会回到稻田里来。我只想离开它。
暑假里,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知了在树上叫得有气无力,听起来像是被热晕了。门外的阳光白花花的,能刺伤人的眼睛。我们穿上硬朗厚实的长袖工服,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走向我们家的水稻田。
田里有一大堆农活在等待着我们。首先要把成熟的早稻收割完。收割稻子是令人感到疲惫不堪的事情,别的不说,单是踩着打稻机脱粒,就要耗费所有的力气与汗水。更别说稻谷的细芒粘在身上,让人浑身上下都觉得痒痒。等到早稻收割完,又要赶着在一个星期内翻耕土地。耕田佬赶着牛来了,人和牛密切合作,把一块稻田的土地都翻了过来,整块的泥巴被翻转、切碎、揉细、搅匀,直到整块田畈变成一锅稠粥。我们疲累的筋骨还没有得到舒缓,就要立即回到水稻田了,因为还要插秧。一棵一棵,一棵一棵,一行一行,一行一行。我们要把那小小的水稻秧苗,插遍整块水稻田,直到整片水稻田被小小的绿色全部铺满。

这是十多岁的我,每一个暑假里都要经历的故事。跟村庄里别的孩子们一样,我无比讨厌稻田,也无比讨厌暑假。
我想,要是没有暑假就好了。
我也想,要是没有水稻田就好了。
我们的小学校,就在三里路外,一条河的那一边。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要从广阔的田野中间穿过。春天闻着油菜花的香,夏天看着水稻生长,秋天听见稻浪翻滚,冬天看见田野被白雪覆盖。这就是我们的村庄啊,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
母亲说,你们啊,要好好念书。好好念书,长大后就不用再种田了。
于是我们不再吭声,只是埋着头,一笔一画地写作业。作业本上的字,写得格外工整。

2
后来我考上了大城市的学校,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嗯,终于不用再种田了!
当我又一次回到村庄的时候,我却发现,我们的村庄正在变得陌生,变得连我们自己都不太认识了。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牧童遥指杏花村”“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我们小时候念唐诗宋词,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的农村,是我们江南的农村。
但是现在,这些情景好像都见不到了。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回到村庄里,发现整个村庄都找不到一头牛了。以前每到春天,人和牛一起,在田野里劳动。如今不仅牛消失了,人也渐渐消失了。田野里见不到人影,大家都进城打工去了。
如果还有人在继续种田,就算是能种出很好吃的萝卜、青菜或大米,他也不会觉得骄傲。

我决心回来种田,跟着父亲一起种田。
跟我一起回来种田的,还有几十位城市的朋友们。我发起了一个文创项目“父亲的水稻田”,邀请城市人回到土地,跟我一起劳动,一起收获。
我没有想到,这个活动居然那么受欢迎。水稻田里的那些农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城市里的大人,也都没有体验过。他们站在水稻田里,站在土地上时,脸上全是开心的笑容。
我们的大米卖到三十元一斤,后来卖到五十元一斤,还供不应求。因为只有预订了大米的人,才能有资格跟我们一起来种田。
当然,我们一起来种田是充满乐趣的事,劳动之余,大家还在稻田里办起了摄影展、绘画比赛、油画展;我们在稻田里一边收割稻谷,一边共同完成一件叫作《TIME》的艺术作品;我们还把各自的体验,用文字写下来,刊登在报纸上,出版一本又一本的书。
这些年轻的种田人,在没有农事的时候,还一起结伴旅行。我们去沙漠,去野营,甚至一起去日本,到人家的水稻田里去参加稻谷收割,还去参观人家的艺术展。
水稻田不仅仅只是纯体力劳动,我们在这里还体验到了精神的审美,享受到了劳动的快乐,更享受到了创造的乐趣。

3
每一件看起来简单的事,其实都不那么简单。
要把一件事情做好,需要刻苦钻研的精神和踏踏实实的作风。有一次,我去中国水稻研究所位于海南陵水的南繁基地,采访一位搞水稻育种研究的科学家沈博士。沈博士一年有两百多天,都在水稻田里。他为了培育出好吃的“长粒粳”大米,数十年如一日,埋头做育种研究。
另一位水稻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钱前,也带着几位同行来到我们的水稻田,和我父亲亲切地握手,肩并肩站在一起。钱院士的团队,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他们鉴定了一个水稻突变体,这个突变体,跟水稻的花有关——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观察过水稻的花?我们在古诗里读到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其实每一朵水稻的花,会结出一粒稻谷。想想看,我们手中的一碗饭,有多少朵稻花?

一株水稻有多少穗数,每穗能结多少粒谷子,每粒谷子重量多少,是考察水稻产量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每个穗上,有多少朵稻花,就决定了每穗能结出多少果实。正常的水稻,每个小穗由两对颖片、一朵可育小花构成。这些术语,是不是太专业了?好吧,简单说,钱老师的团队,就在那朵小花之外,发现突变体的小穗还能在护颖内发育出另一朵完整的小花,并且,结出了正常的种子。可以说,这个研究为水稻高产分子设计育种,奠定了基础。
我的父亲,是中国最基层村庄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几十年种着水稻,却并不懂得水稻背后的科学奥秘。他也不知道,有那么多顶尖的科学家,都在为着一口粮食孜孜不倦地工作。
现在,父亲与中国水稻界这些顶尖的专家们站在一起,他的脸上,也绽放出自豪的笑容。

4
现在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傍晚回到水稻田,在那里看夕阳一点一点落下去,红蜻蜓在稻田上空飞舞,一颗一颗晶莹剔透的露珠,悄悄爬上水稻的叶尖。
我把这些细微的感受,都写进了文章里。
对我来说,我现在有两块水稻田,一块在土地上,一块在人心里。
写作,就是我耕种人心里的那块水稻田。
我现在也觉得,码字跟种田,真是没有太大不同,都是面对大片的荒芜与空白,耐耐心心地一棵一棵地种下去,经历漫长的重复的劳作,然后一粒一粒地收回来。我还觉得,任何一种劳动,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因为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做出成就,做出自豪感来。

在这个年代,依然有很多“笨拙”的劳动者。比如,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时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一万个竹篮。一个农民,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一个水稻科学家,埋头在那些水稻中间,悄悄地,头发白了,背也弯了。
是啊,不管时光如何变换,他们依然是最美的劳动者。现在,我要大声为他们唱颂歌,表达内心最真挚的赞美。
现在,我们也成了他们中的一个。
每一次回到水稻田,站在水稻中间的时候,我内心很踏实,也很宁静。尽管眼前的水稻被大水淹,被日头晒,被虫子吃,也遇到病害,但是一季一季,水稻们都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成熟。我一次次来到水稻田,就一次次地想起那些为数不多的,还留在田里耕作的农民,我觉得或许他们才是对的。
是的,这世上总有些事,是留给“笨拙”的人。如同水稻的生长,缓慢却执拗。
站在田埂上,吹着田野上的风,我觉得自己仿佛重新回到了十几岁。田埂上站着一个乡村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