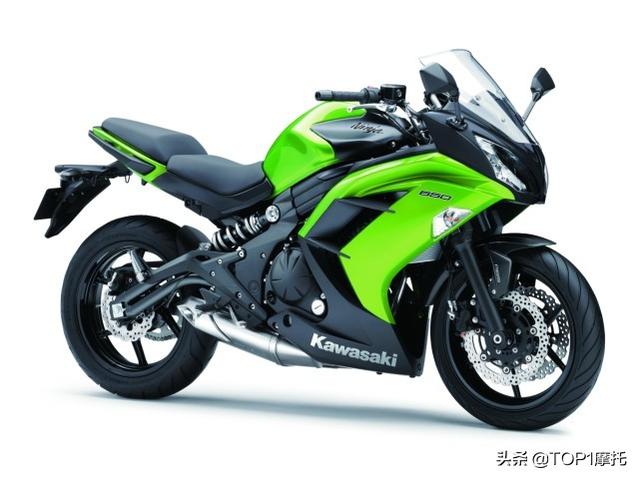这里所称的自力救济行为( 或私力救济行为) ,[有学者区分私力救济与自力救济 ( 参见贺海仁: 《自我救济的权利》,载 《法学研究》2005 年第 4期,第 63 页以下) ,本文未作区分]不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而是泛指原本应当通过公权力阻止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公权力行使的缺失,权利人利用私力阻止违法犯罪,保护合法权益( 包括使遭受损害的权利人获得赔偿等) 的一切行为,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驾驶交通工具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驾驶交通工具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这里所称的自力救济行为( 或私力救济行为) ,[有学者区分私力救济与自力救济 ( 参见贺海仁: 《自我救济的权利》,载 《法学研究》2005 年第 4期,第 63 页以下) ,本文未作区分。]不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而是泛指原本应当通过公权力阻止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公权力行使的缺失,权利人利用私力阻止违法犯罪,保护合法权益( 包括使遭受损害的权利人获得赔偿等) 的一切行为。
例一: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县政府规定每个镇只能依法设立一个屠宰厂。甲经过批准依法在县城和各镇设立屠宰厂。乙、丙没有经过批准,便在几个镇私设屠宰厂,出售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要求乙、丙拆除屠宰厂,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
例二: 甲依法取得了从县城至某镇的客运许可,合法从事客运业务。乙、丙没有取得客运许可,却在该线路上违法从事客运业务。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迫使乙、丙停止非法客运业务,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
例三: 甲在某地取得了采矿权并依法采矿,但附近农民乙、丙等人经常在甲合法取得的矿区内偷偷采矿。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也包括要求乙、丙赔偿损失的行为。
例四: 甲依法从事拆迁业务,乙、丙在签署拆迁协议、获得应有补偿款、拿到补偿住房的钥匙之后,仍然不搬迁。甲组织多人对乙、丙实施恐吓、殴打等行为,要求其搬迁。例五: 乙、丙等人开设的回民饮食店出卖猪肉食品,引起回民的抗议。宗教管理局没有人力查处所有饮食店的不法行为,于是委托甲等人( 如宗教协会的退休人员) 负责查处。甲等人发现乙、丙的回民饮食店出售猪肉食品后,便予以阻止,并按相关规定“罚款”,其中部分用于发放劳务补贴,部分上交有关主管机关。
上述行为都没有构成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与故意毁坏财物等罪,正因为如此,有的司法机关就对上述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一个重要理由是,乙、丙的违法犯罪行为只能由国家机关处理,个人擅自处理就是违法犯罪。其实,正是因为国家机关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处理甚至要求权利人自行处理,行为人才实施相应的维权行为。本文认为,对上述甲的行为都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从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来说,上述案件虽然都有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但这些行为都不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理由: 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这里所称的扰乱公共秩序,是指侵害作为社会法益的公共秩序的情形,不包括侵害国家法益的情形。例如,妨害公务罪虽然被规定在 “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但实际上属于对国家法益的犯罪。)都必然使不特定的无辜者产生恐惧感( 对自己安全的担心) ,甚至使无辜者直接或者间接遭受各种侵害。
例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行为,必然对正常从事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的众多无辜者的相关正当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又如,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必然使公共场合的诸多无辜者的身体活动自由受到侵害。再如,聚众斗殴罪的行为,会使周围的无辜者产生恐惧感,甚至直接或者间接侵害周围无辜者的身体活动自由。概言之,犯罪行为因为直接或者间接针对不特定的众多无辜者,才具备扰乱公共秩序的性质。
可是,上述自力救济行为,都是在特定场所针对特定的人员,而且针对的是正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人员。上述行为不仅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相反维护了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利益。如例一中甲的行为,明显有利于保障公民的食品安全; 例二中甲的行为,明显维护了客运管理秩序与乘客的生命、身体安全。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再如,例三中甲的行为,明显保护了国有矿产资源和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可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上述列举的各例中的行为,都没有直接或间接侵害无辜者的利益,不仅不会让无辜者产生恐惧感,而且反而增加了大众的安全感,故不可能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诚然,部分案例中会出现行为人向相对方“罚款”或者要求对方赔偿的事实。但是,这样的行为同样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可能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一方面,如前所述,《解释》对寻衅滋事罪规定了特定的主观要素,即“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但上述各例中的甲都不具备这样的主观要素,相反,都是出于合理的动机与目的。
另一方面,成立敲诈勒索罪要求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即目的具有不正当性。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属于行使权利,则表明其目的具有正当性,因而不可能成立敲诈勒索罪。(参见 [日] 松原芳博: 《刑法各论》,日本评论社 2016 年版,第 303 页以下。)合法采矿人要求偷采矿石的人赔偿损失,完全是行使权利的行为。受委托向违规的饮食品“罚款”虽然可能存在不当之处,但不当之处源于有关国家机关的授权,而不是源于受托人本身。将“罚款”部分用于发放劳务补贴,部分上交有关主管机关,也表明其目的具有正当性。
即使退一步认为,上述各例中的甲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也应当认为其行为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其中,有的存在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有的存在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
例如,取得了采矿权的行为人,发现没有取得采矿权的人正在非法采矿时,予以暴力手段制止,没有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当然属于正当防卫。因为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条件。或许有人认为,非法采矿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利益,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不能进行正当防卫。诚然,这一观点作为立法论是可能的,但在解释论上,则不能否认公民为了国家利益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换言之,在《刑法》第20 条明文规定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正当防卫的前提下,将为了国家利益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明显违反刑法规定。(张明楷: 《正当防卫的原理及其运用———对二元论的批判性考察》,载 《环球法律评论》2018 年第 2 期,第 51 页以下。)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因为相对方进入行为人享有采矿权的矿区进行采矿,权利人才实施防卫行为。所以,即使退一步认为只能为了保护个人法益进行正当防卫,由于非法采矿行为侵害了行为人的个人法益,行为人的行为也是正当防卫。
再如,行为人通过竞拍取得了某河道采砂权后,成立了采砂公司,为了防止他人偷砂,公司成立稽查大队,稽查人员在河段进行巡查,发现他人私自采砂后,采取拦截、威胁、扣留车辆等手段,要求他人缴纳“罚款”。这样的行为部分成立正当防卫,部分则并不一定成立正当防卫,(如所谓的 “罚款”行为显然不是正当防卫行为。) 但即使不成立正当防卫,也是一种自力救济行为。
( 1) 权利人的利益遭受了侵害。( 2) 权利人的利益难以由国家机关保护,在许多情形下国家机关往往要求权利人自行处理。( 3) 通过拦截、威胁、扣留车辆等手段,要求偷砂者缴纳“罚款”,只不过是挽回自己损失的必要手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罚款。如果不采取上述手段,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就不能得到补偿。(特别要说明的是,既然行为人合法取得了河道的采砂权,就不能将行为人的采砂行为及禁止他人采砂的行为评价为 “非法垄断采砂行业”,否则,就是颠倒黑白的评价。)( 4) 权利人的行为并没有超越必要的限度,只是挽回了自己的损失或者防止相对方进一步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上述行为完全符合自力救济的成立条件。(关于自救行为的成立条件,参 见 张 明 楷: 《外 国 刑 法 纲 要》 ( 第 三 版) ,法 律 出 版 社 2020 年 版,第 160 - 161 页。)
诚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自力救济行为,但这并不妨碍自力救济成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广义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不仅包括正当化事由,而且包括阻却可罚的违法性的事由。(参见 [日] 山口厚: 《刑法总论》( 第 3 版) ,有斐阁 2016 年版,第 184 页以下。)
其一,从民法规定来说。在许多国家,自力救济都是民法明文认可的阻却违法的行为。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 “出于自助之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出于自助之目的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容忍义务之行为进行抵抗者,因不及官署援助,且非即时处理则请求权有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有困难时,其行为非违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 条第1 款前段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
据此,上述阻止、扣留非法采砂者的车辆等行为,完全符合这一规定。再如,《民法典》第184 条规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既然如此,从违法层面来说,紧急救助行为给违法犯罪造成损害的,救助人更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从责任层面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可能承担民事责任。
其二,从刑法规定来说。虽然刑法没有规定自力救济行为,但只要不采取早已被抛弃的形式的违法性论,(形式的违法性论只承认刑法明文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而不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就会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从实质上说,自力救济行为所针对的是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的是合法权益,所以不具备实质的违法性。
从形式上说,自力救济虽然不符合刑法明文的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但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不仅如此,正当防卫不以国家机关不能救助为前提,而自力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不及由国家机关救助或者国家机关没有救助; 正当防卫通常造成不法侵害者伤亡,而自救行为只是挽回权利人的损失,并没有给违法犯罪人造成伤亡与财产损失; 此外,上述列举的自救行为都是在相对方正在实施违法罪行为时实施的。既然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就不能不承认自力救济是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换言之,既然在相对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时,采取造成其伤亡的手段制止不法侵害、维护合法权益的是正当防卫,就不能认为在相对方正在实施不法侵害时,采用更为缓和的手段制止不法侵害、挽回权利人损失的行为反而是犯罪行为。
“许多法社会学实证研究表明,私力救济在现代一直受到国家的压制,但是其仍然在各种场合存在,甚至非常活跃。实际上,从现代以来的社会纠纷解决实践的角度看,法治社会在法律强制性规定界限和责任都非常清晰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私法自治范围内,并不一概排斥私力救济的存在。在所谓‘回应型国家’,私力救济的优先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范愉: 《私力救济考》,载 《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88 页。) 在行为人制止不法侵害的同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不管所使用的是什么概念,都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其三,即使有些救助行为看似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超过了救济限度,也可能阻却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与有责性。
一方面,在对自力救济行为进行法益衡量时,就会发现其行为造成的法益损害没有达到可罚的程度。这是因为,自力救济行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相对方存在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由于救济者的利益优越于相对方的利益,所以,认定不当的自力救济行为构成犯罪的实质条件应当更为严格。不仅如此,在认定自力救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不能将全部结果归属于维权行为人,必须将相对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排除在行为人的负责范围之外。
例如,2020 年1 月4 日,一辆停在停车位内的田越野车,被横着停在前面的一辆捷豹SUV 挡住出路,丰田车车主杨女士当时急着要回去,发现捷豹车上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打了114 提醒对方挪车,等了十几分钟车主也不来。于是,杨女士先后11次倒车撞击捷豹的侧面,直到将捷豹撞开后驶离了现场。“从交警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停车位前车辆横停,停车位里的车辆是很难开出来的,一些车身较短的小轿车也许多打几把方向能勉强开出来,但涉事的丰田越野车比较宽大,确实是开不出来。”“民警说,由于事情的发生地是封闭停车场,不属于交警管辖范围,从视频中看到,捷豹车停放的位置,还横着停着一排汽车,但其实这里是通道,不允许停车。”“民警说,杨女士的行为属于故意损毁他人财物,目前正在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捷豹车辆的车损进行鉴定,如果车损达到5000 元人民币以上,杨女士可能因故意损毁他人财物被刑事拘留。”(蒋大伟、赵鎏杰: 《女司机对着违停捷豹车连撞 11 下开路或被刑拘》,载 《都市快报》2020 年 1月 8 日,第 A01 版。)
但是,其一,如果杨女士确有紧迫的重要利益需要保护,则完全可能是紧急避险,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其二,即使杨女士的行为不具备紧急避险等正当化事由,也不能将全部车损结果归属于杨女士的行为。本文主张,在类似这样的场合,首先要按照民法判断捷豹车主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进而将其承担的责任排除在杨女士应当承担的责任之外。例如,倘若车损总数额为8000 元,但按照民法规定,捷豹车主应当承担40% 的责任,那么,杨女士就仅对4800 元的损失负责,因而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这样处理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有利于避免助长违章停车行为。
另一方面,前述自力救济行为的有责性没有达到可罚的程度。例如,根据《民法典》1177 条第1 款但书的规定,行为人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国家机关授权或者默许行为人采取自力救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行为人请求国家机关处理,不符合生活现实。
其四,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将前述自力救济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必然助长相对方的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原本属于公权力的范围,但是,公权力不是万能的,也不是随时可以行使的。所以,在公权力缺失的情形下,应当由公民行使私权利来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公权力越是有效地普遍行使,自力救济的范围就越窄,卫权,也不需要进行力救济; 反之,如果公权力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有限,就必须尽可能允许公民实施正当防卫、自力救济等行为,从而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如果将公民的正当防卫、自力救济等行为认定为犯罪,就必然助长违法犯罪。所以,在自力救济一方与相对方之间,刑事司法应当注意保护前者,而不是相反。
来源:刑事法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