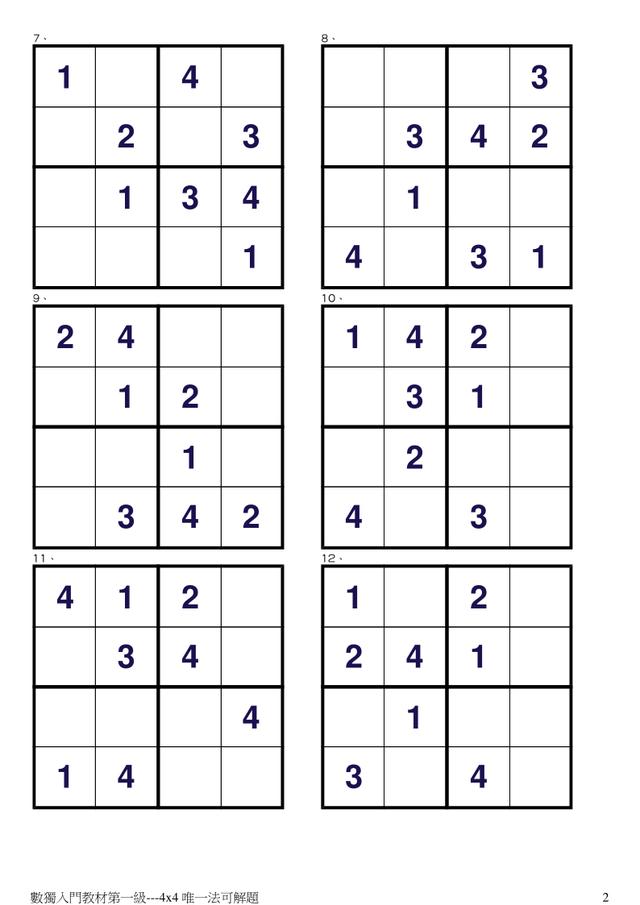那是1977年,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我当时还是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虽然中学毕业都已两年多,功课早忘得差不多了,但由于平时没事时喜欢看个小说什么的,肚子里还算有点货,所以初考统考竟一次次顺利通过了。但没想到的是,大江大河都过去了,却在小沟小汊上遇到了麻烦,体检没过关——我有高血压!
不过还算幸运,那位上了年纪的慈眉善目的医生很同情我,他说我这样瘦的人是不可能有高血压的,就是有的话,也不至于高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他给上面说说看,让我明天再来体检一次。
回到家里,我是不住地哀声又叹气,话不想说,饭也不吃,倒在床上便睡。以为儿子上大学没有问题,逢人便说儿子要上大学的母亲,此时也急得没有了办法。她只是安慰我,说我是太激动了,今晚好好休息休息,明天会好的。
那一晚我似睡非睡,后来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是因为高血压没有考上大学,哭得鼻一把泪一把的,后来竟然哭醒了。而母亲呢,此时正在我的身旁,她这一夜也几乎没睡呢!
一觉醒来,精神更是沮丧,简直不想去参加体检了。母亲这时给我端来了荷包蛋面条,她把饭放到我的面前,很高兴地对我说,她刚才到一个做医生的邻居家去问了一下,听说喝醋可以治高血压,她已经把醋给我买来了,整整一斤,吃完饭,把这一斤醋喝下去,保证没有问题了。
平时我是最怕喝醋的,如今为了上大学,别说让我喝醋,就是此时让我喝下一斤酒去,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不过那醋真是难喝极了,屏住呼吸,一口一口地,硬着头皮,往肚里硬咽。那酸味,直冲脑门,直呛鼻子,直刺喉咙,直反胃,直想呕吐,直喝得我天旋地转,眼冒泪花,双眉紧皱,咧嘴又呲牙。虽然如此,我还是喝得一滴不剩。喝完了,我问母亲还要不要再来一点。母亲接过醋瓶,苦笑着说:“行了,行了,这下保险没问题了。”
这醋到底管不管用,我心里没底,母亲似乎也没多少把握。她又想了想,说:“先跟我到单位的医务室去看一看,有没有降压药可以吃。”
医务室的医生与母亲很熟,她拉过我来先给我量了一下血压。我一看那血压计,心就扑扑跳了起来,好像要跳出胸口似的。她量完了血压,皱着眉,苦笑着打量着我,说:“不可能,不可能。这孩子一定是太激动了。这样吧,吃两片药,保证没问题。”她这一说,我的心又沉重了许多。
服下两片不知名的药片,我独自一人,朝体检站走去。那脚步的沉呀,真如灌铅了一般。而此时我的心情,更是凄凄惨惨戚戚,好像独自一人,去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当我又一次踏进体检室的大门时,当我又一眼看到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医生和他手里的那一副血压计时,我的心又狂跳起来,血往脑门直冲。
量完了血压,老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指了指屋角的席子说:“你先去到那儿坐上一会再说。”我也不敢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心仿佛一下浸在了冰水里,大脑也刹那间成了一片空白。我坐在席子上,眼直直地发呆,而胃里的那斤没起作用的冤枉醋,此时却不住地朝上泛着酸水,我真有点想呕吐了。
这时又来了一个考音乐的。老医生让他给大家唱个歌,轻松轻松。他唱的是他最拿手的歌,《乌苏里船歌》,他就是因为这支歌通过了考试的。他唱得实在美妙动听极了。神奇的北国风光在他宛转嘹亮的歌声里,犹如一幅优美的图画,令人恍入其境。一时间,我竟被他的歌声完全吸引住了。
等他唱完了歌,老医生把我叫了过去。这一次,他没有立即给我量血压,而是先和我拉起了家常。他问我家在哪里,在农村都干些什么活,为什么报考中文专业,喜不喜欢写诗,写诗时激不激动……他像一位老长辈似的,那么温暖,那么体贴,那么平易。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就在闲谈的间隙,他给我量了血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量好了。他轻轻舒了一口气,很平静地说:“没问题了,等着上大学吧!”
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激动,心又扑扑跳了起来。我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是真的吗?”他把写着检验结果的体检单推到我的面前,说:“真的!”
“真的!”我忘乎所以地大叫起来,连声“谢谢”都没说,就欢呼着跑出了体检室,然后又是一路小跑,朝家里奔去,嘴里还哼着那支《乌苏里船歌》的调子。
我觉得那时自己就像一只小燕子,简直可以在天空中轻快地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