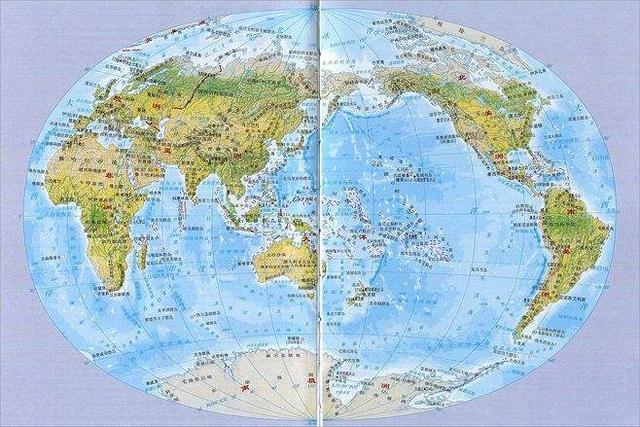再次见到小毛表哥,没想到是在今天的古城西安。这样一种相逢,多少有点意料之外。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儿子,我称为侄子,当然我还没有习惯自己有这么大的侄子,考上了西安的一所二本院校,估计他这辈子也不会来西安。要说原因,似乎是因为没钱,旅游对许多农民来说,不是必需品,算是奢侈品。可说没钱,他其实也挺有钱,每年和表嫂当粉刷匠也能挣个十万八万,但花得少攒得多,这几年在城里陆续为娃买了两套房。
昏暗的路灯下,树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我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肩扛着大蛇皮袋的人走在中间,脑袋紧紧地歪靠着那个大袋子,高扬的双手紧紧抓住袋子两侧,旁边的一位妇女拖着箱子紧随其后,还有一位行李最少的健壮小伙,那显然应该是他儿子。虽然只能看见这样的轮廓,但我已将三人的角色猜得八九不离十。果然,我直奔中间那位,想接过表哥肩膀上的大袋子,却被强力拒绝了。
大袋子装了厚厚的棉被,是属于压在身上能让人喘不过来气的那种。我笑着说,厚被子根本用不上,这里冬天盖一个薄被即可。表哥睁大了眼睛:“我听很多人说,西安冷得人要死。”那一刹那,我反应过来了,没有再接话。我知道,传递给他消息的那些人,都是老家村里在西北做生意的小商贩,他们租住的城中村不一定有暖气。
因为没有去火车站接表哥,我内疚了许久。每当老家来人,我总想努力尽绵薄之力热情招待。偶存怠慢之心,我就给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来的亲戚是达官显贵,自己还会这样吗?”内心时刻告诫自己,不能当一个势利之人,要努力去一碗水端平对待每一位亲朋故旧。只不过,他订的这趟车实在让我发怵,凌晨四点多到西安,我很想去火车站接他们,结果前一天加班,睡得太晚,还是没去车站接成。
午饭我安排的是湘菜,我了解他们,初来乍到北方,面必定是吃不惯的。因为下午上班,吃完饭,我找了一辆越野车送他们去阎良的那所大学报到,走之前,我再三叮嘱司机:“他们第一次去,可能想在大学里逛逛,你就一直等着,把他们带回来。”送去之后没多久,司机打来电话,被表哥打发回来了,说是准备晚上在那住。
表哥是不好意思让别人久等,因为后来他们坐班车回西安,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就返回了。我打电话问他为什么匆匆而别,原本还打算安排他们去兵马俑转一转,表哥用一句万千父母惯用的口径回答了我:“以后有的是机会。”我想,不舍得好好转转的表哥,西安留给他们的记忆,也许只有孩子的大学校门,还有火车站门口那一条长长的古城墙。
之所以对表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源于表哥曾寄宿在我家。父亲是老师,我们住在学校的公寓里,我与他朝夕相处了三年。只记得表哥很勤快,挑水洗碗样样能干,去他的村子里玩,他会带我去钻树洞,村里似乎也没有他“摆不平”的事。
再次见到表哥,总试图去打捞与表哥有关的记忆,却似竹篮打水一般,光留存了一些水迹,没有太多实质性内容。唯一清楚记得表哥是个“武侠迷”,讲起金庸古龙笔下的人物头头是道,教授我一套自编的降龙十八掌,颇有意思。每念一个字就对应一个动作,先是双手相对,左右手上下互换各做一次,尔后两手交叉,再打开成一个八字,最后双掌用力推出,简单易学,动作洒脱,直至现今我仍然能够打出一套来。
金庸笔下的表哥,大多是潇洒俊朗、才华横溢。其实,表哥曾经也很帅,大眼睛炯炯有神,卧蚕眉乌亮含光,只不过如今眼神中写满了沧桑和辛劳,在岁月的侵蚀下已黯然无色。一头蓬松杂乱的发型,看出来是习惯了不带任何修饰,那天他来的时候,穿了什么衣服,我似乎都想不起来了。
看着还算彬彬有礼的表侄,我倏然想到十八年前,在基本上没有手机的年代,他爷爷专程来到我家报生娃的喜,我们问他生了没,他不停地搓着双手,腼腆而羞涩的脸,掩饰不了内心的狂喜,答得倒挺全:“生了,是个儿子。”眼前这个娃娃,就是当年让他爷爷从农村赶到城里奔走相告的那小子,虽然没有考上名牌大学,倒也不枉费几代人的期冀。
一天,偶读《千家诗》,发现其中收录了一位并不有名的诗人窦叔向的一首并不有名的诗:夏夜宿表兄话旧。其中有一句,言语朴实却道出万千情感:“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白云苍狗,抚今追昔,窦叔向与表哥再次相见,定是感慨万端。而如今我却与表哥几乎是默默无语,近三十年未曾深入交流,表哥还是老家的表哥,我已似乎不再是当年流着鼻涕膜拜他,向他讨教降龙十八掌的表弟。看着表哥,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他父亲,憨厚朴实,自己无求,一辈子就活了个孩子。
表哥手上没戴“表”。别人也许拥有戴“豪表”的表哥,而我这个没表的表哥即使渐渐陌生,却依旧可亲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