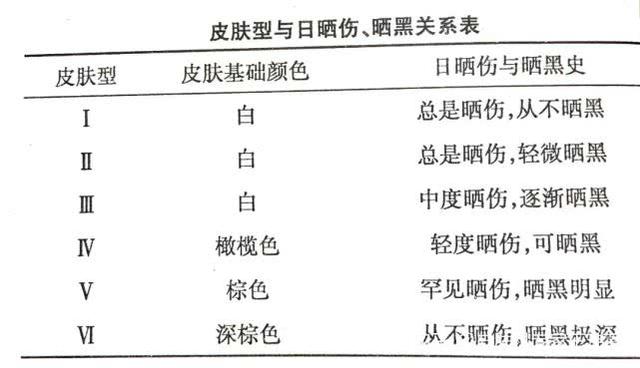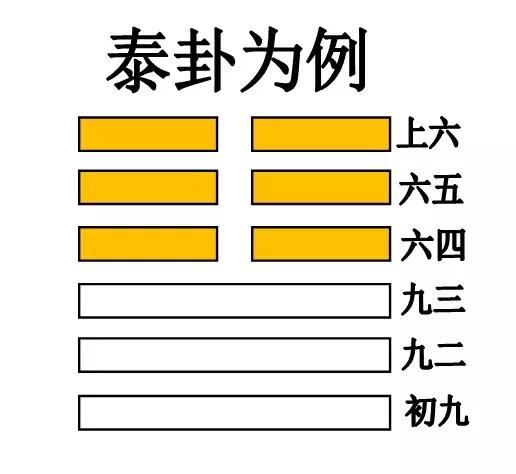2019年4月,母亲在老家院子里面坐歇我的母亲冯秀珍,是1937年生人,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养母是最好的母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养母是最好的母亲
2019年4月,母亲在老家院子里面坐歇
我的母亲冯秀珍,是1937年生人。
我知道,母亲也许再也无法下床,或者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残年余生。
母亲住院治疗,因长时间卧床加之吃饭少而缺钾,上厕所都站立不稳,医生让多吃香蕉、苹果之类的水果补钾。离开医院时,母亲又是双眸泪流。我不敢对视母亲,其实每次的相见何尝不是生死离别呢?明天与意外,谁知道哪个先到?拿出几千块钱塞给母亲,她怎么说也不接,我只好压在她病床枕头下。母亲一把拉过我的手说,妈把你的钱花扎实了,你挣些钱全都扔到咱家这个穷窟窿里了,17岁出门你只拿了8块钱、50斤粮票,再没花过家里一分钱,没穿过妈的一针一线,我把你两个哥的娃都经管带过,而桐桐娃我没给你照看过一天,还一直花你的钱,妈心里不安,你现在娃正在上学,媳妇又没工作,负担也重。说着说着,泪又从妈满是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
我们姊妹四人,只有我一个在外工作,以前家里日子过得再艰难、再紧巴,母亲从没有张口向我要过钱。那些年接连给大哥二哥定亲、结婚、办结婚酒席,粮食和钱都是向村里亲近人借的。每到腊月年关母亲就要发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人口多,收入进项少,往往是旧账未清,又添新账。母亲看尽了人的眉高眼低,尝尽了世态炎凉。
大哥二哥分家后,父母都是自己种地,农闲时母亲拖着病身子给别人拣个辣椒、掰个大蒜挣几个零钱补贴家用,父亲也是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村里的炼油厂看厂子。两兄长和我都觉得父母年龄大了身体都有病,我也让把两人的地分给两个兄长,特别是我在外面工作父母还干农活,打零工挣钱,怕村里人笑话。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能行能走时候,不给我们添负担,她和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也没给我们兄弟留个好过活和家产,别人分家都是分家产分东西,大哥二哥分家时,分摊的是两人结婚时的旧账。现在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有零花钱,真是“王世万”过的日子,还有啥嫌的。
父母亲快七十岁才把地分给两兄长去种。无论环境怎么变,条件再好,旁人怎么劝说,但她却无法改变节俭持家的习惯。那时候她做饭从不放油炒菜,都是清煮或下到面里,晚上也是凑合下,烧点开水就着馍馍吃。每年冬天母亲经常咳嗽,我询问了单位医生并推荐了药,打电话时让她买几瓶咳嗽糖浆吃了就有效果,等几天后我打电话问母亲药买上没、吃了吗?母亲告诉我吃了那甜丝丝的,吃了效果好得很,话没说几句就挂了。一问才知道,母亲一打听那种糖浆一瓶四五十元,就不买了。
我从基层部队干到大军区机关,那时经常出差或下部队检查工作,有机会就抽空回老家,每次都给父母留点钱,几十年下来攒了好几万,但再有钱母亲也是能省则省,不多花一分钱。母亲曾四次病情危重,她觉得过不了这个坎儿了,把父亲叫到身边,叮嘱父亲柜子里的几万元是这几年零零星星给的,她如果走了,让父亲第一时间把钥匙交到我的手里。我知道母亲怕两兄长说她偏心,更怕分这份省吃俭用来的钱。母亲把什么事分得很清楚,帮是帮给是给,是谁的不能含糊。一家人一起时,母亲就说今生你们是姊妹,就要相互帮衬扶持,之间遇事要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把关系处好处和睦,使这份今生今世“一家人”的亲情延续下去,不让外人看笑话。两兄长盖房、侄子外甥定婚结婚,都要给些钱表表心意,在经济上支持。每每想到这些,内心酸楚感激无以言表,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与大爱又怎么是用钱能换来的啊!哪有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二哥二嫂几年前为了照顾父母放弃了出门打工挣钱,长年在家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怕有个闪失,给我没法交待,所受的委屈艰辛苦楚,只有他们内心知道。
二哥在电话中和我商量,母亲这次出院后,让父母一同搬到他家去住,有什么事喊一声就能有个照应。这几年母亲体弱多病,吃饭全由二哥来经管,二哥和父母住的地方连在一起,离他的屋子四五米远,有个上下台阶。那天中午从医院出院回家后,母亲无论二哥怎么说也不搬下去,二哥只好随了母亲,叮咛她在炕上千万不要乱动,有什么事喊他或者等他来,可心勇气盛的母亲不愿拖累别人,自己下炕,一头摔倒在地上,她又从屋子里爬到院里,二哥发现时赶紧背起来放在炕上,问母亲摔到哪了,什么地方疼,那时的母亲已麻木,说不准身体什么部位磕在地的。等到晚上六七点我发视频时看到二哥在炕上抱着母亲,才知道摔倒的事。二哥不停地给我埋怨,说母亲执拗,不听他的话,刚出院又弄出这难子。母亲疼痛难忍,一会儿要侧左,一会儿又让侧侧右,一会儿让放平躺着,一会儿立马又喘不上气来,浑身难受不自在。二哥忙得焦头烂额,又叫来大哥帮着给母亲翻身倒水伺候大小便,到半夜一点多钟看着实在不行,给120打电话,把母亲送到县医院拍片子做检查,才知道胯骨已经骨折。医院没法治疗,建议回家卧床休息……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母亲和两个兄长谁都没合一眼,母亲疼得不停地出声呻唤,大哥和姐夫开着车到周边县城找医寻药,打问到一位姓马的医生,听周边的人说,任何骨折就是摔碎膝盖的,到他那里都能接好。但这位骨科“神医”看了医院拍的片子,询问病史后,也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让回家静养。
母亲的疼痛劲儿使我和两个兄长内心焦急不安,我也是四处打电话给亲朋好友,想买些镇痛药剂,减轻母亲的痛苦,但国家管控严格,个人根本无法买到。我又给老家的战友打电话咨询老人骨折治疗情况,朋友建议做换骨手术,这样以后就能行走。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农村老一辈子人说男人怕脚肿,女人怕脸肿,这样就有生命危险了。母亲摔了后第二天,脸肿得像盆子一样,喉咙里卡着痰,说话都费劲,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多少往事一幕幕浮现,母亲对子女、对家、对父亲、对亲朋好友、对村里人正直、善良、仁慈、温情,忠厚。从前探亲休假或出差顺路回家,母亲知道我是面肚子,中午肯定做手擀面,满满的情、浓浓的意,母亲做的面光滑、筋道、耐嚼,她调的汤汁咸淡适宜,一碗面是满满的家的温暖和情怀,有妈的味道和无尽思念。有年夏天我回家,母亲知道我爱吃西红柿,可村子街道没有走街串巷拉车叫卖的,她就跑到其他街道去找或者到邻村去买。结婚后,每年春节回家,母亲都要变着花样做饭,每次端起饭碗,母亲就端小板凳坐在我身边,她给我盛上一大碗,红红的油泼辣子拌在上面,看着我甩开膀子大口地吞咽,母亲就会笑得像花儿一样。
从战士开始,我一直学写新闻报道,上了军校也是学新闻专业。从此,新闻报道工作伴随着自己成长进步,加班熬夜成了家常便饭。生活比常人少了规律性,一米七五的个头,体重却不足110斤。只要打电话,母亲都要说少熬夜、多吃饭,冬天时候母亲总要说你把自己穿暖和。七十三岁的时候母亲耳朵背了,面对面说话也要出大声才行,但我还是两三天和母亲通次电话,往往是我说十句她能听清两三句,往后日子,我就默默地听她给我唠叨东家长西家短,听她说点以前的陈年老事……
从驻地坐火车回到老家,看到风烛残年的母亲还要遭受这样的折磨,我的心在流泪滴血,那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之伤痛。和姊妹们商量时,都觉得只要做手术能站起来、能行走,母亲虽受了手术的一时之痛,但不受长期卧床之苦,生活能自理、身边也不用人长期照料。怕有什么意外,也怕母亲过不了这一劫,远在兰州的媳妇带小孩利用双休日回到老家,在县城给侄子带小孩的大嫂也都赶了回来……母亲却还坚持着不去西安做手术,说临死了还要花费大钱给儿女们造麻烦,活多少才是够,就是现在一口气断了,也觉得你们把心尽到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母亲身边,内心是那么的安稳踏实,平顺安详。多年以来在外的打拼,为名为利为家为孩子的浮躁、焦虑、不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人与人间的攀比,那种心累不堪回首,在此时此刻都觉得可笑可叹,如浮尘般轻如鸿毛。直到天亮时分,母亲才算勉强答应。
雇用的救护车把我们送到联系好的医院,等做完各项检查,主治医生把我和大哥叫去交代母亲的病情,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压根儿没提骨折的事。看着护士把母亲推进重症监护室,四天四夜的救治,内科病症才有所好转。这时医生又急忙联系骨科专家会诊,最后意见也是母亲用不了麻药,有可能上了手术台就出不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次老,两次小。《晋书·食货志》曰:“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小。”到了老小孩的年纪,母亲的脾气越来越像小孩,任性和固执,爱计较,爱唠叨,指责大哥如何不对,二嫂给她吊脸,二哥朝她吼。母亲耳朵背,说话声音小她听不见,声音大了母亲觉得吼她,每次做饭前二哥、二嫂或侄子都要问母亲吃些什么,次次母亲都会说做什么吃什么,不把内心里想吃的说出来,她怕麻烦二嫂还怕二哥说她费事,越是这样的客气生分,越使得二哥二嫂难以做人、做事、做饭,有时饭做好了端过去,母亲又叨叨着嫌饭咸了淡了软了硬了的,二嫂经常要做三种不同的饭菜。村子里的人和亲朋去看她,母亲往往都会哭起来,说人老了不如七八岁的小孩,吃饭干啥都要人伺候,不能行不能走,还不如利利索索地走了算了,少了儿女们的累赘。母亲在旁人跟前哭啼诉苦,往往把二哥他们搞得很难堪。
近两年姐姐有胃病,家里也有两个五六岁的孙子,从西安回来,有十几天没去看母亲,母亲就给大哥二哥唠叨骂姐姐,说姐姐在她跟前没孝心,不像别的姑娘那样三天两头来伺候父母,给洗衣服……大哥二哥这时就数落母亲,现在都有自己的家,都要过日子,闲了肯定会过来看你,再说有我俩伺候,让过来干啥。过段时间姐看她时,看着面黄消瘦,母亲又拉着姐问长问短,让抓紧看病,还不停催促大哥二哥给姐夫打电话,让抓紧治病,不能耽误……村子里人去看她,说那种药对她的病有好处,某某人吃了那药后都很好,母亲立马就说给大哥二哥给她买,吃了几次没效果就再不吃了,床头放了十多种药,都是母亲让买来没吃完的;邻居常去和母亲拉家常,说喝牛奶好,母亲又让二哥订了牛奶,喝了又拉肚子,就不再喝了;二哥养了十来只羊,母亲又要喝羊奶,也是尝了尝就不喝了。去年回家,母亲要个收音机,我就找了那种操作简单小巧的,用了一两次也是锁到柜子里
……
母亲老了,家里最小的我也是五十出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大哥二哥也是有自己的儿女、孙子,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也有家务、农活和养家糊口的压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都变得心浮气躁,心思用在更高的物质追求上,为房子、车子、票子而奔波忙碌,年迈父母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倒成了发达富裕的负担,每当看到农村空巢老人的景象,暗自在想,这是当代人的悲哀警示还是现实的讽刺,老年人的生活做儿女的倾尽心力了吗……
母亲常念叨“娘的心在儿女身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儿时不懂母亲意,读懂已是意中人。母亲常常因为琐事和兄嫂们发生不愉快,我便成了化解他们矛盾的桥梁纽带。在和兄长聊天拉家常时,兄嫂们埋怨说整天小心翼翼细心照顾,生怕母亲不满意不高兴,日子久了,不但没在母亲跟前落下好,还时常用别人的优长来对比,让兄嫂深不得浅不得,陷入两难境界,最后惹得母亲不高兴,兄嫂们很委屈。面对母亲,爱啰嗦、记性差、乱操心、指教多,而我们没有真的把她当作小孩一样对待,少了理解,缺了温情,没了耐心。久病床前无孝子,也许我们终究走不进老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无法理解她的世界里满是孤独寂寞,是无奈,是病痛折磨的痛苦,是对走到生命尽头时的渴望留恋,是对儿女的不舍和依恋……
人性就是这样,拥有时不知道珍惜,往往失去了才会懂得。我们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了外人,把不好脾气个性留给了亲人,因为亲人不会计较。
我只有在内心默默为母亲祈祷祝福……
□张恋潮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