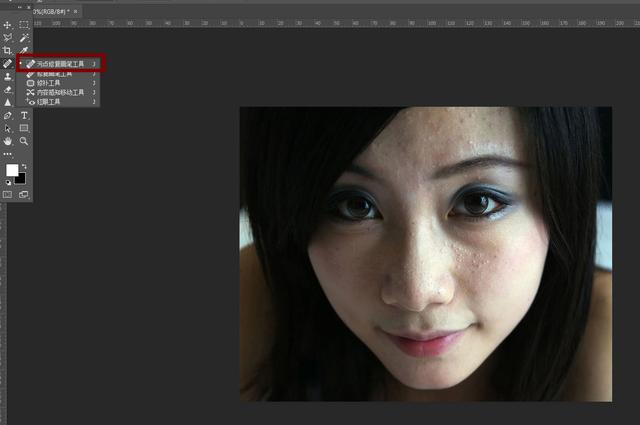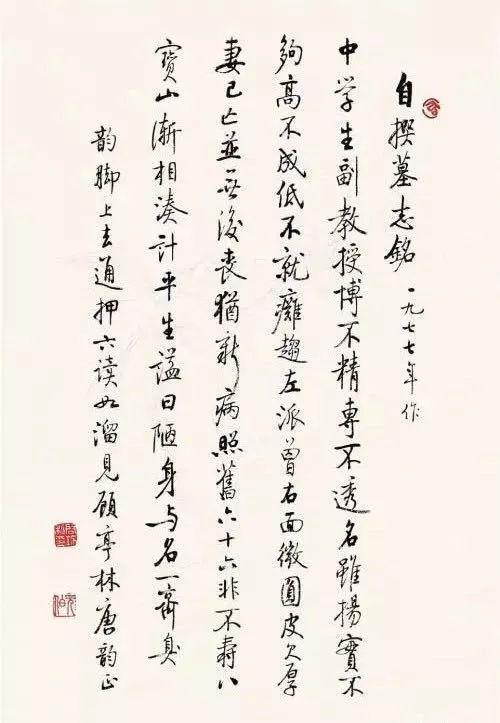◎叶克飞
“(1960年代的鲍勃·迪伦)在他的拥趸与诋毁者当中都激发了程度极为强烈的个人参与,以至于人们不允许他成为偶然现象。世人渴望一个征兆,他们曾经围绕在他的身边,只为等待他丢下一个烟蒂。一旦他真的这么干了,他们便悉心分析他扔下的东西,寻找其中的重要意义。可怕的是,他们真的能够找到——而且它也的确非常重要。”
这是《谈鲍勃·迪伦:精选评论集1968—2010》一书序言中的一段,作者格雷尔·马库斯随后写道:“这就是我成为作家的起点。”
格雷尔·马库斯是美国文化批评家、乐评人,被誉为“第一代摇滚评论家的先驱”,也是“跟踪”鲍勃·迪伦数十年的人。《谈鲍勃·迪伦:精选评论集1968—2010》如同一部以鲍勃·迪伦为主的美国流行音乐文化史,并且跳出音乐范畴,探究美国社会风潮的变迁。
鲍勃·迪伦当然值得书写,他绝非一般的流行文化代表人物,而是一个从创作到人生,恰恰与美国、与大时代、与无数风潮重叠的人物。当他在舞台上吸引着一代美国人的目光时,不但继承着美国的过去,展示着美国的现在,还预言着美国的未来。
鲍勃·迪伦也从不缺乏记录者,但无数人来来去去,唯有马库斯坚持了数十年,与自己所记录的人一起度过跌宕时代。
正如《纽约客》所言,“他(马库斯)仍是一个绘制地图的人,时而描绘乌托邦,时而描绘末日。他仍在旧地图上搜寻新的天地。”
这幅地图过于复杂,以至于许多人无法读懂。此书译者董楠就坦言:“马库斯的书是有一定阅读门槛的,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知识储备,或许还需要一些耐心。”
董楠还在译序中这样描述鲍勃·迪伦:“同任何在人生早年登上巅峰且幸运或不幸地未能英年早逝的人一样,持续终生的诅咒随之降临。曾经顺势将他推向高空的时代巨浪开始了足以令人粉身碎骨的下滑;曾经如同火山喷发般的灵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寸寸枯竭;早年的成功巨大阴影更是始终笼罩在他头上。他,一个如今已是近乎江郎才尽,被后辈视为恐龙的狼狈中年人,依然要在这个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尼斯·乔普林、吉姆·莫里森于27岁死去;‘披头士’无可挽回地解散;伍德斯托克的纯真被阿尔塔蒙特的血迹葬送;在伊甸园之梦已经醒来的世界里寻找自己、失败,再一次寻找自己、然后再一次失败。他曾经尝试赞美家庭生活,最终却以(两次)离婚告终;他曾经尝试赞美信仰,最终还是向平庸的事业心投降。他曾经一次又一次令世人也令自己失望,然而始终没有停下跋涉的脚步。”
在这段路途上,“有少数同样自由坚韧的灵魂,他们并不过于靠近,只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以热切而又严厉的心情始终旁观,并且以文字或其他载体,做了宝贵的记录和见证”,比如马库斯。
马库斯对鲍勃·迪伦可并非只有赞誉,书中的记录甚至从一句“这是什么鬼”开始。多年下来,除了鼓励与赞美,马库斯还贡献了数不清的指责和担忧,那些批评毫不客气,却可视作最深沉的爱与尊重。
这一切基于最深的了解,在马库斯的文字中,鲍勃·迪伦不同时期的作品乃至细节,总因马库斯的发散性思维而隔空碰撞,建立种种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摆脱“在生活中听音乐”的方式,而是要将音乐当成生活本身。
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音乐中感知世界的变化、社会的变化,还有自身心境的变化。简单点说,便是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年纪听来会有不同的认知。
马库斯在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对61号公路的认知:“1965年,第一次听到鲍勃·迪伦的歌《重访61号公路》,我目瞪口呆。刹那之间,它在我心目中成了一条神秘的道路,一个充满显圣与幻象的地方。那条公路离我生活的地方足有两千英里,它显然成了一个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歌中说,在那儿,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去看,你就能够看到一切业已发生。61号公路是宇宙的中心。鲍勃·迪伦是想说,如果你用足够的努力去思考和观察,就能理解整个人类历史,一切故事和句子的组合都在你眼前展现,大路就是你最了解的那条道路。这首歌爆裂开来。”
这样的震撼,在多年后有没有变化?有左翼倾向的马库斯已经知道,“在美国音乐里,‘大路’其实是一个建立在阶级、性别歧视与种族之上的狭隘主题”,但是,有些情绪不会改变。
在马库斯看来,鲍勃·迪伦是从二三十年代布鲁斯与乡村歌手的传统中走出来的:离开这个地方,来到公路,离家乡五百英里,不知道去往何方,把一切都抛在身后。没有人能像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希宾小镇的优雅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大学辍学生这样,如此令人信服地实现这样的目标。
所以,当马库斯自己驾车在61号公路上走上一趟时,尽管“感觉跟开在任何公路上没有两样,什么也没发生”,但“这首歌依然没有失去一丝一毫的力量,至今也是如此”。
而且,它并非只是一首歌,“大路”也并非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它意味着方向,也意味着失去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鲍勃·迪伦与马库斯真可算是“天作之合”。被许多人视为无法解构的前者,正需要天马行空般的后者来书写。当音乐不仅仅是音乐,马库斯从社会学与历史文化等角度的切入,一方面能够回答人们脑中的问号,一方面又增加人们脑中的问号,就像鲍勃·迪伦的音乐那样。
当然,还要感谢深度乐评的时代,相比旧日的单薄,60年代末恰恰是乐评开启严肃化的时期。面对此前无法被书写的鲍勃·迪伦,这个世界找到了接近正确的书写方式,也找到了最合适的那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