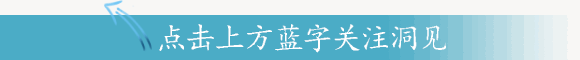《天工开物》泥造砖坯图。
《论语·公冶长》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同学白天睡觉,夫子于是发感慨: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对于宰予么,不值得责备呀。又说:最初,我对人家,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今天,我对人家,听到他的话,却要考察他的行为。从宰予的事件以后,我改变了态度。
这是劝学的著名桥段。以上子曰的内容,照录了杨伯峻先生的译文,以示权威。宰予字子我,名列孔门四科“言语”门下,自是夫子高足,不虞有此差评。
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宰予的判词是“利口辩辞”,也就是话说得好,反应还快,所谓雄辩是也。一众弟子中能入“言语”门,这本是自然。不过,话说得好云云,往往会有场景语气影响下褒贬之歧义。于是,能说会道的人,不免会在道德的某些层面遭际负面。所以,夫子“又说”的那段话,即便不出自他老人家金口,也不妨有广泛的认同度。
值得注意的是,与“朽木”相对的“粪土”,总不免令人费解。夫子自是以譬喻极言之,但与腐烂木头呼应的粪土墙壁,令人不详所从来。前贤有云:此二者以喻虽施功犹不成。这说的是喻义。又云:粪土之墙,易为垝(残缺,毁坏)坏,不可杇镘涂塓(涂刷,涂抹)以成华美。依然是就喻义而言。
有趣的是,阐释经书的诸前贤,解释了后人看来意义明了的“朽,腐也”,然于“粪土”之“粪”,则大多略而不论。
《说文》云:“粪,弃除也。”《广雅》也释为“除也”。王念孙疏证:“粪,犹拂也,语之转耳。”《左传·昭公三年》:“小人粪除先人之鄙庐。”《礼记·曲礼上》:“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段玉裁注《说文》则直言:“古谓除秽曰粪,今人直谓秽曰粪。”
虽然夫子所言之“粪”自是古义,弃除之土,似乎也可以解释为秽土,与“朽木”几乎也都可以从语义上构成对应。所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便说:“是除秽谓粪,所除之秽亦谓粪。此经粪土犹言秽土。古人墙本筑土而成,历久不免生秽,故曰不可杇。”
易为垝坏和历久生秽,取法路径不同,前者是用秽土作墙,后者则是蜕变生成秽土。前者说的是材质,后者则是后期维护的技术问题。而所谓朽木之“腐”,一般而言也是历久不免而生,貌似更符夫子本意。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名世的著名刺客豫让,也曾变姓名为刑人而入宫塗厕。“以时”云云,透露出定期意义上的某种规制,想来所谓后期维护的技术问题,斯时当有所措置,不成其为问题,应该不至于不可杇也。
而弃除之秽土作墙,似乎也令人生疑。
梁任公寄赠梁思成林徽因一部书,称其为千年前杰作,吾族文化之光宠,并嘱其永宝之。这便是声名卓著的《营造法式》,当年享誉一时的营造学社及梁林之子名从诫,皆由之而来。本书为宋通直郎试匠作少监李诫奉敕修撰,“系自来工作相传经久可用之法,与诸作谙会工匠详悉讲究”(《四库全书总目》),是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就营造的具体施工而言,北宋当然与夫子所处的古早时期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工艺应当是有所传承的,所谓相传经久是也,故不妨拿来参照。
作为建筑之一种,墙(本作牆,墙之繁体为墻,墻同牆)在权威辞书中被解释为用土筑或用砖石等砌成的屏障或外围。《说文》说它是“垣蔽也”,而且作为形声字,它是爿声。《释名》解释为“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左传》则有“人之有墙,以蔽恶也”。《淮南子》将本建筑的创始归为舜,赞美他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建筑自然是文明的重量级符号,归结到舜爷身上,也是传统叙事的经典套路。
《营造法式》卷三“壕寨制度”下有“墙”,讨论的是“筑墙之制,每墙厚三尺则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减半。若高增三尺,则厚加一尺,减亦如之”“凡露墙每墙高一丈,则厚减高之半,其上收面之广比高五分之一,若高增一尺,其厚加三寸,减亦如之”种种“制度”。
卷十三“泥作制度”下则有“垒墙”:垒墙之制,高广随间,每墙高四尺,则厚一尺,每高一尺,其上斜收六分(注:每面斜收白上各三分),每用坯墼三重铺襻竹一重,若高增一尺,则厚加二尺五寸,减亦如之。
墼,《说文》云“瓴適也”,王筠说“瓴適今谓之塼”。墼有已烧未烧两种,一如今天依然有砖和砖坯土砖,《说文》也提到“一曰未烧”。才子杨慎在《丹铅续录·拾遗》中引《字林》“磗未烧曰墼”和《埤苍》“形土为方曰墼”,以为“今之土磗也,以木为模,实其中”。土砖不简单等于砖坯,而是传统建筑中出于环境成本诸因素考量经常被用到的材料。
纪晓岚曾戍乌鲁木齐,《阅微草堂笔记》载:“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所筑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墼垒成;每墼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
“垒墙”后又专有“用泥”:“用石灰等泥壁之制,先用粗泥搭络不平处,候稍干,次用中泥趁平,又候稍干,次用细泥为衬,上施石灰,泥毕,候水脉定收,压五遍,令泥面光泽(注:干厚一分三厘,其破灰浞不用中泥)”。又云:“粗细泥施之城壁及散屋内外,先用粗泥,次用细泥,收压两遍。”
所谓粗泥细泥,卷二十七“诸作料例二”下“泥作”条列有粗泥细泥,分别为麦茎八斤与土七担、破碎的麦壳或稻谷壳一十五斤与土三担的配比,中泥同粗泥。既云泥,水自然是其中必需的和成元素,王筠所谓“泥用土及水”。
至于具体的取土,书中未见,想必是泥作行不言自明之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土部》倒是提供了线索。他明确,土以黄色为正色,而“黄土”条下,引陈藏器《本草拾遗》曰:张司空言:“三尺以上曰粪,三尺以下曰土。凡用当去上恶物,勿令入客水。”
张司空即西晋名臣张华,晋惠帝时累官至司空。他是留侯张良的十六世孙,年少贫苦,却才学过人,工于诗赋,辞藻华丽,草书也有名帖传世,更编纂了本土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在本书卷一“地”条下有云:“地以名山为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三尺以上为粪,三尺以下为地。”
这该是粪土的正解。即便今天的泥水活,包括烧砖土砖的取土,也是要挖地三尺的。夫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曾做过主委积仓库之吏的委吏,更在五十岁后,被鲁定公任为中都宰,又由中都宰而为司空,再由司空为大司寇。
司空是个古老的官职,据说舜时便设司空,由禹担任,负责的正是为他博得大名的治水。春秋时周王室与鲁、郑、陈等国均设司空,主管如前引《左传》所谓以时平易道路之类土木水利建设之外,同时职掌土地管理诸事务,当与东汉司空所谓“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云云大致仿佛。所以《国语》中单襄公见到司空不视塗等种种乱象,从而知陈必亡。当然,此处的塗为其诸多义项中道路之义。由于西汉时曾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官职性质已然不同,所以有人称夫子所任为小司空,后来也称工部尚书为司空。而张华所任司空,地位甚高,但往往是重臣的加官。隋唐宋诸朝也延续了这种虚衔加衔的路径。
夫子做官,一向用心,而建筑方面的相关鄙事,他老人家是不会忽略的,于是才会拿来取譬。所谓粪土之墙的粪土,就是三尺以上没有到“地”的土,说秽土未尝不可,但不方便简单视为弃除意义的土,而是不合挖取规制的用土。这样的土垒筑的墙,质地不纯,黏性不足,因而才不可杇塗也。
这一点,韩文公笔下手镘衣食的圬者王承福,尽管“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然于夫子粪土之墙云尔,却是清楚的。
粪土之墙和朽木的譬喻,落实到宰予同学身上,夫子的意思,当是说他不成器,不堪雕琢润饰以成就,即前贤所谓虽施功犹不成。如此极言之譬喻,听起来不免严苛。王充便说:“昼寝”之恶,小恶也;“朽木”“粪土”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崔述也以为,宰予为圣门高弟,朽木之喻种种,愆尤未免太多。这其中,也许果然有宰予个人的器质因素,不过也足以体现夫子严师的本色。
半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