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十年的《金瓶梅》研究中,有人提出了一个颇受注意的观点,即《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而是像《三国》、《水浒》一样,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此观点最早出现于五十年代,由潘开沛先生提出,当时并未受到太多注意;但近年来经过几位先生的反复论证,已成为《金瓶梅》成书问题上一个颇有势力的说法。
笔者在研究了有关文章之后,感到论者提出的论据虽有数十条之多,但有说服力者尚无一条。
本文拟对其中的几个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作为向几位先生的商讨意见。

大安本《金瓶梅词话》
一、何谓“世代累积型”?
“世代累积型”的提出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学现象:
“中国小说戏曲史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相当多的作品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
文人的编写有时在重新回到民间、更为丰富提高之后才最终写成。”(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前言》)
毫无疑问,论者指出的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以“世代累积型”来概括某些作品的成书方式也是很恰当的。
但我觉得要把“世代累积”作为与“个人独创”相区别的一种基本创作方式和一种小说基本类型来认识,对其内涵应该给予严格的规定。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世代累积”理应包括以下几点:
1、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世代流传的;
2、小说中的主要情节是世代相延的;
3、“世代”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比如说,要经过朝代的更替;
4、更重要的,这一切必须有史料根据。
《三国演义》显然是符合这几个条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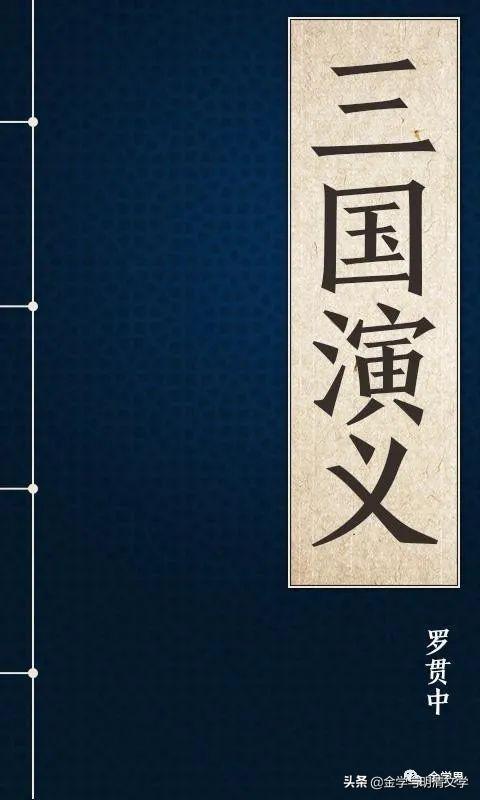
《三国演义》 (明) 罗贯中
书中的主要人物均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有关他们的记载可以说史不绝书;不但正史有传,民间流传亦既广且长。
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也是于史有征的历史人物。
至于三国故事,远自隋唐,直至元代,经过历代各类艺人的努力,内容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整,为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国志平话》已为我们展示出《三国演义》的大致轮廓,而元杂剧中的众多三国戏,
则使《三国演义》的基本情节更为丰富,人物性格更为丰满,使它更具备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云其“世代累积”,可以说名符其实。
当然,这并不影响作者运用增删、移植、更改乃至张冠李戴的手法,对世代累积的题材加以改造,以符合自己的创作需要;也不影响作者运用想象,虚构出一些东西加入作品中。
《水浒传》的情况与此相仿,只是《水浒》的主要人物除宋江、方腊等及其事迹正史有载外,大多数人物与故事都是民间创造的;
至元代,这些流传的传奇人物和故事也初具规模,《大宋宣和遗事》和有关水浒故事的说书、戏曲可为明证。
与《三国》相比,施耐庵创作《水浒》虽也以世代流传的人物、故事作框架,但其虚构的东西更多,在现实生活中的取材更多,“史”的味道则远逊于《三国》。
所以人们才一称为“演义”,一称为“传奇”。
尽管如此,《水浒》的主要人物、故事宋、元以来就广泛流传,并为施耐庵所运用,仍应视为“世代累积”的小说。

《水浒传》 (明) 施耐庵 罗贯中
二、《金瓶梅》的人物是世代流传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丝毫史料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使从作品人物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也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而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1、关于西门庆、潘金莲
两个最主要的人物西门庆和潘金莲,虽在《水浒》中已经出现,但大家都承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潘金莲,绝不是《水浒》中的西门庆、潘金莲。
不但作者赋予他们的生活内容有多寡之别,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格本质是根本不同的,分别体现着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
西门庆在《水浒》中只不过是一个好色的生药铺主人,而且很快成为武松拳脚之下的短命鬼;
在《金瓶梅》中,他却躲过武松的惩罚,又过了很长一段花花绿绿的人生,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公,最后才死于自己燃起的欲火炽焰之中。
潘金莲也由一个好淫的短命妇人,变为性格复杂的小说主人公。
他们在《金瓶梅》中所做的一切,都是《水浒》所不曾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
如果二人在《水浒》成书之前就是世代流传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内容不可能如此贫乏,《水浒》的作者也不可能将其安排为转眼即逝的次要人物,何况,我们并未发现《水浒》之前的正史、说书、戏曲中有关西门庆、潘金莲的任何踪迹。
更可能的倒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奸情,是《水浒》作者作为表现武松的刚直性格而临时虚构的。
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既有对世代累积素材的运用,又有自己的虚构创作,西门庆、潘金莲及茶坊王婆的故事,应属于后者。
虽然持论者“设想”:
“与其说《金瓶梅》以《水浒》的若干回为基础,不如说两者同出一源,同出一系列《水浒》故事的集群,包括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在内。”(同上)
但面对《金瓶梅》前几回对《水浒》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抄袭,以及充满西门庆、潘金莲身上的明代生活气息,这种“设想”是没有说服力的。
另外我们还需注意,据沈德符记载,《金瓶梅》作者还写过一部《玉娇李》,亦为西门、金莲、武大故事,然寓意正与《金瓶梅》相反:
“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万历野获编》)
如果“世代累积”说能够成立,那么与《水浒》并行流传的非仅《金瓶梅》,势必还要有一个《玉娇李》;而后二者在《金瓶梅》成书前均无丝毫信息。
这是不符合民间流传故事的一般逻辑的。
道理很简单,前人不可能只著录《水浒》故事,而放掉与之相联系的《金瓶梅》故事和《玉娇李》故事;更何况,后者对听众的吸引力比《水浒》还要强烈。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金瓶梅》故事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中道)而成的,西门庆、潘金莲是从成书后的《水浒》中化出,不会有其他可能。

《万历野获编》 (明) 沈德符
2、孟玉楼的命名
如果说西门庆、潘金莲尚与《水浒》有所牵连,能使人作出与《水浒》并行的“设想”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主要人物孟玉楼。
孟玉楼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与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等人物关系密切,是整个故事不可缺少的人物,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
孟玉楼的命名来自两句诗:“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西门庆为孟玉楼打的簪子上就刻着这两句。
这支簪子曾被陈经济捡到,后来拿着到严州欲图讹诈玉楼.声称这簪子上刻着你的名字,如何却到我手里?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却被官府抓住痛打了一顿。
我查出这两句诗出自《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原文写奚宣赞被西湖白蛇精捉去,险丧性命,归来后“寻得一闲房,在昭庆寺弯,选个吉日良时,搬去居住。宣赞将息得好,迅速光阴又是一年,将遇清明节至。怎见得:家家禁火花含火,处处藏烟柳吐烟。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金瓶梅》只录后两句,并以“玉楼”作为孟玉楼的名字。
当然,“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两句亦见于其他话本小说,我所以肯定《金瓶梅》是抄自《西湖三塔记》,是因为与此首紧挨的另一首诗亦为《金瓶》借用,原诗为:
“百禽啼后人皆喜,唯有鸦鸣事若何?见者都嫌闻者唾,只为人前口嘴多。”
本为奚宣赞出门打猎,听到的乌鸦叫声。
此诗被《金瓶梅》作为回后诗用在第九十一回,写李衙内的妾玉簪儿见新娶玉楼,心中不快,常常吵闹;以“鸦鸣”喻之,写其不得人心。
《西湖三塔记》收在《清平山堂话本》,是宋元作品还是明人作品难以肯定。
一般认为应为宋元作品,因元代郑经有同名杂剧,虽已不传,内容应该大体相同。也就是说,当《西湖三塔记》与《武行者》、《花和尚》等《水浒》故事同时流行的时候,孟玉楼这个人物尚未“出世”。

戴敦邦绘 · 孟玉楼
而与之相联的诸多人物和情节当然也就不会存在。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有一个与《水浒》同时流行的《金瓶梅》故事呢?
更何况,即便是《水浒》,在宋元时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只是以互不关联的散篇流行,《武行者》、《花和尚》、《青面兽》等在元罗烨的《醉翁谈录》中仍分属“公案”、“朴刀”、“杆棒”,属于不同题材的作品;
将这些散篇串连在一起而成《水浒》,是后来的事情,有施耐庵的创作之功。
另外,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骨干人物,孟玉楼的命名竟是来源于一首文人气十足的诗,也说明她不可能是一个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人物,在现存的宋元小说中,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作品人物是以这种方式命名的。
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文人作家的虚构创作方式。
3、应伯爵、常时节、温必古之流的命名
更能说明本文观点的是几个帮闲人物的命名。
首先应该说明,应伯爵等人在作品中的地位,并不是像论者所云,乃“一些次要脚色”。
《金瓶梅》的主旨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东吴弄珠客),缺了这些人物,《金瓶梅》便不成其为《金瓶梅》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命名尤为奇特,完全用谐音的方式:
应伯爵(白嚼)、常时节(借)、卜志道(不知道)、韩道国(捣鬼)、白来创(左口右床)、吴典恩(无点恩)、温必古(屁股)、游守〔手〕、郝贤(好闲)等等,全书共有二十余人。
前此的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虽然作品人物常有绰号,如《水浒》,但用谐音的方法为人物命名却没有见到。
从张竹坡始,研究者早已指出这是一种奇特的讽刺方式。其独特之处在于利用语音的相同或相似,而字面却不相同,进行含蓄的讽刺。
而这种方式只能是一种文字技巧,而非语言技巧。
也就是说,它只能在文字创作中运用,而不能在讲说艺术中运用;它产生的独特讽刺效果只能在书面阅读中为读者所领悟,而不能在说书场上为听众所理解。
从字面上看,这些名字的含义或冠冕堂皇,或温文尔雅,看不出有任何贬义;但只有在阅读过程中,在联系到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的情况下,才会发现字面下隐藏着另外的内容,才能探知其中蕴含着强烈的讽刺意义。
如应伯爵字光侯,外号应花子。“伯爵”、“光侯”是何等庄重!然其谐隐的实际意义却是“白嚼”、“光喉”,也就是混饭吃。
作者在应伯爵刚出场时就规定了他的性格核心是“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是个实实在在的“食客”。

戴敦邦绘 · 应伯爵
常时节,从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恭,但其寓意是“常时借”,他曾不止一次地向西门庆借银子,书中专有一回写他“得钞傲妻”。
温必古,作为一个破落儒生,名字温文尔雅、古色古香,但联系到他“好南风的营生”,则温必古原来是“温屁股”!
他也正是因为这个不良习惯,被西门庆赶出家门。崇高的下面隐藏着卑劣,庄重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轻薄,这正是谐音的妙用。
显然,这是作者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一种讽刺方式,而且也只能是一种书面文学中的讽刺方式。
正因为这种讽刺方式能产生双重的艺术作用,所以屡为后来的文人作家所效法,甚至连曹雪芹这样的高才都没能例外。
但如果这一切都发生在说书场上,那将会怎样呢?
说书艺人在讲说过程中一直以“应白嚼”、“温屁股”、“不知道”、“白来(左口右床)”等称呼自己的人物,成何体统?岂不变成了一场粗俗的恶作剧?
其独特的深刻而又不失含蓄的讽刺效果又如何为听众所领会?
这一问题看起来不甚起眼,所以至今并未引起有关《金瓶梅》成书论者的注意。
但我以为,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区分文人创作和艺人创作、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分水岭,是《金瓶梅》非艺人创作、非说唱艺术、非“世代累积型”作品的铁证!
4、关于狄斯彬等明人
《金瓶梅》中还出现了不少明代真实人物,据有关研究者考证,这样的人物有十六人之多。
如明正德三年进士韩邦奇,六年进士尹京,十六年进士王炜,嘉靖八年进士任贵,十一年进士何其高,十四年进士王烨,二十六年进士曹禾、狄斯彬、凌云翼,二十九年进士黄甲,三十八年进士赵呐等。
甚至西门庆的亲家陈洪和陈经济也是明代实有的人物。
既然是“世代累积”故事,为何加入了这么多离作者年代很近的现实人物?
如嘉靖时的狄斯彬,在书中充当苗天秀一案的审官,此案贯穿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三回,是揭露西门庆贪赃枉法罪行的一个重要关目。
苗天秀故事借用流传很广的包公案,主人公本为包公,《金瓶梅》却换成狄斯彬。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全为巧合似不可能;如果说是某个“整理写定者”成书时加入,他粗疏得连书中的明显漏洞和重复之处都未来得及改正,却又不厌其烦地做这种移花接木的工作,究竟有什么必要呢?
但作为独创之作,他要借宋事写明代社会,书中出现明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插图本 《金瓶梅》
三、《金瓶梅》的情节是世代相延的吗?
与《三国》、《水浒》、《西游记》不同,《金瓶梅》既未写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又没写英雄豪杰的传奇行为,更没有狐妖神怪的奇异故事,它写的是“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妻妾之争风,优人之卖俏,帮闲之吹牛,全属不起眼的小事,似乎很难分出情节的主次。
相比较而言,像“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潘金莲共李瓶儿斗气”、“西门庆迎请宋巡按”、“李瓶儿痛哭官哥儿”、“西门庆东京庆寿旦”、“西门庆大哭李瓶儿”之类,应该说是较为主要的情节;而这些情节,在《金瓶梅》成书之前从不见著录。
事实上,前人不可能著录,因为《金瓶梅》本来写的就是明人明事。
“世代累积”论者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既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习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社会生活的鲜明印记。”(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
却又坚持《金瓶梅》故事是“世代累积”而成的。实在很难令人明白,明人明事怎么可能在明代之前就“世代累积”呢?
怎么可能在《水浒》故事流传时期就与之并行呢?具体到作品内容,书中除了出现不少明代人,
还有大量明代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如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太庙、佛教与道教、商业、世俗等,正是这些才构成了《金瓶梅》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这些内容都是入明之后才在原有故事基础上加上去的,且不说这还能否算作“世代累积”,而被人“设想”出来的《金瓶梅》说书故事,在宋元时期还能剩下多少可资讲说的内容呢?
至于说这些全是某位“写定者”改写某一“祖本”而成,也无可能。
因为他需要改动的并不是某几个人物或某几个情节,而是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到“史实习俗、方言服饰”都要加以改变。
如此大规模地改动,究竟是一次“整理”呢,还是重新创作?
对于《金瓶梅》中出现的大量他书情节及诗词歌赋,“世代累积”论者认为不是抄袭借用,而是在说书阶段的相互“蹈袭”,
不但与《水浒》的关系是“彼此渗透,相互交流”,与其他话本、曲集的关系也“难以区分孰先孰后”。

四大名著
如《金瓶梅》与《志诚张主管》的关系,论者认为“既不是《金瓶梅》抄袭《志诚张主管》,也不是《志诚张主管》摹仿《金瓶梅》。两者来源都很早,难以分清先后。”
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其实二者先后关系十分清楚。《志诚张主管》见于《京本通俗小说》,一般认为是宋元旧作,曾被冯梦龙《警世通言》收入,题为《小夫人金钱赠年少》,一作《张主管志诚脱奇祸》。
在《志诚张主管》里,主人公为小夫人、张主管(张胜),在《金瓶梅》里,这篇话本小说被一分为三,前半部插入第一回,小夫人变成了潘金莲;
后半部分安插在第一百回,小夫人又变成了春梅,张主管换成了李主管;而小夫人带出来的一百单八颗西洋珠,则又与李瓶儿有联系。
也就是说,《志诚张主管》的小夫人,在《金瓶梅》中一变而为金、瓶、梅。
如果《金瓶梅》在先,号称将“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凌濛初语)的冯梦龙,在收入此篇时,作品女主人公理应是潘金莲,或李瓶儿,或春梅,而不该是小夫人。
因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位,其故事都要比小夫人丰富,也更吸引人。况在《金瓶梅》中,张胜还有寻找陈经济,杀死陈经济的不少情节,冯梦龙收入时没有必要全部删去,而且将其名字换成李庆。
不仅如此,《志诚张主管》中的多首诗词亦出现在《金瓶梅》的不同回目中,如“乌云不整,唯思昔日豪华;粉泪频飘,为忆当年富贵。秋夜月蒙云笼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本为张主管见到的小夫人形象,在《金瓶梅》第一百回变成韩爱姐江南寻父时的形象描写。
这就是说,《志诚张主管》中的小夫人,起码与《金瓶梅》中的四个女主人公有联系。
这究竟是《金瓶梅》作者将《志诚张主管》拆开分别插入有关情节呢,还是民间艺人将《金瓶梅》有关情节收拢为一篇《志诚张主管》呢?我觉得结论是十分明显的。
当然,如果我们将《金瓶梅》与其他话本的关系也稍作分析,就会看出全是这种情况而无一例外。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是《金瓶梅》抄袭了这些话本,而非相反,亦非“相互”;《金瓶梅》在个人创作的基础上,又移用了嘉靖、万历时期流行的话本小说情节而成。

戴敦邦绘 · 韩爱姐
有人说:“个人创作出现明显的抄袭现象,那是不名誉的事”(《〈金瓶梅〉成书新探》)。
“只有当作品能给作者带来精神或物质的报酬,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抄袭。”(《再论〈水浒传〉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
笔者认为不能以今人的名利观念去衡量古代文人,尤其是古代小说家。
古代小说的地位历来十分卑下,为正宗文人、正人君子所不耻;即使到了明代,小说地位已有所改变,靠创作小说以求名利的人也还没有;以刻书渔利那是出版商的事,也没听说他们付给作者稿酬。
明清的那么多小说(包括《红楼梦》)连作者的真实姓名都不愿署(或不敢署),怎么会有名利?
而以《金瓶梅》这类小说求名利,更无异于缘木求鱼。至于说到“不名誉”,对古代小说家来说不存在这个间题。
曹雪芹如果懂得这是“不名誉的事”,何必抄用《金瓶梅》的那么多情节,有时连原话都不变?李开先可谓正宗文人,
如果他就是那个“写定者”,在别人的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塞入自己的《宝剑记》以及同时代的他人著作,岂不是“不名誉的事”吗?
再如《金瓶梅》抄录了大量他书上的诗词曲,有人便断言这是“说唱艺术的特有手法”,只有民间说唱艺人才会这样做,文人创作不会有这些东西。
事实根本不是如此。
这里我们可以用凌濛初为其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所写的“凡例”来说明:“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尚友堂原刊四十卷本《初刻拍案惊奇》)

《初刻拍案惊奇》 (明) 凌濛初 著
凌檬初无疑是位文人作家,他用自己的创作体会表明:
1、文人创作的小说亦是要有诗词的;2、这些诗词有一部分是抄袭别人的,因为这是小说家的“旧例”,故不要认为是“剽窃”。
这就有力地说明,抄袭借用不是说书艺人的“专利”,文人作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名誉不名誉,也与作者“精神或物质的报酬”没有什么关系,
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该据此推断《金瓶梅》为艺人之作,是“世代累积型”作品。
事实上,我们有更多的证据证明《金瓶梅》绝非“世代累积”之作,限于篇幅,只能留在另文中论述。关于书中的某些漏洞和重复之处,
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金瓶梅》作为第一部个人独创的长篇小说,是“仓卒成书”(周钧韬语),
很可能是创作出一部分,便传抄出来一部分,以至他没能就全稿进行统一的整理。
有关《金瓶梅》的最早资料,如袁宏道的“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
袁中道的“见此书之半”,沈德符的“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薛冈的“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等等,都显示了《金瓶梅》不是一次成书,见到全书是以后的事情。
在一段较长的创作过程中,写出部分被传抄出来,后面的创作出现某些不接隼甚至小有重复之处,应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其对他书的模仿、抄袭也正是文人初创时应有之举。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1993,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