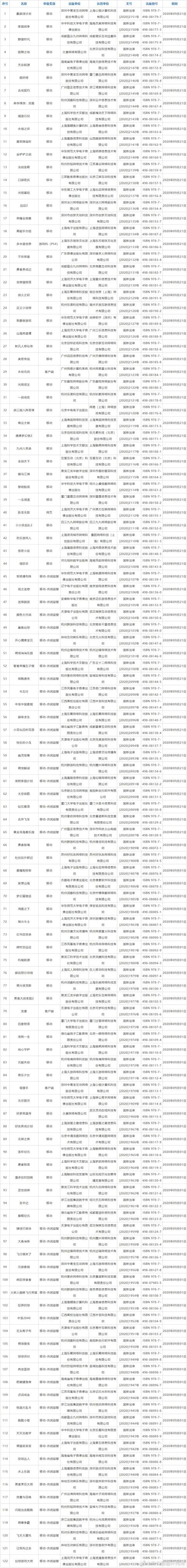罗伯特·威尔基/文 杨雷/译
毫无疑问,电子游戏已经成为技术产业和全球文化潮流的重要方面,其业务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0亿美元发展到如今估价1000亿美元的行业。最受欢迎的系列,例如EA的《麦登橄榄球》(Madden)和Infinity Ward公司的《使命召唤》(Call of Duty),其收入经常超过最赚钱的电影大片、音乐唱片和畅销书(Chatfield,2010:29)。此外,“网络游戏玩家的劳动对全球GDP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二的主权国家”(Dibbell,2006:25)。然而,数字文化理论家如尼克·戴尔·威瑟福德(Nick Dyer-Witheford)和格雷格·德·普特(Greig de Peuter)、朱利安·库奇利希(Julian Küchlich)、麦肯齐·沃克(Mackenzie Wark)、朱利安·迪贝尔(Julian Dibbell)提出,电子游戏不仅是“21世纪全球超级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 xxix),而且是基于“公司以利润的名义控制生活的权利和权力”,但也包含着潜在的“出逃路线(lines of exodus)”。

《麦登橄榄球》游戏截屏
这种矛盾——在“控制”和“出逃”之间——是对数字化或非物质劳动更广泛解读的一部分,它将数字技术的涌入和诸如电子游戏等新媒体商品的崛起,视为“非物质劳动”的资本主义时代的象征,又被称为“认知资本主义”。这些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工人主义(post-Operaismo,又称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数字经济目标中的资本不是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分析大工业市场资本主义时阐明的那样,而是非物质劳动集体产生的抽象智力”(Koloğlugil,2015:133)。根据这一论点,信息技术的兴起和专注于电子游戏与社交媒体服务等数字商品的公司的惊人增长,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资本不再从工人的剩余劳动中榨取利润,而是寻求捕获人们在Facebook发帖、在Google搜索,或者登录Xbox Live玩游戏时的剩余创造力。资本主义组织和目的的这种转变,在其中“数字经济是以‘一般智力’的能力为特征的……在没有资本的指导、控制或管理的情况下进行自组织”,代表着“在资本和社会劳动过程的技术构成方面的质变”(Vercellone,2007:18)。因而,一方面,“劳动的结果仍然包含在工人的大脑中,因此与参加劳动的人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劳动与非劳动之间的传统对立失去了任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电子游戏被解读为从剥削雇佣劳动到捕获创造性能量的典型存在。朱利安·库奇利希称之为“玩工”(playbor)。
“玩”,换言之,概括了所谓的认知资本主义的非物质逻辑,即创造力与物质商品的情况一样,不能与劳动者相分离。“玩”也不能被限制在剥削雇佣劳动的传统机制中,因为它不能被计划或与任何特定的实践、地点或阶级相捆绑。在此基础上,游戏和游戏玩家的非物质劳动被称誉为具有潜力的后阶级运动(postclass),这种运动从生产者和消费者、工人和所有者、游戏时间和工作时间之间的所谓颠覆性的分歧中产生,这些分歧破坏了传统的阶级关系,开启了“新的主体、欲望、拒绝和能力”(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 5),预示着“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Vercellone,2007:5)。简言之,“玩”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迹象,表明全人类可能会出现一种无法定义的合作,以此抵制公司的控制,并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内部破裂。正如汤姆·查特菲尔德(Tom Chatfield)在《趣味公司:为什么游戏将主导21世纪》(Fun Inc.: Why Gaming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0)所写的那样,“尽管游戏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游戏中仍存在一些本质上具有颠覆性的东西,甚至有力量打开资本主义巨大游乐场的大门”,特别是“在一切事物中暴露出来的玩”。
在本文中,我采用了后工人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解释,并认为,对电子游戏的解读重新了定义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划分,这有助于一场更具流动性的斗争,即谁将控制数字经济的非物质公地——帝国的信息垄断者还是大众的黑客玩家——这引发了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导致意识形态层面的扩展,而非挑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推广“玩”(消费)和生产一样具有效力的错觉,数字文化理论中关于电子游戏的主流论点开始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事后”(post festum)——也就是说,在生产层面对劳动的剥削已经发生之后——因此,“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为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09:93)。将工人阶级重新定义为“诸众(multitude)”和将劳动定义为“玩”,这种先进的解读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道德误解。它着眼于改变就业形式和科技公司的管理策略,而非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剥削。在将消费(玩)作为个人“创造一种无法在生产资料中物化的集体智慧的手段”(Koloğlugil, 2015:133)时,这将资本主义更“激进”地解读为“一种基于企业剥削各种类型的有偿和无偿劳动的生命权力制度,以不断满足全球富豪的统治”(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xviii)。这实际上是一种非物质化和非历史化的分析,导致得出的结论是,“不是通过夺取权力,而是通过减少制度的支持,同时建构其他制度”来实现现有制度的转变。然而,真正的自由不会来自“玩”的再分配政治,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和它所依赖的劳动剥削的终结。
一、电子游戏和非物质玩工的意识形态
电子游戏产业已经成为当前数字文化理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思考的一个指标,有一种说法是“互联网公司通过剥削用户的‘玩工’来积累利润”(Fuchs, 2014:126) ,或者,换句话说,“生产正融入玩之中”(Dibbell ,2006:25) 。这种基于玩(消费)而非劳动(生产)的对全球经济进行“滑稽式”的解读,是将“认知资本主义”更普遍解读为“最近兴起的一系列产业的崛起,对这些产业而言,先进形式的集体知识的动员、提取和商品化是基础”(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37)的症候。无论是克莱·舍基(Clay Shirky)和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等作家对技术欢庆式的解读,还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佛朗哥·比弗·贝拉尔迪(Franco“Bifo”Berardi)的批判性论点,数字文化理论的主导框架是,我们正在见证从工业生产的模拟经济向信息交换的数字经济的转变,这与社会生活的根本性重组相对应——从生产到消费,从物质到非物质,从工作到玩。正如迈克尔·A·彼得斯(Michael A.Peters)和埃尔金·布鲁特(Ergin Bulut)所指出,“越来越多的象征性商品的联合生产重塑了生产过程,但私人对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占有只能通过强制执行人们认同的社会惯例(专利、版权、商标)来实现,而不能由市场机制自发地复制”(Peters, Michael A., and Ergin Bulut,2011:xxxiii)。根据这种逻辑,认知资本主义从基于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制度转变为一种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数字经济的收入由租金构成——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通过数字平台的所有权和数字权的使用来控制集体智慧”(Koloğlugil,2015:135)。换言之,只要创造力不与创造者相隔离,资本主义的利润是通过令人费解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EULA)创造的“人为”所有权产生的,以及扩展版权法的适用范围,使其适用于任何时候有人搜索关键词或玩游戏时发布到谷歌或微软上的个人信息。例如,沃克认为,在游戏空间中,资本对游戏玩家“创造力”的政治控制,是经济“游戏化”幻觉背后的所谓现实。她写道,在认知资本主义中,“你无偿做某事,因为你想去做,而不是不情愿地通过劳动换取工资或其他奖励,而是为了好玩,就像‘玩工’一样”(Wark,2013:73)。沃克接着宣称,虽然数字商品消费中的玩和创造力“看起来像是礼品经济的逻辑”,但实际上“不是‘玩’本身创造了游戏,这种游戏是以‘玩’的形式提取劳动,通过创建可以从网络中获取的数据,并且这些数据是绝对专有的”。在电子游戏等非物质商品的扩展中表现出来的对技术和科学日益增长的社会价值,被解读为与生产方式更深层次的变革相对应,即在数字经济中,资本对物质劳动的工资剥削已经让位于一种建立在包围和控制非物质劳动所产生的文化共性之上的经济制度。

《游戏帝国:全球资本与电子游戏》书封
威瑟福德和普特的《游戏帝国:全球资本与电子游戏》(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一书是将非物质劳动和后剥削生产理论与电子游戏研究相联系的主要文本之一。电子游戏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在这种范式中,价值无论好坏,都是被获取和控制的,而不是通过雇佣劳动剥削来榨取的。他们的核心论点是,认知资本主义的运作不是通过剥削,而是通过知识的累积和商品化。例如,在电子游戏中,通过“将游戏玩家—生产者的创新困在商业结构中”(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xxx)。根据这一逻辑,电子游戏已经开始反映非物质经济的核心矛盾,即将玩家的“玩”变成一种累积情感、审美和信息价值的手段。通过参与网络游戏,诸众的非物质劳动通过租金机制成为资本的控制对象。他们写道:“资本现在在诸多方面挖掘主体的能量:不仅作为工人(作为劳动力),而且作为消费者(营销者瞄准的‘智力份额’)、作为学习者(作为职业准备的大学学位)甚至作为原材料的来源(为基因工程提取的生物价值)”。在这个层面,认知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完全“实质吸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09:583)。这样,所有的活动,包括那些专注于创造力和玩而非工作的活动,在产生公司收入方面变得富有成效。在这种背景下,认知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工业阶段被认定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而是存在于试图控制“玩”的尝试和将“玩”作为一种超过任何此类尝试的无政府主义实践方式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式中,“玩”成为“生命”创造性能量的隐喻,它与生命政治试图将其削弱到一个预定的、工具性的模式作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威瑟福德和普特认为,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工人的头脑变成生产的‘机器’,为那些用薪资购买了它的思维能力的所有者创造利润”(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37)。电子游戏既是“帝国的典型媒介”,也是“目前挑战帝国的一种力量”。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处于电子游戏产业核心的“非物质劳动”,“更多的是主体性的生产,较少的是物的生产”。正如游戏产业“开创了基于知识产权、认知开发、文化融合、跨国转包苦活和市场化的世界商品的积累方式”。对非物质劳动的依赖开启了一个新的“创造”价值的场景。根据这种认知资本主义模式,重要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玩”的文化体验。它围绕商品而兴起,并赋予商品以“生命力”。同时,通过侵占玩家的无偿劳动,使之成为帝国对诸众进行政治控制的机制。实际上,正是那些在“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结识的玩家——创建充满活力的在线社区,吸引其他人加入,进而增加付费人数并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才赋予了这款游戏的“价值”。换言之,魔兽世界对其母公司暴雪(Blizzard)的价值在于这款游戏的用途,而不仅仅是它作为商品的生产。然而,由于游戏产业的经济被假定为依赖于“来自体现非物质劳动新梯队自主能力的DIY玩家与生产者文化中不断融合的能量”。它同时成为创建“超出帝国试图限制它们的用途”(Ibid,187)的德勒兹之线(这里指逃逸线)的基础。或者,回到前面的例子,尽管许多游戏玩家的行为“被游戏资本所补偿,有些是毫无意义的或破坏性能量的黑洞”。但总是存在着玩家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网络的风险。例如,有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监视魔兽世界的玩家(以及其他网络游戏的玩家),担心他们利用网络策划恐怖袭击。事实上,威瑟福德和普特提出,认知资本主义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或正式的阶级抵抗的情况下,会从本质上破坏自身。他们写道:“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那些创造奇观的行业——所谓的文化或创意产业——受到自身逐利本性的驱动,制造并传播交流的工具……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削弱了资本对奇观权力的垄断”。“商业游戏文化”远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政治控制系统而存在,威瑟福德和普特总结道,“它还可能同时孵化一种系统仿真、自组织以及合作生产黑客玩家的文化,这些玩家能够寻求超越全球市场边缘之外的未来”。换句话说,对公司控制的抵制,出现在游戏玩家、黑客、“生产者”自发组成的自主网络中,还有一些人以非资本利益的方式使用数字商品和在线空间,因为资本本身提供以程序、游戏和网络空间的形式分发了生产资料。
正如我已经开始表明的那样,这种对电子游戏产业的解读——据说“当代经济生活正在变成玩一场游戏”(Dibbell,2006:23)——是基于非物质劳动和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在与后工人主义思想结盟的学者的著作中取得了最突出的进展,例如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保罗·维尔诺(Paulo Virno)、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20世纪60年代,作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替代品,出现在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或称为Workerism),认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生产和通信方面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性质的质变,特别是在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上。后工人主义运动的中心主张是,“当代历史关键时刻的特征是知识在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动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中心作用”(Vercellone,2007:13)。这样,数字技术给“资本和社会劳动过程的技术构成”带来了“质的变化”。这实际上意味着,“认知资本主义”被认为代表着一种从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向从以非物质劳动中提取剩余创造力为基础的制度的根本性转变,或者根据拉扎拉托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所说,非物质劳动是“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Lazzarato,1996:132)。后工人主义学者认为,利润不是通过雇佣劳动的剥削机制产生的,而是通过捕获免费劳动的创造力产生的。免费劳动包括从医疗保健人员、教师和服务业其他人员的情感劳动(Hardt and Negri,2000:290–294)到“建立网页、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建立虚拟空间等活动”(Terranova,2013:34)。每当用户为一款游戏创建了一个“游戏模组”(MOD,指的是游戏的一种修改或增强程序),注册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或者只是参与一个在线空间,他们就是在贡献非物质的“玩工”,基于时间付出和“情感”注入而产生利润。根据这种论点,这种对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划分的颠覆带来了“价值规律的危机”,因为尽管劳动“仍然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Vercellone,2007:30),但其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再以与生产直接相关的劳动时间来衡量”。
对于这样的学者而言,在数字经济中,资本对物质劳动的剥削已经让位于一种建立在对非物质劳动产生的文化共性控制之上的经济制度,这种共性包括“思想、信息、图像、知识、代码、语言、社会关系、情感等”(Hardt,2010:134–135),例如,正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在《共产主义的共性》(The Common in Communism)一文中提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大型工业在社会中占据着霸主地位”,但今天“工业不再将其特征强加于其他经济部门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上”。相反,哈特写道,“工业必须信息化:知识、代码和图像在整个传统生产领域正变得更加重要,情感和关怀的产生在评估过程变得愈发重要”,他接着说,资本主义的信息问题在于,“稀缺性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想法,与我分享并不会降低它对你的效用”。此外,只要思想的产生不局限于你工作的时间,信息经济的非物质性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工作日”中描述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分,这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石。哈特主张,随着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信息和情感的非物质商品——它们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被生产和消费,无论一个人是否在工作,在电子游戏理论中,尤其是当一个人不在工作时——创造性价值的产生超过了任何衡量它的机制。这种机制即是,资本代替阶级剥削,被简化为通过排他性契约机制从诸众中榨取“租金”的能力。无论是塞拉利昂的钻石矿、玻利维亚的水矿,还是“关于专利、版权、土著知识、遗传密码和种子种源信息的争论”。哈特提出,资本的目标不再是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而是控制后稀缺社会(postscarcity)的信息经济,甚至更广泛地说,控制生活条件本身。哈特宣称,“正如马克思看到运动必然战胜静止一样,今天,非物质战胜物质、可复制战胜不可复制、共享战胜排他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利润可以用马克思理论中的“工作日”来衡量,或者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别来衡量,那么,日益依赖于电子游戏玩家和Facebook用户自发创造力的数字文化经济的兴起,意味着“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劳动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Fuchs,2014:126)。因此,即使受到后工人主义运动影响的学者继续使用“阶级”或“剥削”这样的概念,但在他们的定义中,(劳动)并不是指一个人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是指在生产中缺乏物质基础的随时可能出现的权力和控制网络。

《僵尸资本主义》书封
然而,正如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在《僵尸资本主义》(Zombie Capitalism)中所解释的那样,对资本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产品的物理形式或对社会的有用性”(Harman,2010:122),也不是劳动力是否被用于“物质生产或今天被描述为‘服务’的东西”,而是其“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资本最关心的不是所讨论的商品是拯救生命的疫苗还是杀死数千人的炸弹,也不是一款新智能手机或运行它的软件,而是生产性劳动的剥削。在摒弃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将它们都视为“雇佣劳动拜物教”(Fuchs,2014:110)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评者将这两种劳动的区别简化为正式的就业问题——例如,工厂工人和服务工人——以此驳斥“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并用关于劳动的“道德”理论取而代之。在这样做时,他们提出的更具包容性的阶级理论掩盖了实际上存在争议的工人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问题。在最基本的条件下,生产性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因为它是直接增加资本价值的劳动。然而,非生产性劳动在经济体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对应于资本的再生产和循环,使新价值的生产得以持续。与批评家的主张相反,劳动价值论不是为了政治组织或道德评价而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而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和积累的。它阐明了为何剥削劳动塑造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具有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潜力。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劳动价值论,把劳动者划分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过来,模糊这些区别并不能为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基础,反而通过声称在所谓的后生产经济中可以使消费实践在生产条件之外运作,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展。
后工人主义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对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反工具化理解,它在观念层面再现了资本对技术和工作场所组织的不断更新。正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之下的技术进步,其目的是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剥削率。也就是说,人们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的产品越多,他们工作的时间也就越多地用于生产剩余价值。因此,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意味着结束匮乏,但也成为工人进一步异化,以及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和同事相异化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那样,“由于机器体系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产,产品同生产者的直接需要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从而同直接使用价值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1980:209-210)。工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求生存,因而他们不是为满足自身的需求而生产,而是被迫生产以扩大资本。这意味着,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技术进步就会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提高生产力,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看起来只不过是“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38)。因为他或她工作似乎是为了机器运转,而不是为了自身。然而,后工人主义运动所引发的幻想——人们可以通过利用“诸众的主体性”来“退出”劳资关系,这种主体性“不仅在技术上具有敏锐性、在文化上具有创造性,而且由于其技能、才能和欲望而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超出了帝国试图限制他们的用途”(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187)——以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结构的存在为起点,这使得“趣味的”消费行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伴随着知识去“玩”的能力以技术的扩展为前提,但技术本身并不能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技术创造的价值不会超过一美元魔术般地将自己变成两美元的价值。技术是过去劳动的产物,现在被劳动使用。反过来,假设游戏已经取代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并考虑到游戏跨越了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界限。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被简化为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局部和偶然关系,而非任何一种系统关系。换言之,作为反对帝国的非物质激进主义理论核心的主体性激活是如此分散且难以定义,这并不是因为它反映了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的,就像后工人主义理论家所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在颂扬消费是一种生产行为的过程中,后工人主义将所有这些要素——工作形式、生产的商品、消费商品的条件、生产意图和企业管理结构——混为一谈,最终导致了对资本主义混乱和过激的政治解读。即使就其本身而言,也无法解释谁在控制谁受到控制。

《魔兽世界》
我们可以研究需要玩家大量投入的游戏,例如MMO(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或开放世界的沙盒游戏,来清楚的认清上述论点。这些游戏——例如魔兽世界、我的世界或者即将推出的无人天空——通常都是以类似的功能为前提,即玩家被赋予一个世界的元素,正是玩家的决定塑造了这个世界的可能性。根据威瑟福德和普特的说法,诸如此类的游戏体现了革命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他们写道,“游戏越来越多地不仅涉及到玩世界,而且还涉及到创造世界”。他们接着指出,这模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因为“游戏中包含着越来越复杂的编辑工具,mod(游戏模组)和machinima(游戏电影)文化的兴起,以及对用户生成内容的推动,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意味着游戏玩家不仅在认知上参与绘制预先设定的游戏世界,而且还参与建立或至少调整他们的系统逻辑”。他们认为,“转向用户控制的内容”代表了一种激进的转变,因为“它在玩工和生产商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冲突”,因为“这相当于控制权的下放,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同样需要理解的是,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不是道德上的区分,而是对资本如何通过剥削劳动以此创造和侵占剩余价值的解释。为了让玩家能够使用MMO,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生产性劳动系统。为了解决这个系统中的一些元素,包括开发创建和玩游戏所需要的硬件、游戏代码本身的生产以及为用户提供访问在线组件的基础设施(以及工厂、学校和办公室的建造,收集最初创建电子游戏所需的稀有元素和其他商品)。继而,这些商品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营销商、分销商和零售商,他们利用非生产性工人的劳动来占有游戏生产过程中提取的部分剩余价值。他们为经济的生产性方面提供服务,并反过来从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中获得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没有什么可占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经济的生产方面——例如硬件制造商和游戏制造商——受益于非生产性劳动和“创造性”的消费行为,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了新价值,而是使更多从生产性劳动中提取的剩余价值能够作为利润实现,进而又使生产周期重新开始。游戏理论越是提倡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玩电子游戏是一种“激进”行为的理念,就会生产和销售更多的游戏,也就会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被资本榨取并作为私人利润实现。与其说非物质劳动理论被“激活”去反对资本主义的控制,不如说它将“创造性”消费行为本身称为激进,让游戏主体完全融入到剥削体系之中,同时想象自己在缺乏任何物质的情况下实现革命性的转变。这才是对电子游戏进行解读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扩张,而非撤退。
对“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的挪用,如果不是控诉左翼文化理论已经可悲地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阶级分析和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必要性,转而支持政治“系统调整”和没有组织或方向的自发抵抗,那么,描述玩电子游戏会是可笑的。当然,威瑟福德和普特也谈到在危险条件下开采稀有元素的矿工的待遇以及电子垃圾对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后果是建立在剥夺工人一切(除了他们的劳动力)的制度之上,这是从道德角度解读工人的工作条件,而不是关于雇佣劳动的剥削逻辑。即使是他们听起来最激进的言论,最终也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适度的改变。比如他们的论点“自组织文化的全部潜能只能在一个放宽商品化、支持更多共享和开发使用数字资源的系统中实现”。或者,他们认为所需要的是“更少的自由市场;权力更加分散、更民主的公共规划;更少的商品化和更多的公有化;更少的雇佣劳动和更多的自我管理;更少的掠夺性和更普遍地提供基本生活需要”。呼吁“放宽商品化”、“更少的雇佣劳动和更多的自我管理”,这再次强调的是改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后果,而非消除私有制本身。电子游戏产业并未改变资本主义,而是将资本主义关系扩展到商品生产的新途径。假设“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从而消除资本对固定资本中客观化的一般社会知识的垄断”(Koloğlugil,2015:132)。只是在这方面有帮助。提出游戏玩家的剩余创造力代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观念,并不是对私有制意识形态的挑战,而是将这种剩余创造力从物质领域抽离出来,放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因此,被激活的非物质劳动的主体是一名工人,他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价值的来源是创造力而非劳动力。基于此,他/她会寻找能够欣赏他/她作为创造性工作者的价值的工作场所,以换取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独立于监督。事实上,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美国科技行业背后所谓的自由主义理念。换句话说,像电子游戏文化一样,以优步和爱彼迎为代表的所谓共享经济,打着给有创造力的员工更多“自由”的幌子,让他们可以选择工作时间和方式。同时废除为工人提供了重要但有限保护的健康、安全和工作法规。这反映了资本试图让劳动者相信“创造力”和“玩”文化超越了经济机制,因此代表着阶级和工资剥削等结构的终结。然而,就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它是通过将工资说成是代表着或多或少“公平”时间的交换,从而掩盖对劳动力的剥削。
从这个意义上说,威瑟福德和普特对“放宽商品化”和“分权规划”的呼吁,与亚马逊和美国鞋类电商网站Zappos最近公布的企业文化差异存在相似之处。虽然亚马逊的工作文化在更多的工业术语中被描述为进行一项鲜为人知的实验,以了解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白领工人,重新划定可接受的界限。方法是通过使用一套自我强化的管理、数据和心理工具,激励成千上万的白领员工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这就把员工变成“自动机器人”(Ambots),由于压力,他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哭泣。而Zappos的工作文化被描述为“传统等级制度”消失的地方,经理不再存在。该公司的1500名员工定义自己的工作,任何人都可以设定会议议程。在现实中,亚马逊和Zappos(实际是亚马逊的子公司之一)管理风格之间的这种“冲突”表明,资本主义在工作日组织方面的“灵活”程度,只要不改变利润的基本结构,即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自治和分权是可以恢复的。
二、科学、劳动和一般智力
非物质劳动理论建立在关于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之上,该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业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Hardt and Negri,2000:364)。 以至于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劳动价值论被认为不再有效。例如,保罗·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一书中提出,“劳动社会的危机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财富来自科学、来自普遍智能,而不是来自个人提供的工作”(Virno,2004:101)。也就是说,就价值的源泉而言,是创造力而非劳动力。维尔诺认为,“劳动和非劳动显示出完全相同的生产力形式:语言、记忆、社交、伦理和审美爱好、抽象思考和学习等的能力”(Virno,2004:103)。同样,安东尼奥·奈格里在《艺术与诸众》(Art and Multitude)一书中写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不再有任何“丝毫区别”,因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吸收诸众的“潜能”,以“以便否认其生成独一的可能性,否认其对某人或某物的有效性”(Negri,2011:18)。换言之,在非物质经济中,个人所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成为资本“价值”的潜在来源,这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生产性劳动,而是因为价值是通过资本对生活和对劳动的控制程度来衡量的。简言之,资本变成了一种政治关系,而不是一种经济关系。
维尔诺和奈格里都声称,马克思《大纲》(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断”是非物质生产理论的理论基础。在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论述时,马克思在这个片段中指出,新技术的发展水平表明了“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198)。维尔诺和奈格里之所以对科学在更广泛的经济中发挥作用的这种表述着迷,是因为“一般智力”的出现代表了这样一个时刻,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通过减少“直接劳动”的程度来支持“一般科学工作”,即自然科学的技术应用,以及“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一般生产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维尔诺写道,“尽管物品的物质生产交付给了机器的自动化系统,而由活劳动提供的服务却越来越像语言艺术的服务”(Virno,2004:58)。这些服务没有任何最终产品,依靠来自思想流通而非商品生产的“丰富可能性”(Virno,2004:70),所谓的“价值规律”被“被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瓦解和驳倒”(Virno,2004:100)。同样,奈格里写道,“在后福特主义里,活生生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正变得越来越非物质,越来越协作化。但在实际的情境中,智力和协作同样越来越不可能被包含于价值生产的世界秩序”(Negri,2011:94)。换言之,资本不再能够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价值,因为他们声称,“认知”或“ludo”(来源于拉丁语Ludus,意思为游戏game或玩play)经济主要依靠创造力而非劳动力。
资本在通过技术发展简单地消除了(限制)自身的存在基础之后,如僵尸一般继续存在。维尔诺和奈格里提出,作为一种政治控制体系,而非经济体系,资本通过工具性的手段强加一种文化“普遍性”。用奈格里的话说,这种普遍性“必然以战争和一切类型的毁灭为基础”(Negri,2011:85)。进而,鉴于除了意识形态之外,资本不再有任何基础,而且由于劳动本身在生活条件的生产中不再具有物质地位。两位作者的结论基本相同,即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不再取决于“夺取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或者新的政治决策垄断权”(Virno,2004:43),而是取决于被定义为“叛离之行动的形象——要去寻求潜能和欢乐”(Negri,2011:95)。以“从一个只承认现有世界的世界内部进行,并且,那个世界知道有待建构的‘外部’只能是一个绝对内部的他者”(Negri,2011:108)。换言之,对于后工人主义思想而言,技术已经使劳动成为资本功能的多余部分。因此,因此,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干脆选择退出现有的东西,而不必担心革命的“杂乱”之事。
威瑟福德和普特也依赖于对马克思一般智力理论的后工人主义解读,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电子游戏上,以此作为劳动价值论失效的标志,并创造了“退出帝国的社会转型”(Dyer-Witheford and de Peuter,2009:218)的条件。他们写道,“就像许多历史上的生产形式都需要集体劳动力一样,今天,集体智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作直接的生产力”。他们认为,这种集体智能的力量是“通信技术”的方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协作和知识共享”。然而,他们继续说,“帝国的赌注是,在资本主义的‘知识经济’中,一般智力可以被吸收到世界市场的结构中”。事实上,“免费和开源软件的生产和分发,利用数字网络促进各种形式的团结经济,以及模拟开发以协助民主化的环境和社会规划等例子,都是网络通信的一般智力用于超越世界市场及其营利性优先事项的方式”。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技术网络现在的功能就像工厂车间一样,但工厂车间将无产阶级聚集在一起,而在线网络游戏则将“玩家—阶级”聚集在一起。虽然无产阶级具有革命潜力,并且可以夺取生产资料,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为资本提供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但对于威瑟福德和普特而言,认知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方案”不是集体夺取权力,而是通过创造替代的、合作的个体自治空间,大规模地“逃离”现有的社会。

2022年4月17日,英国伯明翰,当地举行一年一度的失眠游戏嘉年华,失眠游戏嘉年华是英国规模最大的游戏节之一,游戏爱好者们在4天内能接触到最新的VR设备和游戏作品。主办方还邀请了顶尖游戏选手现场竞技一决高下,在场观众将会获得相当有趣的游戏体验。
维尔诺、奈格里、威瑟福德和普特都称赞电子游戏等数字技术代表着“玩家—阶级”通过从“认知剥削”的政治控制中退出而夺回“玩”的乐趣。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关于工作的政治理论,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所采取的现象学形式,而不是其潜在的经济逻辑。它是对资本主义工作场所所具有的工具性的抵制,但也是对生产的实际经济逻辑的完全模糊。在宣扬电子游戏等数字技术代表着资本主义内部超出以往时刻的形象时,他们重写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作为正式的矛盾。在其中,工作的工具性受到游戏的后工具性的挑战,对劳动的经济贬值被对创造力的道德重估所取代。人们在谷歌、脸书、微软、索尼等公司的办公楼发现通用的反工具逻辑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公司,员工可以免费用餐、玩电子游戏放松、乘坐上下班班车、享受干洗店、运动和锻炼设施、医疗保健中心的服务,以及在工作期间留出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不是由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技术或公司组织来定义的,而是由马克思定义生产关系的理论来阐明的:即劳动价值论。正如后工人主义学者所提议的那样,简单地在资本主义内部创建具有共同创造力的替代性共同体,并不会对资本主义构成任何严重挑战。因为它保留了决定消费形式和条件的生产逻辑。事实上,这是最先进的资本部门的论点,他们寻求找到新的劳动组织方式——有时不仅采用“玩家—黑客”的心态,而且还采用侵入和窃取其他公司信息的实际做法——同时也掩盖了定义雇佣劳动的基本剥削。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他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对马克思而言,科学技术问题不能脱离对生产方式的形成和改造特别是资本主义剥削条件的研究。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始终具有社会性。正如他所论述的那样,资本的驱动力是积累利润,这是由于剩余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再生产所必需时间的延长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技术创造价值的能力只在两方面是可能的:“(1)由于固定资本具有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形式上的一定的劳动量;(2)由于固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使劳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大量的维持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192)。换言之,技术始终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受制于使用劳动的生产条件。人们只能从技术社会本身看到这一点。这样,虽然资本代表着一种“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但它不能像后工人主义理论家奈格里、维尔诺、威瑟福德和普特等人所说的那样,仅仅通过技术发展来实现(资本)自身的解体,因为“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资本才采用机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概念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这不应该被解读为像后工人主义思想所暗示的那样,标志着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来源的劳动剥削的内部瓦解和消失。相反,我认为人们应该采用类似于马克思用来解释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全球文化发展的术语来解读“一般智力”,即“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的出现。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劳动集体性与社会变革潜力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表述,“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34-35)。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把所有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包含在自身内部,直到剩下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差异。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促成了他们所说的“世界文学”的产生,或一种互动和交流的全球文化。同样,正如资本主义在全球商品关系的扩张中产生了“世界文学”一样,它也催生了“一般智力”,这标志着以思想和技术为形式的人类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生产条件。
因此,一般智力是资本主义基本阶级矛盾的标志,而不是它的解体。这正是这种历史的和物质的矛盾在科学层面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大纲》中写道,资本主义越是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和深化商品生产体系,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186-187)——即人类的“一般智力”——“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一般智力之所以具有独立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不是作为劳动的产物,而是作为资本利益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是在资本私有的条件下使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技术——即劳动的产品,而不是它们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今天最常被庆祝为人类的成功,或者反过来被指责为金融危机和失业等社会动荡现象的罪魁祸首。这种技术庆典并未反映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事件实际上是技术作为一种自主力量的效果。相反,这种庆祝式的解读表明了生产关系已经变得模糊到了什么程度。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资本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这一事件,使得劳动力看起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指令似乎来自技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要求加速、生产更多产品和更努力地工作。技术是劳动的社会体现,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变成了反对劳动的武器。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使社会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34)。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资本家)将生产力提高到商品被毁坏和人为淘汰,数百万人挨饿的地步,充分说明了劳动生产率与其对利润动力的限制之间的现实矛盾。
三、结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活水平下降之间的危机的最有效方式。虽然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近60%,企业利润在同一时间框架内增长了20%以上,但这是由于新技术的引入,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需求和成本。与此同时,北半球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我们被告知,两位数(实际)失业率很可能是“新常态”(Gilson,2011)。这些矛盾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马克思所写,“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195)。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发展,只要它加深了剥削条件,就代表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劳资矛盾的消解。
相比之下,与电子游戏行业作为自我解体的资本主义或依赖于“玩”思想而非劳动的资本主义形象相反,工人在工作时间或下班后的创造力和“玩”可能表达了对异化劳动的反感,正如马克思写道,“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但这种“玩”取决于在利润动机下组织起来的商品和服务的劳动,有助于扩展产生这种异化的剥削条件。事实上,人们在后工人主义思想发现的“独一性的诸众”(Negri,2011:23)反对“还原为一个价格”——或者个体对资本主义同质化文化机器的愤怒——的斗争形象,最终与人们在所谓“创意阶层”的想法中发现的企业逻辑是相同的。对他们而言,开放式平面图、免费食物和其他非正式活动意味着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这种结构在剥削劳动的同时也“尊重”劳动。
换言之,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用来加强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对象化劳动。虽然资本主义不能不增加对人类一般智力的科技“教育”,但它自身的矛盾却不断地使这种智力沦为通过加剧剥削而强化进一步追求利润的动机。虽然“玩家”理论使工人的注意力从必要的(时间)自由转移开,转而支持思想的非物质自由,但只有将从以利润为基础的社会转变为以需要为基础的社会,剥削才能结束。
*本文英文版原刊《明尼苏达书评(minnesota review)》第87期(2016年),原标题为“Gaming Labor:Class, Video Games, and the ‘General Intellect’”,作者罗伯特·威尔基(Rob Wilkie)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英文系,中译得到作者授权,译者杨雷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
参考文献
Benkler, Yochai. 2006.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Berardi, Franco. 2012. The Uprising: On Poetry and Finance. Los Angeles: Semiotext(e).
Boutang, Yann Moulier.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Ed Emery.Malden, MA: Polity.
Chatfield, Tom. 2010. Fun Inc.: Why Gaming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Pegasus.
Dibbell, Julian. 2006. Play Money, or How I Quit My Day Job and Made Millions Trading Virtual Loot. New York: Basic.
Dyer-Witheford, Nick, and Greig de Peuter. 2009. 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Gelles, David. 2015. “At Zappos, Pushing Shoes and a Vision.” New York Times, July 17, nytimes/2015/07/19/business/at-zappos-selling-shoes-and-a-vision.html.
Hardt, Michael. 2010. “The Common in Communism.” In The Idea of Communism, edited by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Žižek, 131–44. London: Verso.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man, Chris. 2010. Zombie Capitalism: Global Crisis and the Relevance of Marx.Chicago: Haymarket.
Koloğlugil, Serhat. 2015. “Digitizing Karl Marx: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General Intellect and Immaterial Labor.” Rethinking Marxism 27, no. 1:123–37.
Lazzarato, Maurizio. 1996. “Immaterial Labo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Potential Politics,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32–4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azzarato, Maurizio. 2014.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Translated by Joshua David Jorda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Marx, Karl. 1986.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58. Vol. 28 of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Translated by Ernst Wangerman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87.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57–1585. Vol. 29 of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Translated by Victor Schnittke and Yuri Sdobnikov.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94.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1861–1863. Vol. 34 of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996. Capital, Volume I. Vol. 35 of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976.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6, 476–5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azzi, Christian. 2011. Capital and Affects: The Politics of the Language Economy. Translated by Giuseppina Mecchia. Los Angeles: Semiotext(e).
Negri, Antonio. 1991.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Edited by Jim Fleming. Translated by Harry Cleaver, Michael Ryan, and Maurizio Viano.New York: Autonomedia.
Negri, Antonio. 2011. Art and Multitude: Nine Letters on Art, Followed by Metamorphoses:Art and Immaterial Labour. Translated by Ed Emery. Cambridge: Polity.
Peters, Michael A., and Ergin Bulut. 2011.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apitalism,Education, and Digital Labor, edited by Michael A. Peters and Ergin Bulut,xxv–xxiiii. New York: Lang.
Shirky, Clay. 2010.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New York: Penguin.
Terranova, Tiziana. 2004. 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Terranova, Tiziana. 2013. “Free Labor.” In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edited by Trebor Scholz, 33–57. New York: Routledge.
Vercellone, Carlo. 2007.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o. 15: 13–36.
Virno, Paolo. 2004.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lated by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Los Angeles: Semiotext(e).
Wark, McKenzie. 2007. Gamer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rk, McKenzie. 2013. “Considerations on a Hacker Manifesto.” In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edited by Trebor Scholz, 67–75. New York: Routledge.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