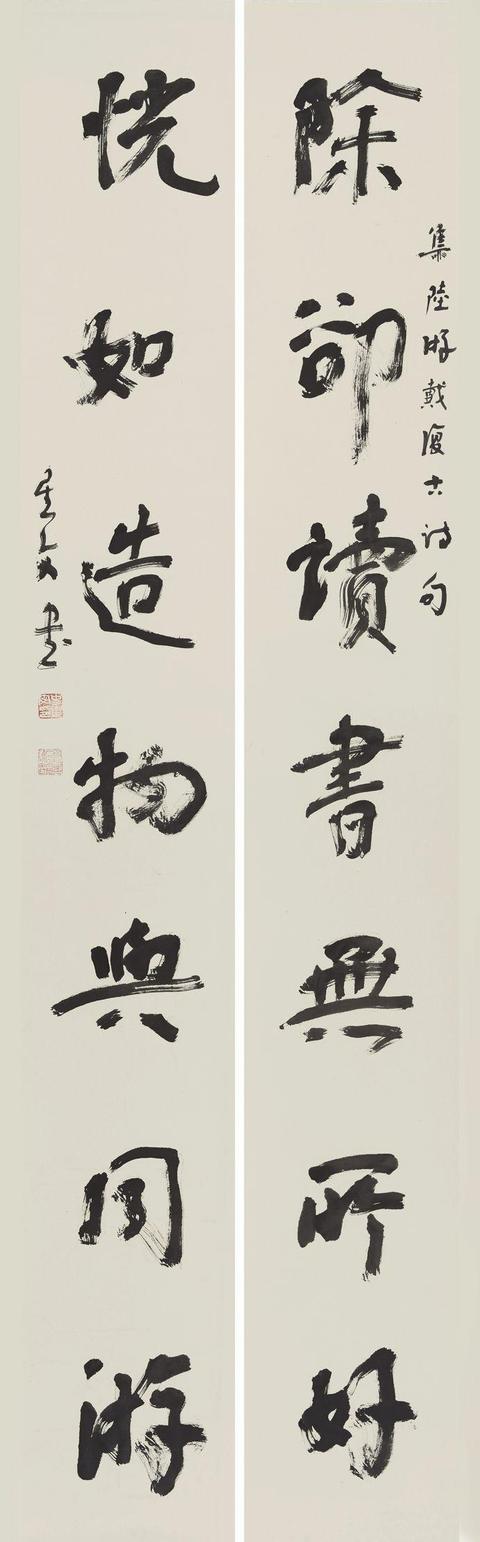
冬天的太阳
冬天天气奇冷,我一直为住在乡下的父亲担忧。父亲年近八旬,农村生活苦,父亲在冬季能过得好吗?
我一直为我的所谓事业惨淡经营,自知缺乏天赋,但还是痴迷不弃,只是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期望能有所收获,这就常常给生活留下许多缺憾。我三天两头给家里打电话,问家里一切可好。母亲说:“一切都好着哩!”我放心了。
遇一个好天气我回到老家,进门见父亲在炕上半躺着休息,额头贴着一大块油污的纱布。我问父亲怎么了?母亲这才告诉我,二十多天前父亲想出门,腿脚不利索没有迈过台阶被绊倒了,父亲说没事一直不让告诉我。这时,父亲对我说,现在好了,一点也不疼了,他还拉住我的手在额头摸了摸,竟若无其事地笑了。
天不刮风,太阳很好,我扶父亲到院子晒太阳。父亲穿着棉衣外面又披着大衣,但在阳光下还只是瑟缩着;我知道父亲身上没有多少热量,像这冬天的太阳经不住一点儿风吹。
我和父亲晒着太阳,说着多年的那些老话。渐渐地,父亲暖和过来了,脸上有了红润颜色。父亲说:“今天太阳好,一冬天就数今天的太阳好!”
我果然感到浑身暖烘烘的,望着父亲,我随手解开了一冬天都不曾松动的领扣。
我一直生活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里。我一直生活在父母亲播撒的阳光里。我就一直想着等我退休了回我的故乡去陪父母,重温往昔那些悠长而温馨的日子。然而岁月无情,2006年冬天,父亲突然患了“脑梗”,多亏治疗及时,康复得也快,生活很快也能自理,父亲拄上拐杖也能到街巷和田野里转了。然而时隔三年,眼看就是春节将至,突然的一次重感冒彻底击垮了父亲,父亲全身器官迅速衰竭,医院乏术,我们于无奈中只有深深地悲伤着。而此时的父亲却非常淡定,也非常清醒。我赶紧回老家为父亲箍墓,准备后事。后来,当母亲小心翼翼地将箍墓的事告诉给他时,没想到一生胆小的父亲脸上竟浮出了笑意。他决意回家,一刻也不愿在医院多停留了。2008年腊月二十日黎明时分,我从北京开完会坐火车回西安。途经渭南时,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父亲躺在老家的土炕上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就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紧接着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是妹妹的声音,她抽泣着告诉我:“父亲不在了!”父亲不在了?!我的眼泪唰地就淌了下来。我在西安下了火车又乘火车往渭南赶。我遗憾着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没能与父亲说上最后一句话。火车的每次哐啷声都重重地撞击在我的心上。
我一回到家就扑倒在地,紧紧地抱住父亲那双瘦骨嶙峋的双腿——这是一生都在匆忙奔走的双腿,然而这双腿再也不能站起来行走了。我完全还像当年那个孩子一般依偎着父亲,望着安详如睡的父亲,我一遍又一遍地诉说着心中的悲伤与悔痛。妹妹哭着告诉我,几天来父亲约见了他挂念的所有亲朋,反复叮咛要将院子打扫干净,临走的昨天晚上,还让给他从纸活店里买一匹白马。妹妹从纸活店将白马买回来了,父亲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父亲就像平常一样闭上双眼睡着了,这一觉竟成了长眠。父亲是骑着那匹大白马去了天堂。
父亲本姓程,他是外乡人。父亲自小没了父亲,他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刚刚十二岁那年,父亲就跟村里大人去西安一家纺纱厂当了童工,不为挣钱,完全是为了找口饭吃。父亲成年后,就来了我们这个村子。父亲一来就将根扎下了。多少年艰难困苦,多少年风霜雨雪,父亲一直咬着牙扛着生活往前走。父亲出身贫寒,心地善良,在村里赢得了很好的人缘。父亲出殡的那天早晨,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那是入冬以来难得的一次下雪,村里人感慨地说:“老天动容,在为这个好人送行了!”
母亲幼年丧母。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棵草。母亲苦命。母亲虽然没上过学,但母亲聪慧,爱干净,又会持家。她没有片刻闲暇,一年到头缝衣、做饭、纺线、织布等等。我一直不知道母亲是何时休息的。白天她要下地干活,只有将家务活放在了夜晚和空闲时,那纺车的嗡嗡声和织布机的哐啷声一直伴随着我。一大早我起床去上学,母亲却还没有休息,她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我下面本来是有一个弟弟的,不料弟弟得了“四六风”早早就夭亡了,母亲就为一家姓韩的人家奶养了一个孩子,那孩子叫韩建民。母亲后来用养孩子所得的一点养育费和周借来的一点钱买了一台缝纫机,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裁剪缝补衣服,靠为别人裁剪缝补衣服所得的微薄收入补贴家用。母亲常常提起她养育的那个孩子,想起那孩子就抹眼泪。当我后来读到诗人艾青写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时,就不由得想起我的母亲,母亲就是那个保姆,我就常常禁不住泪流满面。
父亲是靠山,父亲是顶梁柱,父亲是遮风挡雨的墙。父亲走了,母亲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紧跟着大脑迅速萎缩,以至人事颠倒,连生活也无法自理。母亲是在糊里糊涂中离世的,这给儿女们留下了永远的哀痛。
母亲离世后的那年秋天,我去四川看望母亲唯一的姐姐,我一直亲切地叫她作大姑。大姑是我们长辈里唯一的亲人了。大姑年近九旬,行动不便,但思维却很清楚,我们一直瞒着她没有告诉她我母亲去世的事。一见大姑的面,大姑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让你妈也过来吧,我想和你妈说说话!”我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只是无声地流淌。
父母亲在,家就在,父母亲不在,家就没了。我心中那不断剥蚀的院墙终于坍塌了。没了父母亲的关爱和庇护,漫漫人生,我只能独自面对风雨了。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