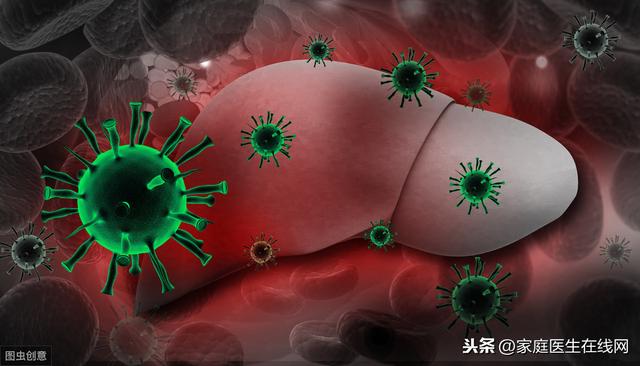1947年6月28日,艳阳高照,知了声声,盛夏的北平城人流如织。《新民报》的两位记者走进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四合院,黑漆的大门残迹斑斑,门口挂着某某医寓的铜牌子,大门的顶棚支离破碎,门内横陈着大小多种腌菜瓮,一切杂乱而热闹。他们进入北屋,看到一位头发斑白、面目浮肿、艰难喘气的瘦小老妇躺在床上,身边同样头发斑白的一位老妇坐在屋内,用绍兴方言拉着家常。躺在床上的老妇便是鲁迅的遗孀朱安女士,另一位老妇是侍奉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女佣王妈。
记者向朱安说明来意,朱安端详了两分钟之久,方才肯定的说:“失认得很”。然后瘦削的脸上浮起一丝笑容,说道:“请坐,谢谢大家的惦记。”她随后讲述了自己的病状:“我的病没有好的希望了。周身浮肿,关节发炎,因为没钱,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先生的遗物,我宁死也不愿变卖,我尽我自己的心。”她还说,王妈来周家二十几年了,一直陪伴着她,忠诚而忍耐,否则的话,她早就死了。
她又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海婴很聪明,有机会的话,我想见到他。”
记者随后参观了鲁迅的书房和亲手种植的树木,朱安说,樱花树去年被虫子咬坏了,只好砍掉。杨桃长得绿叶森森,遮盖住半个院子。记者临走跟朱安告别,朱安连声说着“再见,再见。”
记者走后,朱安让王妈请来一位姓宋的女士,专门交代两件事,特意嘱咐宋女士一定要转告远在上海的许广平。第一,灵柩想回上海葬在大先生旁边。第二、每七须供水饭,五七要请和尚念经。她一边说一边哭,念叨着鲁迅的名字,海婴的名字,许广平的名字,宋女士听了,非常心酸。
当晚,朱安撒手人寰,享年69岁。

早在1947年3月,自知时日无多的朱安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经病了三个多月,病势与日俱增。西医看过,没有见好,改由中医诊治,云系心脏衰竭,年老病深不易医治。自想若不能好,也不想住医院。身后寿材须好,也无须在北平长留,至上海与大先生合葬。海婴不在身边,两位侄儿我也不想找他们。”
朱安死后,她的丧事遵照鲁迅“埋掉、拉倒”的意旨,一切从简,她心心念念的孝子戴孝(指海婴。她是旧时代的“遗物”,满脑子都是陈腐的传统观念。以为自己是鲁迅正室,许广平是偏房,因此偏房所出要给正室戴孝。所以她不让侄儿料理后事,希望许广平和海婴料理。周海婴先生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也说,朱安女士一直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看待。),上好寿材(当时物价飞涨,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吃饭都是问题,上好寿材根本买不起,也没人给她买。),每七供饭(人死后要供水饭七七四十九天,但是这些都是儿女们应该做的事,她没有后代,所以这些也就无从谈起。)等等都没有实现,人们看她可怜,在她死后第二天还是请和尚念了念往生咒。本来想把她埋在周母墓边,可惜未能如愿,只好埋在了西直门外保福寺。后来保福寺附近大兴土木,绝大多数坟墓被毁,朱安坟墓也在其中。
朱安死后,有人写了《鲁迅夫人朱安小传》,登在报上,其中写道: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而聪慧,工女红,守礼法,柔声淑色,晨昏定省,侍奉太夫人鲁氏数十年如一日。夫人以女子无才为德,因不识字,又无所出,故其夫鲁迅,常卜居春申(即上海,小编注。),夫人以善从为顺,初无怨尤。迨(抗战)胜利后,米珠薪桂,几无以自存。呜呼,夫人生依无价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物价杀人,识字者已朝不保夕,彼又安得不贫困而死哉。
这篇传记主要说了一个意思:朱安晚年过得非常贫困,最终贫困而死。而贫困的根源,便是她生前嫁了“无价”的文人。这里的无价,不是无价之宝的意思,而是无有身价的意思。意即鲁迅去世后没有给她留下多少财物。接着记者说,“识字者已朝不保夕”,意即活着的文人,也挣扎在死亡线上。
当时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教书,家里穷得连过冬的煤都买不起,季羡林正在北大教书,找到校长胡适,胡适想送陈寅恪一笔美元,陈寅恪坚决不收,经过朋友们斡旋,陈寅恪把珍藏多年的孤本书籍卖给胡适,得了两千美元,方才度过危机。朱安的远房侄儿,也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朱自清,便因病饿而死。
朱安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曾想过变卖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生活困苦之极的朱安在周作人建议下,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周作人让北京图书馆开列藏书目录,并且委托来薰阁出售。许广平闻讯,忧心如焚,赶紧写信劝止朱安:我知道你一定是生活非常困难,不得已才这么做。鲁迅先生死了以后,人们都可惜他,纪念他,他在上海留下的书籍、衣服、什物,我总极力保存,不愿有些微损失。至于你的生活,鲁迅先生死后六七年间,我已经照他生前一样设法维持,从没有一天中断。直至我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汇兑不便,熟托的朋友又不在北平,方才断了接济。

鲁迅先生没有几个亲属,你年纪又那么大了,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一定想方设法汇款。你一个月最低生活费需要多少,请实在告诉我,我尽量筹措。虽然我这里生活比你困难得多,你住自己的房子,我租房;你一个人,我两个人。你旁边有作人二叔,他有财力,有地位,比我们旁边建人三叔清贫自顾不暇好得多。
鲁迅生前好友内山完造也写信劝止朱安,朱安回信道:我侍奉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今年也已经66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依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非常宝贵的。无奈一天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求之不得,又何苦出此下策呢?
与此同时,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也委托鲁迅的几位生前好友前往北平劝阻朱安,时已黄昏,朱安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闻知来意,沉默良久,忽然大喊道,你们总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当然她说的是一时激愤之语。当来人说起许广平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以及日子过得同样艰难时,她冷静下来,说道,海婴是大先生唯一的骨肉,既然他们这么难,为啥不来北平呢。
当时周作人一个月给朱安150元生活费,来人表示给得太少了,朱安说,大先生生前,没要过老二一分钱。150元我不要,我没有办法,才卖书。我身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指周母鲁氏)怎么说,我怎么办,绝不违背。
1945年年末,《世界日报》两位记者前来采访朱安,正好赶上她吃饭。多半个小米面窝头,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小手指粗的白面做的短面条(即拨鱼子),另外是一碟虾油小黄瓜,一碟虾油尖辣椒,一碟腌白菜,一碟霉豆腐。没有油也没有肉。朱安头发花白,面色蜡黄,只有两只眼睛,忽闪着光芒。她没有收来人的钱,因为她的生活一向是靠许广平接济的,没有许广平的同意,别人的资助一概拒绝,“宁自苦,不愿苟取。”
两位记者于是给许广平写信,许广平回信说,谢谢你们关心鲁迅家属的生活,但是我会尽力解决的,你们的好意心领了。
1946年8月,朱安给海婴写信,北平最近物价大涨,大米七百多元一斤,白面六百多元一斤,小米三百多元一斤,玉米面二百多元一斤,煤球一百斤两千六百多元,劈柴一百多元一斤。我们每天最少要吃两斤粮食,别的零用还不算。房子也要修理,昨天瓦工看过,最低要三万余元。以前每月五十元,还可以够花,现在只能买一个烧饼,真有点天渊之别。
1947年除夕,北平城下了罕见的大雪,积雪深达三尺,天气异常寒冷。病重的朱安全身浮肿,呼吸困难,“一开始晚上气喘,后来早上也喘,再后来整日喘气”,饭也吃不下,“两条腿冰冷得几乎不是自己的了”,非常可怜。探望过她的人都想,还不如赶紧死了,省得活受罪。她自己也说:“想死又死不掉。”
临终前不久,朱安自知时日无多,于是列了一个遗物清单,又列了一个送人衣物清单,其中有“白汗玉七块、翡翠镯一对、房契单一张”等贵重物品。她经常梦到自己的亲人,时时胡言乱语。死后,记者在报纸上写道:朱夫人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

朱安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但是关于她的故事,一直以来却鲜为人知。但是她在鲁迅的生活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回避了她,对鲁迅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有鉴于此,著名鲁迅研究作家乔丽华女士历时十余年,阅读了大量资料,走访了大量知情人,勘探了大量故迹,写成了这本《朱安传》,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朱安的完整传记,杨绛先生看完以后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并且说道:这本书定能成为常销的畅销书。本书精装正版,随书送杨绛先生手写书信。
喜欢鲁迅先生的朋友可以买一本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