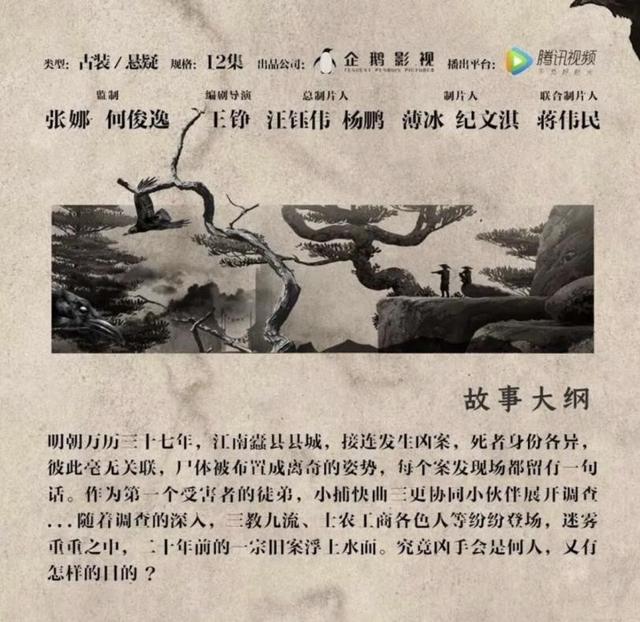打开书柜,抽出一本曾经被我翻看了不知多少遍的《放歌集》,再次读了起来。
《放歌集》的作者贺敬之,是我最为仰慕的当代诗人之一。
贺敬之是山东枣庄市峄县人,1937年日寇南侵,13岁的贺敬之随学校流亡到湖北均县,在湖北国立第六中学学习。之后,又随校迁入四川绵阳,并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夏,贺敬之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到华北工作。1945年,21岁的贺敬之根据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这部歌剧通过雇农之女喜儿遭受地主黄世仁摧残后逃进深山变成白毛女的传奇故事,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的旧社会,在解放区引起巨大的轰动。后来,这部歌剧还荣获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先后担任《剧本》与《诗刊》杂志编委、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贺敬之的主要作品除了歌剧《白毛女》,还有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这些诗歌紧跟时代的节拍,放歌伟大的祖国。贺敬之的诗在艺术形式上注重把新诗自由体与旧体诗的排比对称和谐统一,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些诗作均感情深厚,语言质朴,皆脍炙人口。
比如他在《三门峡——梳妆台》这首诗中,纵情放怀: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之水天上来!”
神门险,鬼门窄,
人门以上百丈崖。
黄水劈门千声雷,
狂风万里走东海。
望三门,三门开:
黄河东去不回来。
昆仑山高邙山矮,
禹王马蹄长青苔。
马去“门”开不见家,
门旁空留“梳妆台”。
梳妆台啊,千万载,
梳妆台上何人在?
乌云遮明镜,
黄水吞金钗。
但见那:辈辈艄工洒泪去,
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
梳妆来啊,梳妆来!
——黄河女儿头发白。
挽断“白发三千丈”,
愁杀黄河万年灾!
登三门,向东海:
问我青春何时来?!
何时来啊,何时来?……
——盘古生我新一代!
举红旗,天地开,
史书万卷脚下踩。
大笔大字写新篇:
社会主义——我们来!
我们来呵,我们来,
昆仑山惊邙山呆:
展我治黄河万里图,
先扎黄河腰中带——
神门平,鬼门削,
人门三声化尘埃!
望三门,门不在,
明日要看水闸开。
责令李白改诗句:
“黄河之水‘手中’来!”
银河星光落天下,
清水清风走东海。
走东海,去又来,
讨回黄河万年债!
黄河女儿容颜改,
为你重整梳妆台。
青天悬明镜,
湖水映光彩——
黄河女儿梳妆来!
梳妆来呵,梳妆来!
百花任你戴,
春光任你采,
万里锦绣任你裁!
三门闸工正年少,
幸福闸门为你开。
并肩挽手唱高歌呵,
无限青春向未来!
1958年初,贺敬之有感于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而创作了这组诗歌。诗人以豪迈之气,面向历史的超越之志,全面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治理黄河的伟大事业中的英雄气概,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诗人通过对三门峡及黄河东流入海的雄壮气势的描述,为时代而欢呼、为人民而歌唱。此诗以“黄河女儿梳妆来”为核心句,以句的反复为主要方式,让诗人的热烈情感得以尽情地发挥。诗作的用词以口语为主,摈弃诘屈聱牙的陈旧词汇,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词汇,使全诗得以意境崇高。同时,作者借用诗人李白《将进酒》一诗,却有所提升,体现了新时代诗人的心胸和诗性思维。全诗充满正气,读后催人奋进,在青年中广为流传,被称为当时人们学习写作现代诗的经典范本。
贺敬之绝非一位只喊口号的诗人,他所写的抒情诗极为感人。尤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他的诗作中,毫无忸怩作态无病呻吟的病夫之态,也没有半点无聊惆怅的小资情怀,而是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充满对新时代的颂扬。就连他在写景的诗作中,也无不处处流露出他欣喜面对新社会的胸怀。比如在《桂林山水歌》中,诗人是这样吟咏的: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
水绕山环桂林城……
是山城呵,是水城?
都在青山绿水中……
此山此水入胸怀,
此时此身何处来?
……
黄河的浪涛塞外的风。
此来关山千万重。
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
“桂林山水甲天下”
……
是梦境呵,是仙境?
此时身在独秀峰!
心是醉呵,还是醒?
水迎山接入画屏!
而诗歌《回延安》,更是贺敬之的经典之作。这首写于1956年的抒情诗,尽情地展示了诗人回到阔别十年的延安时的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贡献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全诗采用陕北信天游的形式,语言生动质朴,感情炽热而强烈。
一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进亲人怀。
二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分别十年又回家中。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三
米酒油馍木炭火,
团团围定炕上坐。
满窑里围得不透风,
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
“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
亲人见了亲人面,
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
“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
白头发添了几根根。”
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
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
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
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
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
长江大河起浪花。
十年来革命大发展,
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四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
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
头顶着蓝天大明镜,
延安城照在我心中: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
一座座楼房披彩虹;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五
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
革命万里起浪潮!
宝塔山下留脚印,
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
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
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
再回延安看母亲!
全诗共五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拭目远望”、“手抓黄土我不放”,时而进入梦境,时而又回到现实,突显作者回到延安时的激动心情。古人在形容感情的逐渐强化时曾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人此刻“手抓黄土我不放”的急切形体动作,比嗟叹永歌、手舞足蹈更为强烈,确是远方归来的人一旦重新踏上故土以后才会有的特定表现,能够迅速地引导读者进入诗人所描述的情景之中。
诗的第二部分,诗人的感情渐趋平稳,开始向各个方位延伸。诗人没有平铺直述地记述过去,而是选取了当年若干生活细节,如“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如“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诗人和战友们在延安参加大生产的场面立刻出现在眼前,把一件件往事刻划得鲜明单纯,亲切感人,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诗的第三部分,勾勒了老少三辈的团聚。有气喘吁吁地跑进门来的老爷爷,有从当年的放羊娃成长起来的社主任,有争着把手拉的娃娃们,诗人在描写他们的的同时,又有概括的形容:“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这样既有人物描写,朴素自然,把一场老少的团聚写得绘声绘色,流露出温馨深厚的情谊。
诗的第四部分描写延安新貌,第五部分展望美好明天,最后以“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结尾,和开头刚到延安时的描写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全诗中,通过有血有肉的情感描写,使得《回延安》这首诗情感浓烈,自然动人,既通俗易懂又耐人咀嚼,闪发出耀眼的色泽和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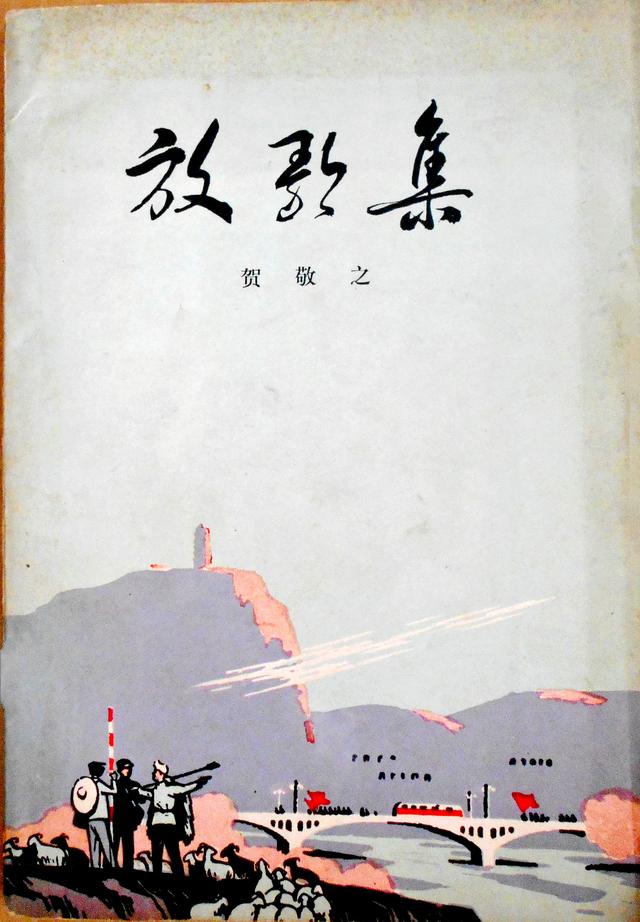
再看如今一些“诗人”的作品,不是充满“屎尿屁”的词句,就满篇都是“性取向”,甚至还《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些居然还得到一些“评论家”的热捧,被翻译成洋文!其实这些“诗作”,大多都属于胡编乱凑,是盲目堆砌,无病呻吟,毫无意境之类,若不是看作品的写作年代,还真以为是哪位满身积尘之人又从古墓里爬出来了。
我们这个火热的时代,还是更需要贺敬之这样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