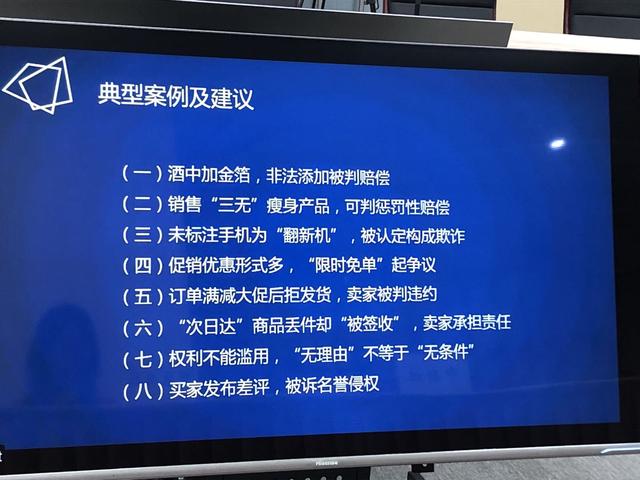直到哈德利艾布拉姆斯 10 岁时,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同性恋”这个词。即便如此,它还是在《西部故事》中的《我觉得很漂亮》的背景下——他们认为这只是意味着快乐。
27 岁的艾布拉姆斯回忆起在安大略小镇长大的经历:“我成长在一个‘啊,这太同性恋了’的时代——这是一种侮辱。”

但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艾布拉姆斯是非二元的、酷儿和无性的(王牌)。他们说,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没有搬到像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没有专门的互联网研究,他们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意义地了解自己的身份。
在安大略省的霍普港,你可以很酷,但“不要大声喧哗,”艾布拉姆斯说。
直到艾布拉姆斯在 23 岁时采用了无性恋标签,他们一直表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同。艾布拉姆斯几乎没有感觉到性吸引力,尽管一般来说,王牌人感觉到吸引力的程度在不同范围内有所不同。芳香剂(aros)也是如此,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浪漫的吸引力。
“这就像意识到有人一生都认为天空是绿色的,而我想,‘你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认为的绿色,”艾布拉姆斯说。
当艾布拉姆斯试图在他们知道无性恋之前约会时,他们遇到了很多让他们感到困惑的阻力。
“我经常被指责为性冷淡、机器人、冷漠、挑逗、喜欢引导他们——而且很多时候我只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进行。”
人们会变得沮丧并问他们出了什么问题,而艾布拉姆斯不会回答。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他们当时觉得。
出来后,他们说他们感到一阵轻松,好像他们终于被允许感受他们所做的那样。
“但与此同时,我想‘哦,不,这会让事情变得更难,不是吗?’”
艾布拉姆斯对为什么他们没有性吸引力有了答案,其他人的问题和挫败感并没有停止。不只是异性恋者不理解艾布拉姆斯的取向——同性恋群体中的人也是如此。
在大流行之前,艾布拉姆斯在餐饮业工作,并在轮班期间遇到了一位也是酷儿的新员工。当艾布拉姆斯分享他们既是同性恋又是无性恋时,另一个人问道:“你确定这不仅仅是创伤吗?或者像那样你有一些身体形象问题?”
在另一份工作中,艾布拉姆斯让一位同事告诉他们,无性恋不是真的。
“但就像,这只是人性,”同事说。“这就是人们所做的,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如果没有,请去看医生。”
无性恋的医学化无性恋在更广泛的加拿大社会中并未享有太多知名度。加拿大统计局甚至不收集有关无性恋加拿大人的信息,因此不清楚有多少加拿大人认为自己属于无性恋谱系。
大多数人对无性恋和浪漫主义的介绍要么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研究,要么是在流行媒体中遇到了一个罕见的无性恋表现的例子。
40 岁的贾斯汀·安切塔(Justin Ancheta)是一位作家和前教育家,住在多伦多。他将自己描述为“酷儿宝宝”,因为直到最近他还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在经历了人生的动荡时期后,他向一些朋友吐露了自己在质疑自己的身份。
“经过更多的对话、大量的自我反省、大量的自我探索和大量的阅读,无性恋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义,”他说。
“这真的很肯定,帮助我意识到我没有被打破。我没有缺陷。它帮助我真正更好地了解我是谁。”
发推文点击在推特上分享引用:“这真的很肯定,帮助我意识到我没有被打破。我没有缺陷。它帮助我真正更好地理解我是谁。”
和艾布拉姆斯一样,安切塔直到晚年才真正意识到无性恋是什么,正是通过亲人的帮助,他才能够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和取向。
对于 Ancheta 来说,对无性恋者的诚实描述在媒体中很重要,因为“很多酷儿的表现——至少是隐含的——如此关注性,以至于限制了我们对酷儿意味着什么的理解。” 他发现无性恋表现可能在两个主要方面造成破坏和问题。
首先是“对无性恋的描述表明王牌人被医学化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医学上有问题。” Ancheta 说,这可能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失去人性,并贬低 ace 和 aros。
“当无性恋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或双性恋一样有效时,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假设。”
医疗化尤其可能发生在那些被编码为神经发散性和无性恋的角色身上——想想电视和电影中的谢尔顿·库珀。
来自堪萨斯州的残疾王牌活动家考特尼·莱恩 说,“这种代表的缺陷在于它被视为一件坏事。” Lane 是 Ace Couple 播客的一半,由她和她的无性配偶 Royce 主持。
莱恩说,像这样的表现将无性恋描述为神经分歧的“症状”,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角色是异类的——事实上,无性恋和神经分歧都是一种完全有效的体验。
另一方面,安切塔说,在一般流行文化中,无性恋的表现是如此之少。
艾布拉姆斯指出,无性恋角色通常被归为病态的连环杀手(例如德克斯特)和非人类角色。“他们是机器人或外星人,或者像模糊的类人生物,当然,他们没有性欲——因为他们不是人。”
然而,流行媒体如何直接将无性恋医学化的一个鲜明例子是 2012 年House MD 的一集
在第八季《美好的一半》中,豪斯看到一位处于无性婚姻状态的病人,他打赌他的同事,他可以找到医学上的原因来解释这对夫妇不想发生性关系的原因。
豪斯的错误想法是,“唯一不想要(性)的人要么生病,要么死去,要么撒谎。”
在这一集结束时,豪斯发现垂体问题正在影响丈夫的性欲,而他的妻子只是假装无性恋,这样她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许多无性恋群体谴责这一解决方案有害且不真实.
这一集引发了多 篇思考 ,讨论了这一集对无性可见度的破坏性。
实际上,在这部剧播出的时候,莱恩一直在考虑以无性恋的身份出现——尽管她现在认为自己更像是有性欲的。
“所以这并没有给我向朋友和家人出柜的希望,因为我也是一名残疾妇女。我患有慢性病,”莱恩说。
“我非常担心人们会利用这一点以及我自己的疾病来诋毁我自己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Ablism和无性恋“很多人的一个普遍神话是,无性恋是一块巨石,”安切塔解释说。
就像在频谱上表达无性恋的方式一样,ace 和 aros 通常具有与他们的无性取向相互作用的交叉身份。
Ancheta 是菲律宾人,也是残疾人。他说,在关于倡导无性能见度的对话中,种族化和残疾的声音经常被边缘化。白色和健全的 A 被视为“正确”的代表,而外面的人则不是。
莱恩特别注意到对失能王牌的审查增加了。
“几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希望与这两个社区保持距离,因为残疾人社区经常被去性化,”莱恩观察到。“因此,在一个现代、更加积极的社会中,在某些情况下,这表现为围绕着希望被视为性解放者的残疾行动主义。”
发推文单击以在 TWITTER 上分享引用:“几乎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愿望要疏远这两个社区,因为残疾人社区经常被去性化,”莱恩观察到。“因此,在一个现代、更加积极的社会中,在某些情况下,这表现为围绕着希望被视为性解放者的残疾行动主义。”
莱恩曾看到残疾活动家发表的声明,例如“残疾人确实有性行为”,并加上了诸如“就像其他人一样”之类的修饰语。或者,“残疾人确实有健康的性行为,因为我们是人类。”
“这样的言论对无性恋者有害,其中一些人也是残疾人。这可能会让人很疏远,”她补充道。
去年,当她在一篇关于她的交叉身份的文章中被引用时,莱恩非常熟悉这种残疾和无性恋的紧张关系。
“是的,我是无性恋者,是的,我是残疾人。这是我独特的问题,”她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无性恋者那里收到了几十个 DM,他们说‘你怎么敢,我们不想让你谈论这个,你不应该再公开谈论无性恋了。’”
在线讨论引起了多伦多一家名为Asexual Outreach的非营利组织的注意,Lane 开始与其执行董事 Brian Langevin 交谈。
Asexual Outreach 每年举办一次 Ace Week,以提高人们对 ace 和 aros 的认识并建立社区。莱恩认为那一周的某一天应该是为了放大残疾王牌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残疾王牌日诞生了。
第一个残疾人王牌日是 2021 年 10 月 27 日。
Ancheta 说,在 2SLGBTQIA 社区内倡导通常意味着与其他争相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的人发生冲突。
“很多人觉得社区的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必须相互竞争空间、时间、片刻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安切塔说。
“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有空间。每个与我经历相同旅程的人都有空间。”
他希望加拿大不仅会更加接受无性恋人群,而且王牌社区将更加包容交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