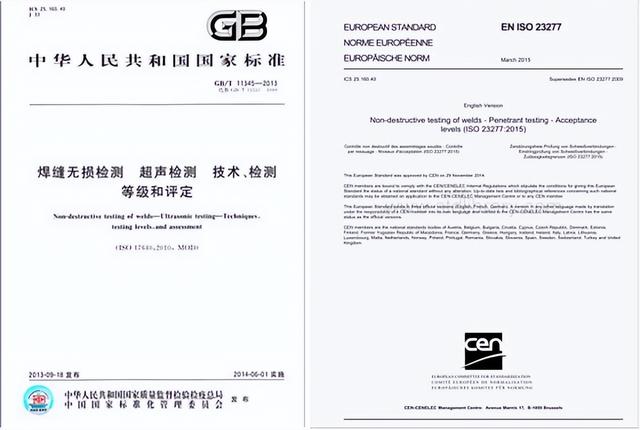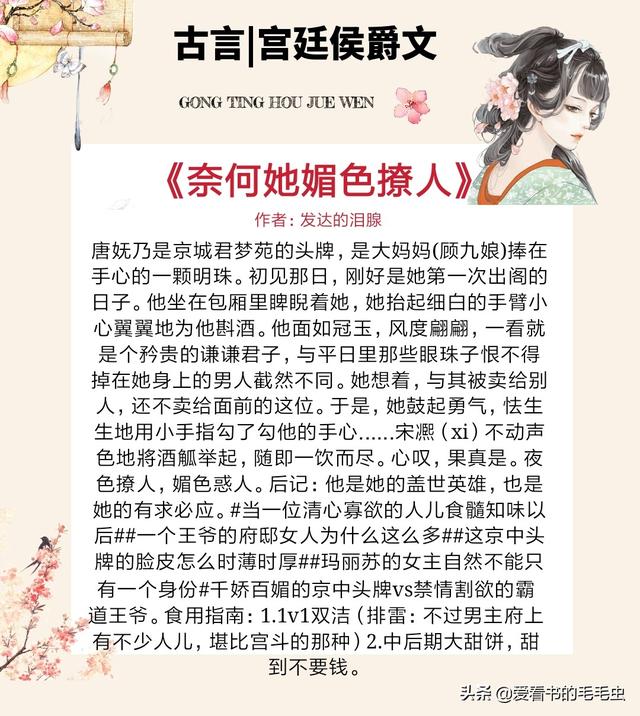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古代即已有阶级的概念,但与现代的阶级概念不同,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既包含一个阶级内部的等级,如公、候、伯、子、男,也包含作为阶级的等级,如贵族、平民、奴隶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关注起源于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近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推向高潮据王贵仁所作的研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观念是从十九世纪从西方输入的梁启超言“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是新含义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最早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生产品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的形成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差别等级那些处于相同等级的人们,在利益驱动下,形成相同的利益诉求“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这就是构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阶级状况作了表述:“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十七世纪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十九世纪则是大厂主和无产者”马克思认为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存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过渡……”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给出了阶级由产生到消亡的轨迹其理论前提是生产力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作为阶级存在基础的生产关系即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消灭阶级的唯一手段和短暂的过渡,“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不过,理论的轨迹并没有成为历史的轨迹,这是因为理论先已发生了错轨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中既能看到传统人性论的影响,也有其独特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使我们想起克利西帕斯所说的“每一动物的首要的和最关切的事情它自己的生存,及其生存的自觉”马克思在1842年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1844年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在1845年说过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这使我们想起人有自私的本性的论述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写道:“如果人们要按效用原理来判断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等等,也首先要广泛地研究一下人的本性,然后研究一下各个时期曾经历史地发生过变化的人的本性”在这里,马克思把人性分为人的本性和变化的人的本性而他在1844年写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划分:“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也使我们想起张载的“天地之性”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性放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他在1845年的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人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存发展、人有与生俱来的共同本性这些公认的人性论基本原理是认同的,但在同时,他又认为人性是随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他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随着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于是人性也随着时段的变化而变化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性的形成与社会关系也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非一时一地的联系,而是从动物到人这样无比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联系这正是理论的歧义所在在我国,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极端片面的演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社会流行后来愈演愈烈的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否认有超阶级的人性存在,只承认有阶级性,不承认人性,发动了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阶级觉悟”的支配下,十几岁的学生成群结队,对白发苍苍的老教师、老将军、老元帅拳打脚踢,不惜致伤、致残、致死,毫无恻隐之心家庭也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儿子斗争父亲,妻子告发丈夫,只知愚忠,不明是非,帮助恶人打倒亲人;一少年听到妈妈议论领袖,便去报告,结果妈妈被枪毙,懂事以后,愧悔万端,痛不欲生;著名戏剧家严凤英服毒自杀,军代表竟命人当作众人的面剖腹检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结果只能是人性泯灭、社会紊乱、道德沦丧用阶级性来否定人性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性是人依赖基因传递的与生俱来的本性,而阶级性只能从后天获得,是人们依据占有生存资源的多寡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和立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世间万物皆有其本性,它们随着万物的生成而生成,与万物的物质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无例外,人性也与人的生物结构、人的新陈代谢、人的食与色等等密切相关而阶级性仅仅与人们在后天所掌握的生存资源多寡相关假如有一个人,出生于资产阶级,但由于人生的变故,他从小就被一名工人领养了,那么,我们该怎样来想象他未来的阶级性?我们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想象他将来一定会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吗?显然不能所以,阶级性只与人们占有生存资源的多寡有关,而与人的出生并无必然的关联实际上,出生于什么阶级,并不等于就会有什么样的阶级性人的社会立场、思想意识的形成,并不仅仅与人的一时一地的经济利益相关,同时也与他的长远利益、他所在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影响、与社会思潮、时代风尚等等密切相关现实中的人的阶级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穷人能变成富人,富人也能变成穷人,在这个变化中每个人的性情变与不变,变化多少也不一定的,而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人的本性,仍然是深藏在他们心里在氏族社会,阶级是不存在的,将来,作为现代意义的阶级也可能模糊或消亡,在这样两个时段,我们不能说因为阶级不存在人性也就不存在再说,相同阶级的人,思想、观念、立场并不都是一致的就像打天下的那一代领导人,多出生于富裕家庭,却是站在工人农民一边,他们革命的动因不能说没有人性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明证,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对人性阶层的理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对人性阶层的理解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古代即已有阶级的概念,但与现代的阶级概念不同,是指社会上存在的身份等级,既包含一个阶级内部的等级,如公、候、伯、子、男,也包含作为阶级的等级,如贵族、平民、奴隶。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和关注起源于法国和英国近代史学。近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推向高潮。据王贵仁所作的研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观念是从十九世纪从西方输入的。梁启超言“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是新含义阶级一词在近代中国最早的运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剩余生产品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的形成。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差别等级。那些处于相同等级的人们,在利益驱动下,形成相同的利益诉求。“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这就是构成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将欧洲中世纪以来的阶级状况作了表述:“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十七世纪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十九世纪则是大厂主和无产者。”马克思认为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是证明了下列几点:“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存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过渡……”。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给出了阶级由产生到消亡的轨迹。其理论前提是生产力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作为阶级存在基础的生产关系即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为消灭阶级的唯一手段和短暂的过渡,“只要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就能解决这次斗争”,“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不过,理论的轨迹并没有成为历史的轨迹,这是因为理论先已发生了错轨。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中既能看到传统人性论的影响,也有其独特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使我们想起克利西帕斯所说的“每一动物的首要的和最关切的事情它自己的生存,及其生存的自觉。”马克思在1842年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1844年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在1845年说过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这使我们想起人有自私的本性的论述。马克思在后期的著作中写道:“如果人们要按效用原理来判断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等等,也首先要广泛地研究一下人的本性,然后研究一下各个时期曾经历史地发生过变化的人的本性。”在这里,马克思把人性分为人的本性和变化的人的本性。而他在1844年写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划分:“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也使我们想起张载的“天地之性”。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人性放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他在1845年的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写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人性的本质是人的生存发展、人有与生俱来的共同本性这些公认的人性论基本原理是认同的,但在同时,他又认为人性是随着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他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随着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于是人性也随着时段的变化而变化。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性的形成与社会关系也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非一时一地的联系,而是从动物到人这样无比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联系。这正是理论的歧义所在。在我国,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极端片面的演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社会流行后来愈演愈烈的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否认有超阶级的人性存在,只承认有阶级性,不承认人性,发动了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阶级觉悟”的支配下,十几岁的学生成群结队,对白发苍苍的老教师、老将军、老元帅拳打脚踢,不惜致伤、致残、致死,毫无恻隐之心。家庭也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儿子斗争父亲,妻子告发丈夫,只知愚忠,不明是非,帮助恶人打倒亲人;一少年听到妈妈议论领袖,便去报告,结果妈妈被枪毙,懂事以后,愧悔万端,痛不欲生;著名戏剧家严凤英服毒自杀,军代表竟命人当作众人的面剖腹检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结果只能是人性泯灭、社会紊乱、道德沦丧。用阶级性来否定人性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性是人依赖基因传递的与生俱来的本性,而阶级性只能从后天获得,是人们依据占有生存资源的多寡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和立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世间万物皆有其本性,它们随着万物的生成而生成,与万物的物质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无例外,人性也与人的生物结构、人的新陈代谢、人的食与色等等密切相关。而阶级性仅仅与人们在后天所掌握的生存资源多寡相关。假如有一个人,出生于资产阶级,但由于人生的变故,他从小就被一名工人领养了,那么,我们该怎样来想象他未来的阶级性?我们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想象他将来一定会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吗?显然不能。所以,阶级性只与人们占有生存资源的多寡有关,而与人的出生并无必然的关联。实际上,出生于什么阶级,并不等于就会有什么样的阶级性。人的社会立场、思想意识的形成,并不仅仅与人的一时一地的经济利益相关,同时也与他的长远利益、他所在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环境的影响、与社会思潮、时代风尚等等密切相关。现实中的人的阶级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穷人能变成富人,富人也能变成穷人,在这个变化中每个人的性情变与不变,变化多少也不一定的,而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人的本性,仍然是深藏在他们心里。在氏族社会,阶级是不存在的,将来,作为现代意义的阶级也可能模糊或消亡,在这样两个时段,我们不能说因为阶级不存在人性也就不存在。再说,相同阶级的人,思想、观念、立场并不都是一致的。就像打天下的那一代领导人,多出生于富裕家庭,却是站在工人农民一边,他们革命的动因不能说没有人性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