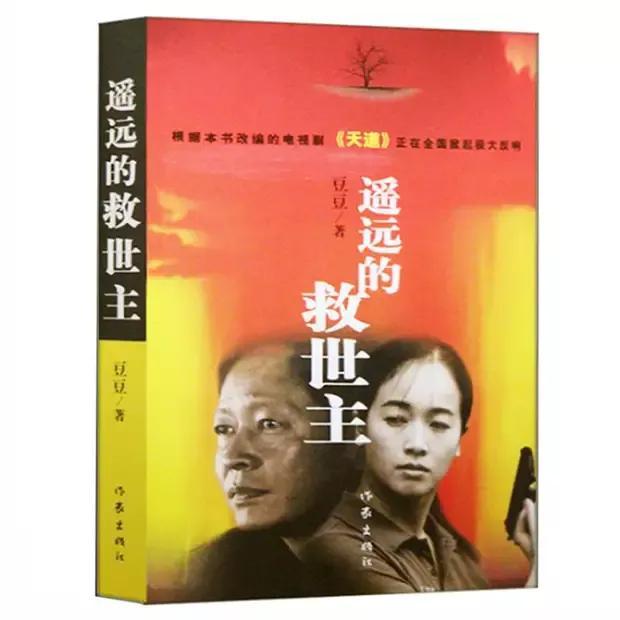中国读书人每每喜谈“养气”,有时还劝人“心平气和,多养气啊!”养气这工夫可真难。我们试看宋末元初方回的一首诗,就知道养气之难了。
万事心空口亦箝 如何感事气犹炎
落花满砚慵磨墨 乳燕归梁急卷帘
诗句妄希敲月贾 郡符深愧钓滩严
千愁万恨都消处 笑指邻楼一酒帘
他第一句诗说“万事心空口亦箝”,本来把万事都看空,把世间一切都看透了,自己把嘴巴也封起来了,对人对事都不再去批评讨论了。“如何感事气犹炎”,可是一碰到什么事情,气就来了。就像讲究养气的人打坐,原来在座上,心平气和挺好的,可是一碰到不对劲的事情,就发怒了。“落花满砚慵磨墨”,这第三句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本来想写写字、作作画的,可是一阵微风过处,落花片片,有几瓣飘飞入窗,刚好掉落在砚池中托身。见到这砚池中落花沾墨,又是一种情思,而打消了写字作画的念头,连墨也懒得去磨了。这就是受了外境的影响而移转了自己的心意,虽然人好像懒了,但还是心动气浮,几片落花就影响了自己。可见这和孟子说的“持其志,无暴其气”的七字“真言”就不相符合了。
“乳燕归梁急卷帘”,这第四句的写景也颇美:一双筑巢在梁上的燕子生了乳燕,初出窠巢试飞,倦了归来时,帘子挡住了它们的归路,自己又急忙去把帘子拉起来。虽然是一个善意的举动,但到底还是动心了。
第五句“诗句妄希敲月贾”,这是描写作诗的好胜之心,“好胜”也是气动。这句诗中“敲月贾”三字是有典故的。唐时有一个著名诗人贾岛,他有一次作诗,其中有一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又想想其中“推”字不大好,而改为“敲”字,成了“僧敲月下门”。但是究竟用“推”字好,还是“敲”字好呢?决定不下,于是在走路的时候,他边走边反复吟诵,不知不觉就撞了韩愈的驾。那时韩愈是大官,正骑在马上,卫士们当然把贾岛抓来。韩愈一看是个秀才,就问贾岛走路为什么莽莽撞撞的。贾岛说因为我正在一心作诗,所以没有注意到。韩愈听到这个人会作诗,大感兴趣。贾岛说明内容,韩愈大为赞赏,而且主张用“敲”字。于是贾岛的诗名大起,名满长安了。后来把斟酌文字称作“推敲”,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就知道方回这句诗的意思就是作诗时也是求好心切,望胜的心大了。
第六句“郡符深愧钓滩严”,这是坦率说自己养气工夫的不行,遇事仍会动心。严子陵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好朋友,光武中兴,刘秀当了皇帝,找严子陵来做官,严子陵不但不去,反而躲到富春江上,穿件蓑衣,戴个斗笠,在江边钓鱼。但是方回接到郡守的任命状就高兴起来,回头一想到严子陵的高风,反而感到惭愧了。
我们记得公孙丑问孟子,假使在齐国当政功成名遂时动不动心,孟子说不动心。现在方回对一张任命状都动了心,这又是说明养气之难了。以诗论诗,这首诗第五、六两句都不算高明,喜欢用人名来押韵,是学苏东坡的作诗技巧。但苏诗这种技巧,并不足以取法。
最后两句“千愁万恨都消处,笑指邻楼一酒帘”,这是他的结论,最后想想,人生还是不要动气,不必动心。不过他的不动心、不动气,是要靠隔壁那家的酒来帮忙的,这不是要靠酒醉来自我消气吗?
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哲学思想很难研究,因为多半都包含在诗词与文学作品之中。我们看方回这首题为“春半久雨走笔”的七律,句句都含着哲学思想。
事实上,唐宋以后的士大夫们讲究静坐的、学习吐纳的、做炼气、养气工夫的非常多,我们随便举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如唐朝白居易有首诗:
自知气发每因情 情在何由气得平
若问病根深与浅 此身应与病齐生
这完全是他养气工夫的报告,他说自己明明知道气动的时候一定是受了感情的影响,是心动而同时气动。所以在没有修到无心地、尚有我此心时,则必因情而动心,心动就气动,那么气也就没法养得平了。如果要问容易动气的毛病有多大的话,老实说,当你一出生,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这个动心、动气的毛病就有了。因此他又有一首诗说:
病来道士教调气 老去山僧劝坐禅
孤负春风杨柳曲 去年断酒到今年
一面在修心养气,一面又在动心惹气了,看来蛮好笑的。又如宋朝苏东坡的诗:
析尘妙质本来空 更积微阳一线功
照夜一灯长耿耿 闭门千息自蒙蒙
他说这是一个物理世界,我们予以层层分析,分析到像微尘那么微细,再去层层剖析,到最后,它里面的中心则是空的。现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苏东坡所引用的这项佛家理论的真实性。所谓原子、核子、中子等,剖析下去,最后的中心是空的。而这本来的虚空,又因“更积微阳一线功”——这又是我国传统文化《易经》的道理。本来世界就是虚空的,只是因为一点点阳能持续回复的作用而奏功,由虚空产生了万物万有。认识了这一项真理,在晚上一盏孤灯之下打坐,把心念之门关上,千念万虑都摒诸心门之外,于是气息平静,久久都在一种濛濛然的氤氲状态之中,自由自在,舒适安详了。本来苏东坡对佛道两门的学问修养都很喜欢研究,而且也有点实践的小工夫,所以在他的这首诗里,对养气的工夫做得好像较有进步;但是他在狱中作的诗有“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不免又动心惹气而不安了。
还有陆放翁的词里也说:“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所谓潭是指山中小溪流经之处有一较宽阔的深水聚处,天然有调节溪流水位的作用,在溪流中称为潭,如台湾的日月潭、碧潭、鹭鸶潭等。在河川间则名为湖,面积就更广阔,水也更深,如大陆的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等。放翁在词中说,养心养气要养到像没有丝毫风吹的潭水,水面上没有一丝涟漪,平静得如同镜子一般,这样一坐下来,就连续数千息。一呼一吸称为一息。平常人打起坐来,心念平静的时候,呼吸是非常缓慢轻微的,甚至好像不在呼吸,而勉强去分辨,一息可能至少要三四秒钟。而在这心如止水的平静之中,一坐可以数千息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陆放翁的“一坐数千息”,是在静坐中做数息观的老实话。
心理专注出入息的次数,便是佛家讲修养方法的专注一缘、系心一缘,也就是与孟子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的原则相同。我们读了陆放翁这些词句,便知道他晚年也讲究养气的工夫,这和他少年时代“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的气概虽然同样是使气任性,但此时的数息养气当然不是少年时代壮气凌云一般的粗放了。如果以人生的经历和心情来讲,他写“一坐数千息”的词句应该在他写下面这首《再过沈园时》之后了。
梦断香销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犹吊遗踪一泫然
如此论断都是想之当然的事,而放翁毕生的意气却是至死不衰,所以才有下面这首诗表达的临老的庄严壮气。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些虽然都是文学上的气概,但文字、语言与意气之间却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
从这些唐宋文学名人的作品中,可以知道养气之难。这个养气,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与不动心相配合的养气,需要大勇。像文天祥这类的人才可以谈得上正气,所以这也可以说是“难言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