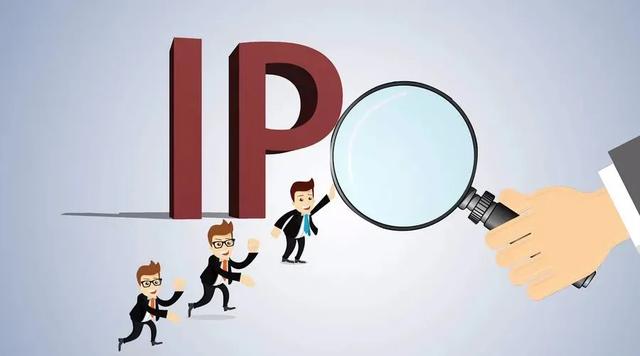籍原意是书册的意思,逐渐有隶属关系的意思。
祖籍我认为祖先的生活地应是最原始的意义,古代人有族谱或家谱,有据可考。而时代的变迁,一代一代人的繁衍生息,家谱逐渐消失。随着科技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对祖先的生活地仅是一个口口相传的信息,已无据可查。
本人的简化理解为,祖籍为祖父出生地,籍贯是父亲出生地,户籍是随户口变化的地方,本人出生地就不必解释了。
本人2019年曾有寻根的经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着八十的父亲找到了祖籍山东文登,寻找经历也颇有点意思。
父亲的口中能够得知的最早的祖籍信息是我的太爷爷应是兄弟四人,排行老二,生卒年不详,出生地是文登崖(读ai二声)子头村,文登属丘陵地带,当地取名以村子边有个小山崖得名,能追溯到唐宋时有人在此地居住逐渐形成村落。我的太爷爷据说在北京生活过两年左右,当时京城胡同里给人打水送水的水夫。

当时以山东人为主垄断了送水的行业,逐渐形成水霸的局面,不但盘剥他们的山东老乡水夫,同时也会欺负用水人,要是得罪水霸,可能要几天吃不上水,应是当时行业里的潜规则。

据说太爷爷在义和团京城混乱的时期离开了北京。
我的爷爷出生在崖子头村,也是兄弟四人排行老二,生于1904年,属龙。1992年我高一那年去世。从爷爷生前讲述的故事,包括这次寻根听当地未出五服的叔叔的讲述,爷爷应该是18岁左右闯关东,出来之前应该是在家里惹了点祸,从烟台或威海乘船至大连,沿路北上至安东(现在的丹东),投奔他的舅舅,后跟随舅舅在长白山地区伐木,沿鸭绿江将木材运至安东,大概干了三五年,后在安东逐渐定居。我的伯父出生在文登,从闯关东之后,据说爷爷仅在三四十年代回了两次文登,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父亲生于1940年的安东,也属龙,与爷爷相差36岁,兄弟姐妹五人,也是排行老二。十多岁时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当时地处边境的丹东时常受到炮火的袭击。父亲高一在丹东二中上学,算是我的校友前辈,我及表弟、我的外甥、外甥女都是二中毕业的。后来爷爷一家迁至内蒙古包头大概两三年时间,因为伯父在抚顺钢厂工作,为支援包钢建设举家前往包头。
父亲是在包头参加的高考,而且当时收到了现在北京地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最终他在北京短暂停留,究竟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还是因为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原因,他没有选择在北京念书,而是直接回了丹东,从此开启了他的平凡人生。这就是命运,如果当时他选择了北京,现今的我就不会存在。
我1976年出生在丹东,也属龙,与父亲也相差36岁,姐弟三人,高中毕业后在沈阳念的大本。1999年毕业后在沈阳一家私营企业打工两年,也是不经意间去北京出差,特意看看在唐山工作的伯父,借此机会2001年调到了二十二冶。在这里娶妻生女,本是干工业建筑的施工企业,虽然辛苦,但是成长很快。
几代人的擦肩而过,换来了我现在北京的定居生活。冥冥中自有安排,2004年企业在北京参与酒店项目的建设,在这里与命运中的另一条生命线相交集,开启了人生中第二段婚姻的生命历程,也促成了我在北京17年的生活经历。
这就是至今历时100多年的家族的生命的延续,必然中存在着偶然,偶然中造就着必然。人与人生命的关联生命的传承就是遵循着这种规律。
如今,祖籍地太爷爷这支已经没人了,崖子头村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改成了香山村,理由是文登当地当时有三个崖子头村。本次寻根也是先找到了地图上的崖子头村,已经变成社区,好在提前做的功课,父亲还记得奶奶村子的名字孙家埠,也知道爷爷奶奶村子离得不远,才寻迹而去。找到了村中未出五服的叔叔,看到了当时爷爷奶奶住过房子的遗址,也是未必准确,因为爷爷离开村子时,他们也没有出生,只是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父亲很兴奋,但也有点遗憾,真是没有特殊的准备,没想到能够找到,也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来去匆匆,只是寒暄了一个小时,互相赠送了些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