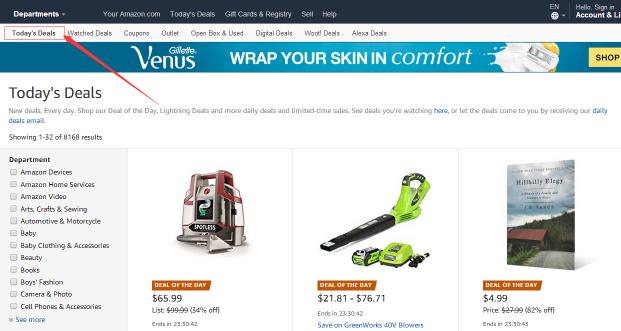《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林奕含最后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遗作,当我们谈论它时,几乎没有办法把文本与林奕含本人割离开来。虽然现实中的遭遇与小说里的情节不可能完全吻合,13岁的房思琪与离世时26岁的林奕含不能粗暴地等同,但在捧起文本去阅读的时候,我们仍能感受到那股丝丝缕缕都与现实密切衔接的痛感。
是的,痛感,林奕含选择一个虚构的世界把自己装进去,但那些露骨的疼痛是绝对真实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奈何“创痛酷烈,本为何知”?疼痛是将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起来的最强有力的纽带。在这儿,痛感就等于“真实”。林奕含在采访里说“如果你感受到痛苦,那是真实的”,她足够明晰地在向世界呼救,可惜在这之前,她已经做下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定。
在过去几年,书评周刊曾多次发文悼念林奕含,与读者分享和讨论了房思琪的故事,也反思了社会上依旧猖獗的性侵现象。(如《林奕含逝世三周年:我们如何挽救下一个“房思琪”?》《林奕含逝世一周年:每次看到这个姑娘的名字,就好心痛》)四年过去,“房思琪式的暴力”“房思琪式的谋杀”仍然在社会的隐秘角落上演,我们被迫一次次与林奕含以及她的房思琪故事相遇,她的故事不断控诉与提醒着我们,性侵害事件背后的暴力之网与其中的制度性缺漏。
今天这篇文章来自一名文学爱好者。她曾多次拿起《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溺在林奕含用文字搭建的失乐园里,一次次被房思琪的故事折断。她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比喻为一把匕首,一件凶器,剜割着人们对文学的信仰,对真相的信仰。在她富有情感性的讲述中,我们审视与纪念林奕含与房思琪的故事。悼念之外,我们更想叩问与反思:“房思琪”面临的世界更好了吗?

林奕含(1991—2017),台湾作家。梦想是一面写小说,一面像大江健三郎所说的:从书呆子变成读书人,再从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
撰文丨刘西西
以“文学”为名的诱奸
“诱奸”一词由两个字组成,先有“诱”然后才是“奸”,诱导房思琪进入这个“初恋乐园”的,是李国华构建的文学天堂,或者索性说是文学也不错。
从读者角度出发,或许会忍不住叩问,如果李国华不那么深谙文学之道,不那么博学、有才,他还会不会将房思琪摧毁得如此体无完肤?房思琪及林奕含,还会不会被这段记忆给杀死?
从很多角度而言,答案都可以是否定的。当李国华娴熟地对她说着那些情话,当他用自己满腹学识走进房思琪的世界时,他的一只脚就已经踩进了房思琪的身体里,且这种踩踏是不可逆的。对房思琪而言,文学是精神上的父母,在发育与成长的人生初期,精神与大脑向一切美好敞开,对一切恶还不具防备,在这个阶段,一切与她在文学上共舞的人都短暂扮演父母,比如美好而伤痛的伊纹姐姐。
一个人怎么可以杀死自己的父母?就算精神上杀得死,情感上也杀不死,对于文学的情感是深嵌在思琪与怡婷整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的,是她们生命的根,“连根拔起”对一个热爱文学的女孩而言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十几岁的房思琪,还是二十几岁的许伊纹——房思琪的邻居姐姐,一个放大版的、同样忍受着难以启齿的痛楚的女孩。
书中有一个词被频繁提起——“快乐”。这个寻常词语被多次用作形容词出现,“房思琪‘快乐’地对老师说”,李国华“快乐”地发现女孩的……在这些语境下,“快乐”真的代表“快乐”吗?抑或是“开心”,这两个如此单纯、纯粹的形容词,被用在如此龌龊的地方,令人胆寒。
林奕含在采访里也特地提到了“快乐”这个词:“房思琪的‘快乐’是带有引号的快乐,她知道那不是快乐,可是若她不把那当作快乐的话,她一定会活不下去,这也是我觉得很惨痛的一件事。”

林奕含生前接受访问时的画面。
把单纯无情杂糅了污秽,把单纯用力揉碎了,嚼碎得稀烂,是房思琪和林奕含面临的共同苦刑,它们像凌迟一样狠狠惩罚着两个女孩的敏感内心,嘲笑着她们的自尊心。
在一段性关系中,“快乐”的确是很自然、很常见的形容词,这儿更近似于一种肉体上的快感与精神上的放松。放松是快乐的先提条件,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彻底放松?在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对周遭环境具有掌控力的时候。比如李国华清楚地知道,利用一个女孩的羞耻心去强奸她,全世界都觉得是她的错,包括她自己也觉得是她的错。
热爱文学、从事文学的人,天然都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在李国华这里,想象力是一把剖开少女身体的利刃。在房思琪这儿,想象力也是一把利刃,迫使她撕开自己,一刀刀剜割自己,到最后,她看到一切事物都会不由自主联想到李国华对她做的那些事,在头脑里摆脱不掉,“联想,象征,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
以“权力”为刃的谋杀
现在,读者都知道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个关于权势的性侵,是一场建立在社会性喑哑之上的诱奸。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各版本封面:最早的繁体版(版本:台湾游擊文化 2017年2月)、大陆简体版(版本:磨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1月)与韩文版(译者:허유영;版本:비채 2018年4月)。
李国华与房思琪的关系,除了表层的师生,更多了一层权力以外的利用关系:李国华利用房思琪的羞耻心,狠狠利用她的自尊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利用文学的纯净性,自尊心代表房思琪的灵魂,她的灵魂寄予对文学的期待和信任之上,然而李国华狠狠践踏了这份信任,摧毁的是房思琪“对生命的上进心,对活着的热情”。这是一种信念性的东西,很难通过新闻来讲述,但文学可以。
她活下去的理由成了臆想中的爱,但这爱是年仅13岁的房思琪编造出来的,她从文学里获得的对爱的理解,浇灌在这段强侵与凌虐的关系里,唯有幻想爱能让她同时接纳李国华的侵占和保有不说的自尊。因为“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这句话也适用于书中另一个女角色,许伊纹,她爱着新婚丈夫一维,爱屋及乌,说服自己强迫去爱他的暴力。书里说,伊纹对一维说过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可以白天上我,晚上打我。”
多么羞耻、多么痛的一句话,它已经是伊纹可以说出来的最心狠的话了,它是一种请求,也是一种自我麻醉,她强迫自己相信,与一维的婚姻仍然是平等的,是可以商榷的,这份商榷是借口。
借口,为了给罪行、暴行寻找合理化,她们必须寻找借口,生命成了在幻想的爱与充满耻辱的借口之间拉锯徘徊的过程,就像李国华气定神闲地对房思琪说:“当然要借口,没有借口,你和我这些,不就活不下去了吗?”
他太自信了,自信到可以凭空营造一个恋与爱欲的牢笼,把思琪这个小小的坚韧的人儿死死困在里面,这只有他们二人的空间里,李国华化身掌控者,房思琪成了他的玩物,他可以狠狠地释放欲望,狠狠地把这欲望纵溺在文学的海洋里。
温良恭俭让。出现了不下五次的五个字,每次在书中露面都是一根鞭子,狠狠地抽着房思琪的身躯,狠狠地将她扔到地上,又享受她如同小狗般卑微的摇尾乞怜。
为了活下去,房思琪先是内化了这个给自己寻找的借口,然后从诱奸、性权力压迫与自尊心的罅隙里企图寻找一个缺口,跳进去,漏至更深的谷底。
“不只是他要,我也可以要。如果我先把自己丢弃了,那他就不能再丢弃一次。反正我们原来就说要爱老师,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她开始自我麻醉,自我投入到爱情的幻象里,爱情不只是喜欢与欢喜,不只是“接受”与“忍让”,也需要主动,不仅是心意上的主动,也可以是肉体上的主动。
在今天,铺天盖地的、碎片化的新闻里,类似的性侵事件藏头露尾,虽然读者大多只能获知冰山一角,但从中亦不难感受到一种共通性:所谓房思琪式的暴力,大多建立在权力的压迫上,用一把强对弱的巨伞笼罩着主人公。现实不同于小说,然而二者皆有自我说服与自我欺骗的共通之处,性侵之所以能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即是这种无法反抗的、无形的权力压迫。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林奕含离世后不到一个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通过了“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第九条修正条文,明定补习班教职员工都必须揭露其真实姓名。法条还明定,补习班相关人员如果知道有性侵害、性骚扰发生,应向有关机关通报,杜绝不适任人员进入补教业。
不过,现实社会所做的诸种努力,看起来怎样都显得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意思。一个有些悲痛的现实是:某种程度上,现实中的法律越完善,林奕含越是不可能得到彻底的救赎。据其生前采访与其父母的回忆,遭受补习班老师(李国华原型)侵犯,应当是在十八岁前后,跨过了成年节点,在伦理、司法与制度上产生的惩处,又完全是两回事了。
林奕含的确不等于房思琪,但她们感受着同样的痛苦。这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文学价值以外的更深、更远的现实撼动。
以“知耻”为训的喑哑
文学让房思琪早熟,也让她早衰,从一开始,她就过早地、过于敏锐地明白,加害者不仅仅是李国华,更是身边整个社会环境,遗弃她的也不只是文学,是身边口口声声关心自己、爱着自己的家人与朋友们,是包含文化观念与社会反馈系统的整个大环境。

林奕含生前露面的新书活动。
我们有理由说,在一个社会里,任何关于性的暴力与犯罪,都不会是哪一个人单独的罪行,受害者身边接受的态度、规训与目光,皆是帮凶。正如美国人类学家Cathy Winkler在其自述《强暴是社会性谋杀》里说的那句:“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一起完成的。”
李国华利用的是整个大社会对性的禁忌感,这禁忌感不仅仅存在于台北或台南,不仅存在于李国华家的书房与卧室里,也不仅仅弥绕着思琪与怡婷的童年。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从古至今,禁忌感都是性犯罪里一把最好用的凶器。
钱一维利用的是其身边的小社会对自己的纵容。伊纹是张太太介绍给一维的,但张太太“知道钱一维打跑几个女朋友”,张太太“穷死也不让女儿嫁过去”。不仅张太太知道,老钱奶奶也知道,面对这般暴力,却没有一个知情者发声。
无论是李国华还是钱一维,无论是面对房思琪,还是再早的郭晓琦、饼干,以及一群在后面排队等着自己的小女生,因为这个社会命令她们要有羞耻心,这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成了帮凶,最终以致“他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的现象。
日本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曾这样分析儿童性侵犯者的心理:“无需担心男人性主体地位被侵犯的危险,在性活动中控制他者,为此选择障碍最小、最无力反抗的对象,并且还希望对方也很情愿。”
于是,需要被进一步追问的是,无处不在的禁忌感究竟从何而来?答案一目了然:性别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童年阶段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越是优雅、知识分子的家庭,越喜欢强调传统,他们可以一面呼吁全面发展,一面要求自己的女儿温婉、懂事,浓缩概括一下,离不开两个字:知耻。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房思琪有两次试图向家长求救。第一次是在饭桌上,她故意漫不经心地提到,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偏偏缺乏性教育,妈妈却十分干脆地说:“什么是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的,所谓教育不就是如此吗?”
第二次是假借一个并不存在的“同学”爱上老师的经历,小心翼翼地试探母亲,却得到母亲一句“小小年纪就这么骚”。大人的一句话就把房思琪噎死了,她的自尊心被李国华噎死之后,仅剩的一点求助的欲望与决心也被自己的妈妈噎死了。
“父母将永远缺席,他们旷课了,却自以为还没开学。”这场关于性与生命的教育,是给大人而不是给小孩的。
大人,涵盖的不仅仅是作为监护人的家长,还包括法律与哲学层面的,每一个拥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有独立理智与思维的成年人。我们的成年人自然而然地奉行着这样一套价值观:女孩得听话,得乖巧,更重要的是,得“知耻”,这些东西媾和起来被装进名为教养的壳里。而诱奸受害者的脆弱之处,正是这套与法律精髓互相矛盾的伦理价值体系。
这或许不只是福柯所说的“规训”,在各式信息无孔不入的今天,“规训”被互联网的模具重塑,每天都在上演性侵、家暴的新闻,反而让观众对这些司空见惯的事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审美疲劳”,媒体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窥探欲,不得不进一步挖掘细节,造成波及所有年龄段的另一种媒介文化规训。
今天,不知道多少人还在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但房思琪式的悲剧从未停止上演,文学仍然在绽放它的魅力和魅惑能力,权势、教育的进步和改善都是迫切的,但也是缓慢的,当我们回忆起林奕含,应该想起的是,那个在订婚宴前一夜躲在厕所里用iPad哭着写小说的女孩,应该想到的是,文学与艺术也具有其致命的迷惑性,在致力于消除房思琪式的谋杀之前,我们的教育者、创作者,应该随时保持警惕掉进某样事物最“美”一面的陷阱。
作者 | 刘西西
编辑 | 青青子 罗东
校对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