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社会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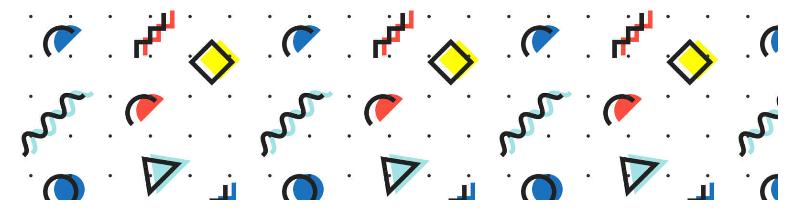
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傻屄”(twat) 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只不过当它是“挖苦、嘲笑”(twit)的一个学名。我在那个耳光过后明白了两点: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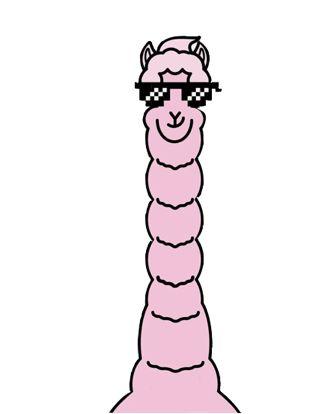
当然您看,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步入职业女性道路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脏话跟男同事们打成一片。要知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着仪器大喊“该死的狗屎”(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可以算作某种入团仪式。
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真他妈的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实验里有67名勇敢的志愿者,一桶冰水,一句脏话, 还有一块秒表。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脏话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
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纽带的功效。不论是在工厂车间,还是在戏剧排练场,科学家们都通过对照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全凭酣畅淋漓的一句——“我日!”脏话研究也帮助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脏话用于情感测评、量化,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已有超过150 年的历史。由此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的事实,包括大脑分为左、右半球,以及特定脑内结构如杏仁体在情绪发生、控制之中的作用。

脏话也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比如说,人在用非母语说脏话的时候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这一点指引我们去探寻人在早期教育阶段如何逐步了解情绪和禁忌。又比如,说脏话会使人心率加快并给予大脑暴力的暗示,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实际使用暴力的概率——真是应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俗语。
在集体的语言储备之中,脏话还是异常灵活易变的一环。社会禁忌不断变迁,脏话的面貌也得以代代变异。曾经的指天咒骂能够演化为喜悦之情的流露——足球球迷满口不堪的字眼,众所周知是不限于发泄愤懑与诅咒的。
在一次和伦敦大学同事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数千名足球球迷在比赛期间的脏话行为。对于脏话出现的频率,尤其是像“日”(fuck)、“ 屎、狗屁”(shit)这样的字词泛滥成灾的情况,我们早有准备。但是两者之间(“日”“屎”)呈现出某种比例关系且能与胜负形势高度吻合,倒是令人始料未及。是这样的:几乎毫无例外,“屎”等粗口对应的是球队失球或其他赛场上不利的状况,而“日”则不区分形势利与不利。另外,脏话连篇的球迷尽管看似鲁莽,其脏话的攻击性却远不及我们想象中的程度——在网络媒体上观测到的球迷骂脏话,几乎全部指向自己支持的球队或球员,而非赛事对方。

这项研究一经发表,着实让我品尝到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最先上门的是英国某著名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我不点名,但对于它雷厉风行的道德急先锋姿态,以及一面披露大幅女星长焦裸照,一面煞有其事地批评其“出位”,可谓老少皆知。两个质问劈头盖脸扔过来:一、浪费了多少钱在这项研究上面;二、可不可以从事一些有用的研究(比如癌症治疗)。
我的回答是:第一,统共6.99 英镑——研究小组自费的一瓶超市红酒,是我们在制定研究假设的时候喝的;第二,我与另外一位此次项目的负责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在医治肿瘤方面没有丝毫的专长,不得已只能把癌症患者托付给相应的专业人士。之后那家报社便再没回音,舆论风波不久也平息了。虽说如此,脏话研究仍为公共舆论所不齿,确实通过这次事件得到了验证。
尽管您可能对脏话也抱有“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成见, 但要知道在科学界,脏话研究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其抱有长久的兴趣,实在是有极好的缘由的:脏话现象看似不值一提,却恰恰能告诉我们人脑、思维以及社会是怎样运转的。
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 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他妈的放尊重点!

她为脏话写了本书
埃玛·伯恩,一名科研领域的特立独行者,像这篇文章开头讲的,因为小时候无意说了一句脏话而被扇了一个耳光,在此之后,他反而对说脏话这件事生出浓厚的兴趣,并且投入极大热情,以一种非正统的方式、秉持严肃的态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她结合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探究了脏话的起源及进化,以及说脏话的各种妙用,令人耳目一新。
埃玛·伯恩说,在她这本《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中,并没有把脏话作为单独的现象来剖析。她认为脏话非常“屌”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触类旁通、无孔不入,所以写着写着,必然会岔得远一点,甚至在有些章节中不提任何脏字。但是从日语拐弯抹角的语式,到黑猩猩的坐便训练,不管乍看之下再怎么不可思议地离题,她保证“我们是如何骂脏话的”这一点将会贯彻始终。
有人会问: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宣扬不和谐、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非也。埃玛·伯恩说,她绝对不希望看到脏话泛滥成灾。况且,脏话之所以还能有脏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上的震慑效果。反观过去一百年间主流脏话的变迁,可以轻易发现早先的脏话或消减于社会上的过度使用,或没落于普遍价值观的变革,而新的禁忌又不断被制造出来以填补空缺。与过去以不敬神、没有信仰为根基的脏话咒骂不同,当今社会视种族、性别歧视为大忌,也就因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咒骂。到底这是象征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霸权,还是代表了抗击恶毒偏见势力的可喜进步,这点就要留给读者您自己来判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