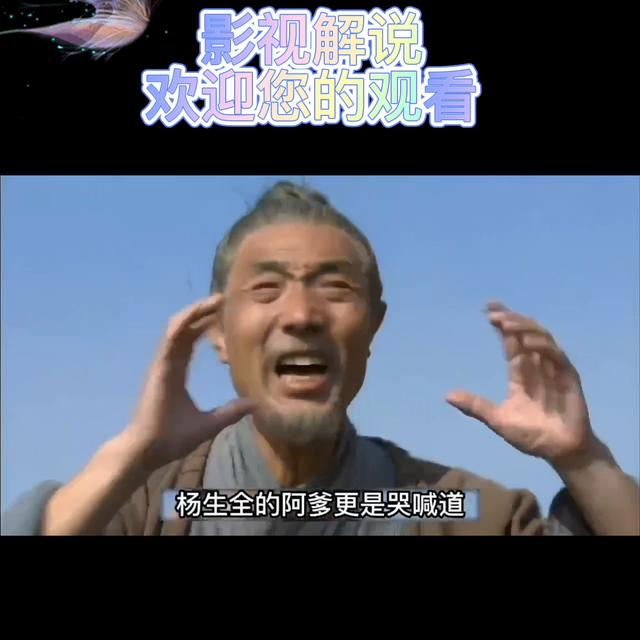大
姑
大姑姓刘,这是肯定了,但叫个啥,官名小名,至今想来好像从来就没有人知道。因为在她生前,我们打小就没有听过父辈们谁说过或者叫过大姑的名字。这一点,几十年后想想,的确奇怪。当然,还是我们疏忽大姑了,在父辈们生前,我们怎么就不问一下呢?
大姑因为比家父大许多,所以我们叫大姑妈。
大姑嫁到了隔河而望鸡犬相闻的香积寺,对姑父印象不深,他去世时我们还小。只记得是一个和气不善言谈的老头,姓王。

对大姑的最基本印象,就是从来没见她笑过,一张大脸,任何时候都在吊着,好像谁欠她钱似的。小孩们都怕大姑,逢年过节出门去她家或者她来我们家,小孩们都是见了面叫一声就赶快跑了。
大姑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一个胖大半大老人,一幅佛爷像,富态,周正,想起来应该在年轻时很是漂亮。也许,正是这,养成了她的傲气和“拿作”,以至于连比她大的大伯和比她小二伯、父亲,以及小姑,都对她有些“怕”,后来的兄弟媳妇就更不在话下了。在一起时,也都是尽量顺着她的话说话。听父辈们说,也不是怕大姑,而是她生性“暮叨”,谁也不想惹她。
大姑一双小脚走路颤颤巍巍,让人只操心脚承受不了体重。最早,回我们村时,经常都是表哥推一个独轮车她坐独轮车过窄窄的木板桥。自从潏河上修了水泥桥,过年过节,我们村里耍社火,都要事先派我们拉个架子车铺上席子被子去接她送她。这既是尊重,也是必需,因为大姑要的是这个“派”。这样,不管在香积寺,还是在我们周家庄,大姑就很有面子,端端正正地坐在车上,由香积寺村子拉出来,拉进周家庄,几乎走遍两个村子,大姑会满脸的自豪,这时人也和气了许多,大姑笑盈盈的还真是好看。
按说大姑也是嫁了个穷农家,应该也受了不少苦,不会不干农活和家务,要不家里咋维持,儿子咋长大?但在我们印象中,大姑又好像从来没见干过啥活,不管是我们去她家还是她来我们家,她都穿戴整齐干净,抄着手坐在热炕上跟长辈们说话,说儿子的辛苦,说媳妇的不贤惠。
大姑有一个儿子,即表哥,大我们很多岁,我们叫念念哥,是一个满脸胡茬的黑脸汉子。高个儿,魁梧,少言寡语,嗓音低沉饱满,叫人觉得即坚韧又无坚不摧。以至于在今后的人生中,每每说起浑厚,不管是高原还是大山,我都会想起表哥。
因为家里穷,加之木讷少语,表哥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娶到媳妇,这成了大姑的最大心事。还好,天下任何事情都有个了结,不管好与不好。
有人给介绍了个死了男人的年轻寡妇,尽管大姑心里十分别扭,觉得丢人,但表哥愿意,大姑也只能勉强认可,凑凑合合地为表哥办了婚事,总算成了家。
二婚的表嫂是女人里面少见的高个儿,两根长长的大辫子,白净,漂亮,开朗,能干。一过门,很快就显示出来是个好媳妇。
大姑家住在村子中间,左邻右舍房子差不多,都是惯有的两间蹶根厦子,一间半安间,不同的是大姑家安间盖在后面,临街是围墙,盖了个门楼。

自从表嫂进门,不管什么时候,一个窄窄的小院都扫的白光光的,连带门口街道,也是干干净净。
表嫂跟表哥很恩爱,从没有见他们高声吵过。
表嫂有一手绝活在我们那里很少见。每到过年过节,家家户户吃肉臊子长面是最重要的饭食和仪式。每次,都是表嫂自己擀面,她擀的面又薄又筋,最叫人称绝的,切面不是通常家家户户的把面叠起来切,而是摊开,用长擀杖逼着,一刀一刀地“剓”。整个过程,快速利落,如一幅舞台剧。
表嫂做饭,表哥烧锅,等饭做好了,第一碗一定是端给大姑。后来我也常常疑问,大姑也是苦出身,怎么就活像戏里演的地主婆呢?这个想法,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演秦腔白毛女时我就有了,老觉得大姑不用化妆直接上台就是个最形象的黄世仁他妈。
表嫂后来跟表哥生了两个儿子,比我们小一些,小名应该叫益信、红信。小时候经常跟我们一起玩。
大姑在文革期间去世了,后来不几年,因生活艰难和老一辈渐渐老去,表哥也就跟我们断了来往,以至于对于他们的情况再也没人知道。如果他们还健在,现在都应该有九十的人了。
悠忽之间,半个世纪过去,老一辈都已走了多年,小一辈也都成了老人。那些老一辈的事,有多少秘密也都随着他们的离世而带走,剩下的麟麟爪爪,抓也抓不住。
香积寺和周家庄很快就要拆迁,以后,就是连这些麟麟爪爪也将随风飘散,不知流落何处。
一切叫人唏嘘!
愿大姑恕侄子不敬。
文中采用了孙宝田先生两幅钢笔画,在此致谢!

作者简介
刘英雄,网名西岸老雄,陕西长安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潏水流梦》《看河》《风过城南以南》《遥远的乡愁》《沉月》等。
编辑:水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