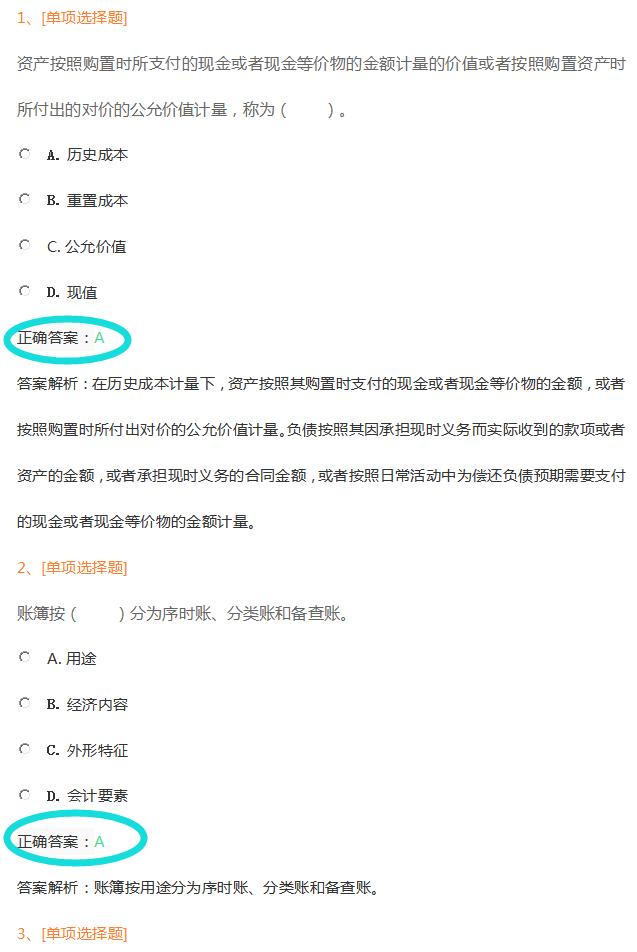三:布罗茨基诗《献给奥古斯塔的新诗篇》析(三)
5
水在我的前方汩汩地流淌。
霜伸手寻觅我嘴巴的缝隙。
人有两个裂开还怎么呼吸!
这可是面孔,抑或
山崩的景象?
我的笑是扭曲的笑;
横切那黎明沼地的
灌木丛因此悚然。
一阵雨将黑暗击成细末。
我的影子奔跑着,象个活物,
从这两片红肿的眼睑,
跃上松树和垂柳下的浪峰。
它消失在双重的阴影中,
我却无法效尤。
和曼杰斯塔姆对待寒冷时那种绝望的骄傲有所不同,布罗茨基在这首诗中则着重于对于寒冷的个性化体验-一种灵魂和肉体的双重寒冷,在诗人的笔触下处于过程和加深中。
霜伸手寻觅我嘴巴的缝隙。
人有两个裂开还怎么呼吸!
这可是面孔,抑或
山崩的景象?
至此诗歌的幻觉中出现了两组画面:面孔和山崩的景象,这一小一大,一细腻一壮观的对比呈现的是陌生化的美感,或许是愁苦的面孔会呈现出山崩的碎裂感,又或许山崩的景象系一张空洞的面孔凝固而成,继而被赋予成为永恒的可能性。面孔和山崩的并列出现为文学美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而当诗人写出面孔的固定表情:笑。霜的探寻和两个裂口带来的尴尬,诗人进行了如下表达:
我的笑是扭曲的笑
“扭曲”一词的出现既使笑容变得更加清晰,也更明显地表达了诗人情感的倾向性,通过一个有意味的词,快乐不再是单纯的快乐,那究竟会是什么呢:无奈?麻木?抑或……
横切那黎明沼地的
灌木丛因此悚然。
一阵雨将黑暗击成细末。
以上三句诗运用了拟人手法对意境进行了烘托,因恐惧于那扭曲的笑,横切那黎明沼地的灌木丛悚然,而完全的黑暗在被雨击成细末之后,诗人的影子便出现了:
我的影子奔跑着,象个活物,
从这两片红肿的眼睑,
跃上松树和垂柳下的浪峰。
以影子衬托孤独的最著名诗句,莫过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本诗中的这一小段,其写作手法也异曲同工:我外之我,我观之我-影子在奔跑,在跳跃,相比于诗人内心沉闷的孤单,和影子的和谐共处为诗人带来了一点点心情的亮色。
它消失在双重的阴影中,
我却无法效尤。
6
踩进再拔出。咀嚼那朽败的小桥。
教堂公墓周围的泥淖
啜饮木十字架上的青黛。
就连碧绿的草叶
也不能染得它一丝绿色。
践踏那燕麦仓,
狂奔在密集的叶簇间。
深深地刺入土中,
唤起一切的死人,一切的亡魂。
在那泥土里,在这我心中。
让他们逃走,抄着近道儿飞奔,
穿越这麦茬,钻进空寂的村庄。
让他们挥舞稻草人的帽子迎接
飘然而至的秋日-突如鸟儿其来。
随着旋律的推进,诗人“踩进再拔出”的动作还在机械地持续着,如同节奏感很强的鼓声,初步定位了这一节诗歌的音型和背景。
“咀嚼那朽败的小桥”这一句因咀嚼一词出现了些许歧义,这小桥是面包,是食物,如此让人如鲠在喉?歧义是带领读者好奇心的前提,至此诗人笔锋一转:
教堂公墓周围的泥淖
啜饮木十字架上的青黛。
在这里,泥淖带给人的感受是污浊和拖沓,笔者认为以上诗句的本意是泥淖溅在了教堂公墓的木十字架上,“啜饮”呈现的拟人化手法更是写尽泥淖的黑暗和贪婪:
就连碧绿的草叶
也不能染得它一丝绿色。
美好被玷污,光芒被遮蔽无疑会让人心痛,诗人则采取了以下的行动:
践踏那燕麦仓,
狂奔在密集的叶簇间。
深深地刺入土中,
唤起一切的死人,一切的亡魂。
在那泥土里,在这我心中。
是的,究其世界的本质,死亡注定不可避免。我们在通往死亡的大路上,也许会有青春,爱情这些碧绿而生机盎然的草叶,但它们终将被啜饮,使经历此经历的人因其得而复失更加痛苦。况且,当心灵失去了青春和爱情的感受,这种心死的冰冷会更独特,更尖锐,上文中的一个刺字,定下了本节诗里渴望交流和持续痛苦的基调,而且还是-深深地刺入。
被刺入之后必将是更深刻的幻觉和孤独,需要伴侣,需要理解,需要活的诗人,竟然要唤起亡魂来作为自己交流和恳谈的对象,这种主体的奇特情绪在继续深化,制约并规定着诗人对身外世界的反映和观察:
让他们逃走,抄着近道儿飞奔,
穿越这麦茬,钻进空寂的村庄。
让他们挥舞稻草人的帽子迎接
飘然而至的秋日-突如鸟儿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