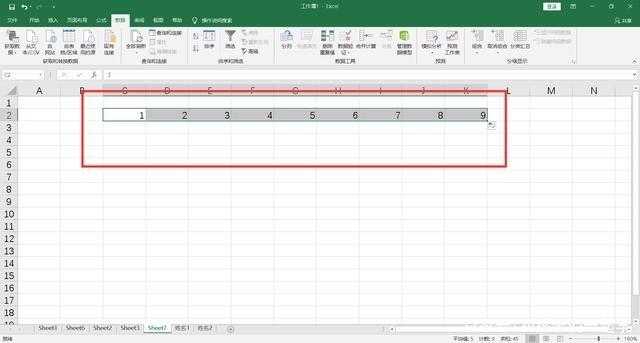苏珊娜·西马德(Suzanne Simard)出生于一个伐木世家,长大后成为第一批投入伐木行业的新一代女性。然而,她儿时目睹的那个会自然修复的森林已不复存在。大树被砍伐一空,补种的人造林却溃不成形。怎样才能实现森林再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珊娜将她的一生献给了森林。

本文经授权节选自《森林之歌》(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有删改,标题为编辑所加。前往“返朴”公众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此书。点击“在看”并发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区,截至9月18日我们会选出2条留言,分别赠书一本。
撰文丨[加]苏珊娜·西马德(Suzanne Simard)
翻译丨胡小锐
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他与自然的战争必然成为一场针对自身的战争。
——蕾切尔·卡逊
我走进艾伦·维斯的办公室,他微笑着和我握手。他凹陷的双颊和高科技运动鞋告诉我,他认真地对待跑步这项运动。他示意我坐在他的橡木办公桌旁。桌子的一边是一堆整整齐齐的期刊文章,而他的面前放着一份尚未完成的稿件。书架上堆满了关于森林、树木和鸟类的书籍,旁边是衣帽钩,上面挂着他的森林巡查员专用背心、雨衣和望远镜,下面是工作靴。这是一间政府办公室,有米黄色的墙壁,窗外是一个停车场,但整个房间很舒适,让人感觉这里进行过很重要的会谈。我瞥了一眼滴在我T 恤前面的蛋黄。他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表现出来。虽然他的表情很严肃,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善意。他询问了我的丛林工作经历、兴趣爱好、家庭背景和长期目标。
我挺直身体,向他介绍了我的暑期工作和在林务局做的生态系统分类工作。“那些是在行业内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我说道。我认为对于一个只有23 岁的人来说,这样的背景是非常全面的。我希望他持相同的看法。
“你做过研究吗?”他问道。他浑浊的绿眼睛盯着我,仿佛正确答案就藏在我的脑后。看来,他找到了我简历上的空白区。
“没有,但我在攻读本科学位期间担任过几门课程的助教, 还在林务局做过研究助理。”我回答道。我的喉咙发紧,因此我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能畏缩。
“你了解森林再生吗?”他在黄色的便笺簿上潦草地写着什么。两个穿着绿色裤子、灰褐色衬衫的护林员从旁边大步走过, 其中一个拿着铁锹,另一个拿着马桶水箱一样的东西——带手持水泵的背携式水罐,这是用于救火的。
我告诉艾伦我在利卢埃特山上栽种的幼苗都发黄了,我想知道那些人造林为什么会失败。我没有说我不打算回到那家伐木公司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但我告诉他,我发现仅仅在栽种意见书上做文章,永远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为在这么多其他因素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想孤立地考虑我遇到的树根问题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我当时准备订购根系较大的树苗,把树苗栽种到半腐层中,栽种到有菌根真菌的其他植物旁边,希望这些真菌能接触到树苗。
他跟我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学习实验设计。”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统计学方面的旧书。我注意到他的森林经济学硕士学位证书和林业本科学位证书都装在相框里,并排放在书架上。他的硕士学位是多伦多大学授予的,本科学位是阿伯丁大学授予的。艾伦有英国口音,但我猜他也有苏格兰血统。
“我在大学学过统计学。”我说。看着他桌上摆放的因为多年表现突出而获得的奖章(金色饰板上蚀刻着一棵树和他的名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菜鸟。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学位都没有让他为设计实验做好准备,所以他只好自学。听他这样说,我放松下来了。
艾伦那里没有空缺岗位,但他肯定地告诉我,春天可能需要人调查“自由生长人造林”,到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
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自由生长”是什么意思。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还在想自己是否彻底没有机会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要求彻底清除邻近的植物,使针叶树幼苗可以自由生长,不必遭遇任何非针叶树的竞争。非针叶树指的是所有原生植物,它们被视为必须根除的杂木。这一政策源于美国越来越将森林视为林场的集约化做法。但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幼苗必须在越橘、桤木和柳树附近生长。我真是个白痴, 我想。我为什么要提到那些发黄的幼苗呢?他会觉得我的世界太小了,会认为我只关心那些发黄的幼苗。现在是11 月,春天还很遥远,即使他认为我适合那份工作,到那时他也会忘记我的。
2 月份,艾伦打来电话。他为我找到了一个合同项目,让我调查高海拔皆伐区清除杂木的效果。这并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但它可以培养我的研究技能。艾伦愿意帮我设计这个实验, 并指导我完成研究。不过,我需要雇人帮忙做丛林里的工作。
我们的实验将在落基山脉西面卡里布山脉的高海拔恩氏云杉和亚高山冷杉林中进行。我和萝宾来到了离实验场地最近的蓝河镇。为了支持皮毛贸易以及铁路和黄头高速公路的建设,这个小镇作为一个定居点早在100 年前就已经建成了。在此居住了至少7000年的恩拉卡帕穆克斯人被赶走,迁移到了蓝河和北汤普森河交汇处一个狭小的保护区。
我要干什么呢?我负责的实验要求我杀死植物,这同样是一种驱赶原住民的行为。我突然觉得我的任务与我的所有目标都背道而驰。
这片有300 年历史的森林在几年前被砍伐一空,没有了遮蔽阳光的树冠,因此白色杜鹃、假杜鹃、黑越橘、醋栗、接骨木和山莓都长得非常茂盛。灌木的枝杈向周围伸展,结出了一片叶子、花朵和浆果的海洋。锡特卡缬草、橘黄山柳菊和铃兰等草本植物也在疯长。尖针云杉的种子在它们中间发芽。后来,作为对这种自然种植的增强,人们还栽种了苗圃培育的云杉幼苗。但是,栽种的树苗每年只能生长半厘米,远远不能满足未来砍伐的期望,而且许多树苗已经死亡。因此,这片皆伐区“补种新树苗的效果不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司的林务员计划喷洒除草剂,以杀死灌木,将栽种后存活的多刺云杉幼苗从这些灌木的遮蔽下“释放”出来,使它们独享阳光、水分和营养物质。孟山都公司在20 世纪70 年代早期发明的除草剂镇草宁(亦称农达),可以让原生植物中毒,而不会影响到针叶树幼苗。尽管镇草宁深受欢迎,许多人在他们的草坪和花园随意使用这种除草剂,但执拗的温妮外婆是个例外。根据人造林的设计思想,杀死叶子茂盛的植物将使树苗免于竞争,然后这些公司就可以履行其“自由生长”式放养的法律义务。自由生长就像变魔法一样,100 年后又能再来一次皆伐,这要比任由它自然生长快得多。因此,只要是自由生长的人造林,都会被认为管理有方。
在我设计实验,测试不同剂量的除草剂杀死原生植物、“释放”下层树苗使其免于竞争的效果时,艾伦为我提供了帮助。根据推测,使用除草剂有助于树苗存活和快速生长,从而满足种植数量和高度增加的标准,以符合自由生长政策的规定。这就是我和萝宾要在这片皆伐区完成的任务,尽管我有些担忧。艾伦也不喜欢这个新政策,但他的工作就是测试杀死灌木是否能提高人造林的生产率。他跟我说过,他认为这个政策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从政府相信的事情出发,通过严谨、可信的科学研究,说服政府做出改变。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逐步弄清楚不同剂量的除草剂对树苗和植物群落的影响,看看我们是应该使用除草剂,还是应该拿起剪刀,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看看杀死非经济作物是否真的能创造出一个自由生长的、相比任由原生植物蓬勃生长更健康更多产的人造林。
在艾伦的帮助下,我设计了4 个除草方案,测试了3 种镇草宁剂量(每公顷施用1 升、3 升和6 升)外加1 个手动除草方案的效果。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对照组,让那些灌木丛保持原样。这5个方案都需要重复实施10次,以确定哪种效果最佳。在利用50个圆形地块进行重复试验时,每个地块随机使用其中一个方案。一位统计学家批准认证了我们用图形表示的实验设计。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打开了大门。在艾伦的指导下,我设计了我的第一个实验!
虽然我极不喜欢这个实验的目的,因为我知道它与我们的正确方向背道而驰,但我觉得离解决我那个发黄小树苗的难题又近了一步。
在随后的这个星期,我们开始做实验。我和萝宾按照我和艾伦画的图,利用指南针和尼龙链绳确定了50 个圆形地块的中心点。每个地块的直径约为4 米,跟绳球场差不多大小。中心点间距10 米。总之,我们这个网格地块大小是100 米乘50 米,或说0.5 公顷。完成这些工作后,我们接着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辨认各个地块内的植物、苔藓、地衣和蘑菇并计算它们的数量,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除草方案效果如何了。
几天后,我们在凌晨5点出发,按照除草方案喷洒除草剂。在最后一个拐弯处,我在一个绳索路障前猛地刹住车。三名抗议者挥舞着标语牌,抗议我们喷洒除草剂。其中一个动作敏捷的人从萝宾在蓝河酒店工作时就认识她了。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在确定我们做实验的目的是证明不需要使用除草剂,而且将来我们会阻止使用除草剂之后,才给我们放行。
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到来了。我在坎卢普斯农场用品店的柜台上买镇草宁的时候发现任何人走进这家店都能买到镇草宁。我应该感到庆幸,起码我需要申请许可证才能在归政府所有的土地上喷洒。萝宾皱着眉头,因此她内心的担忧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我按照每公顷1 升的除草方案,量出所需的粉色液体,把它倒进蓝黄两色的20 升背携式除草剂喷雾器中,然后加入适当的水进行稀释。我教萝宾像我一样戴上防毒面具,穿好雨衣。我仍然是她的妹妹,我们之间的关系(由谁做主)只是暂时调换了。她这辈子都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姐姐,但现在轮到我来确保她不会中毒。
萝宾戴上防毒面具,把带子系紧。她透过护目镜直瞪瞪地看着我,好像在说我最好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她的黑色长发向后梳着,露出了褐色的、棱角分明的脸和魁北克人典型的瘦削鼻子。“好重啊。”她一边嘟哝,一边把那个笨重的方形水箱(大约25 磅重)背到后背,然后解开了连接伸缩杆的皮管。我向她展示了我在妈妈的院子里用水练习取得的成果,告诉她在喷雾时需要摇动手柄。
在测量植物时,我们可以轻松地避开木头和灌木丛,但是现在它们把我们脚下的路变成了障碍跑道。萝宾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她冲着我喊道:“我看不见了,苏西!”由于戴着防毒面具,她的声音有点儿闷。我像导盲犬一样,把她引到了第一个地块。
她挥舞着黑色的伸缩杆,一边在盛开的杜鹃花上喷洒毒雾, 一边抱怨说她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和我一样,不愿意杀死这些植物。穿着雨衣,戴着防毒面具,还要背着一个装满毒药的水箱,这让她的心情糟透了。
我告诉她我会在旁边的10 块土地上喷洒6 升除草剂,希望能让她觉得我安排给她的任务没有那么令人痛苦。
当天晚上,我们去蓝河军团酒吧喝啤酒。酒吧的墙壁上挂着紫色挂毯,当地人坐在破塑料凳子上。一个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来啤酒。萝宾礼貌地说啤酒没什么泡沫,那名服务员说:“亲爱的,我们这里不卖奶昔。”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精确地完成了所有用到除草剂的方案。超级棒!几天后,我们又带着工具,对指定的那10 块土地进行了手工除草,还留下10 块地作为不处理的对照组。接下来,我们要等上一个月,才能衡量这些方案的效果。我非常愿意学习如何在森林里做实验,但我不愿意杀死这些植物以测试一个我本来就认为不正确的森林管理办法。
再次来到试验场地时,我们发现被喷洒最大剂量除草剂的杜鹃、假杜鹃和越橘已经枯萎死亡。死亡的不只是灌木,而是所有的植物——连野山姜和野兰花都死了。地衣和苔藓变成了棕色,蘑菇已经开始腐烂。一些灌木长出了新叶,但那些新生的叶子已经发黄,明显发育不良。一度饱满圆润的浆果从枝头掉了下来,连鸟都不吃。只有带刺的云杉幼苗还活着,它们的针叶仍然苍白,看起来发育得不好,有些还滴着粉红色的水滴,但毫无疑问,突然暴露在充足的阳光下,所有针叶都不太适应。大多数被喷洒中等剂量除草剂的目标植物也死亡了,但还有一些仍然没有变色,因为在喷洒除草剂时,它们藏在更高的植物的叶子下。在喷洒最小剂量除草剂的地块上,大多数植物仍然活着,但受到了伤害。剪过的灌木的茎已经重新发芽,盖过了树苗。由此可见, 对于自由生长的人造林来说,最好的方案就是使用最大剂量的除草剂。
萝宾都快哭了。她想知道镇草宁是怎么杀死这些植物的。她说:“我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我们面对情感上的创伤时,她总是首当其冲。她会咬牙承受各种不公正,希望能解决问题。
我盯着自己的脚,因为我们都哭的话,就会越哭越伤心。这些植物是我的盟友,不是敌人。我在脑子里飞快地想了一遍这么做的理由。我想学习做实验,我想成为一名森林侦探。这是为了更远大的利益,是为了从根本上拯救那些树苗。我会找到证据,证明采用除草剂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并提出帮助树苗生长的其他方法,供政府调查研究。我看着一株糙莓,它的茎光秃秃的,耷拉在一些新露出来的苍白的树苗上。尽管苦苦挣扎,但它取得的唯一成果就是在基部发出了一小簇黄色的叶子,就像插满针的针垫一样。这种除草剂应该不会伤害鸟类或动物,因为它的毒性只针对草本植物和灌木体内产生蛋白质的酶。
但那些蘑菇已经干瘪、死亡了。
那是我们最喜欢的鸡油菌,它们都死了。
根据直觉,我认为病苗面临的问题是它们无法与土壤结合,需要真菌的帮助。但即便得到了真菌的帮助,在这里幼苗也会生长得很慢,因为一年中有9 个月在下雪。我对萝宾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杀死植物,包括一些是真菌宿主的灌木,而我认为真菌对树苗来说是有益的。各家公司都疯狂地用直升机地毯式喷洒镇草宁。也许我们的实验会证明这个计划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好。
萝宾说:“看看这乱七八糟的场面,难道还看不出这个计划是错误的吗?”很难想象,竟然有人认为“自由生长”是一个好主意。
那天晚上回到营地后,我们的心情很不好,都没有吃晚饭。我蜷缩在睡袋里,萝宾待在她的帐篷里,两个人一声不吭。很难说我们到底是因为除草剂感到不适,还是我们因为对植物使用除草剂感到后悔。
实验表明:除草剂的剂量越大,效果就越好。看到这个结果,艾伦摇了摇头。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他说这些证据仍然无法检测除草计划是否有助于树苗,它只是证明了大剂量的除草剂可以除掉所谓的杂木。没有时间悔恨,要想阐明树苗和邻近植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学会如何进行“除草”试验之后,我得到了一份规模更大的工作合同,测试不同剂量的除草剂和手工除草能否杀死锡特卡桤木、叶形狭长的斯考勒氏柳树、白皮的纸桦(北美白桦)、会长根出条的颤杨和长得非常快的三叶杨,能否清除开紫花的火草、丛生的红拂子茅和顶部呈白色的锡特卡缬草,能否杀死本地植物——包括可能会阻碍苗圃树苗生长的树。苗圃培育的主要是多刺云杉、美国黑松和软针花旗松的树苗。这三种针叶树(尤其是美国黑松)利润丰厚,耐受力强,而且长得快,因此全省所有的皆伐区几乎都种上了这些树种。越早杀死这些讨厌的原生树木和植物,越早实现自由生长,就越有利于公司早日履行管理好人造林的义务。
自由生长政策的实施相当于针对原生植物和阔叶树发起的全面战争。我和萝宾不太情愿地成了专家,通过砍、锯、环割、喷洒除草剂等方法,消灭全省范围内新生森林里的阔叶树、灌木、草本植物、蕨类植物和其他毫无防备的生物。这些植物都必须被清除掉,至于它们为鸟类提供巢穴,为松鼠提供食物,为鹿和熊崽提供藏身之处,为土壤添加养分,防止土壤侵蚀,这些都无关紧要。人们根本不关心绿叶桤木能提高土壤中氮的含量,它们将被砍伐一空,烧成灰烬,为栽种树苗让路。人们不关心一束束的红拂子茅可以为花旗松的新芽遮蔽阳光,防止皆伐区无遮无挡的毒辣阳光将它们烤焦。人们也不关心杜鹃可以保护矮小的带刺云杉幼苗,防止它们被寒霜冻伤。开阔地的霜冻比树冠下厉害得多。
这些他们都不关心,他们的想法简单明了,那就是:不要竞争。一旦消灭原生植物,不让它们占用阳光、水分和养分,那些利润丰厚的针叶树就会独占这些资源,像红杉一样快速生长。这是一场零和游戏,成功者占有一切。
我就是一名士兵,参加了一场违背了我的信仰的战争。从我们开始这些新的实验时起,那种熟悉的负罪感就困扰着我。但我参加这个项目是为了获得最终的奖励:学习科研方法,找出栽种树苗的致病原因。
在所有的方案中,只有一种方案能促进针叶树生长。当然, 它也会降低原生植物的多样性。以桦树为例,清除掉它们可以促进一些冷杉生长,但会导致更多的冷杉死亡——这与人们的预期相反。桦树的根受到砍伐和除草剂的压力后,无法抵抗土壤中天然存在的致病蜜环菌侵害。这些真菌感染了受到除草计划影响的桦树根部后,还会传播到附近的针叶树的根部。而在对照组中,未受影响的白皮桦树与针叶树混杂着生长,土壤中的致病菌受到了它们的抑制。就好像是桦树制造出了一种促使致病菌与土壤中其他生物保持稳态的环境。
我到底还能撑多久呢?
不久之后,我的好运来了。
林务局有一个永久性的造林研究工作岗位需要招人。我和4 名年轻人一起提交了申请。一些科学家从首府飞了过来,以确保招聘过程的严格和公平。当我得知自己得到了这份工作时,简直不敢相信我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艾伦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现在,我可以自由地考虑我认为重要的问题了,至少我可以尝试说服出资单位,让他们相信哪些问题非常重要。我可以在实验中根据我对森林生长的认识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测试政策驱动的那些处理措施——那些措施似乎会破坏森林的生态,使问题恶化。我可以基于自己积累的经验开展科学研究,了解如何更好地帮助森林从砍伐中恢复过来。我测试除草剂方案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我真的可以认真考虑树苗到底需要从真菌、土壤和其他植物或树木那里得到什么这个问题了。
我得到了一笔研究经费,测试针叶树幼苗是否需要与土壤中的菌根真菌连接才能生存。我还添加了一项内容:研究原生植物是否有助于它们建立连接,并建议对栽种在不同群落中的树苗和那些单独种植在光地上的树苗进行比较。我对这个项目的想法,以及我能成功得到这笔经费,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边境线以南林业出现的新情况。当时,由于森林破碎化和斑林鸮等物种受到的威胁令公众忧心忡忡,美国林务局进行了一些变革。科学家逐渐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包括真菌、树木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对森林生产率来说很重要。
单一的物种能茁壮成长吗?
如果树苗与其他物种混合种植,会使森林更健康吗?将这些树和其他植物一起成片栽种,会促进它们生长吗?还是说应该让它们以棋盘格的形式,彼此间保持距离?
这些测试也可以帮助我了解高处的亚高山冷杉和低处的花旗松都成簇生长的确切原因,帮助我了解生长在针叶树旁边的原生植物对针叶树与土壤的联系是否有促进作用,生长在阔叶树和灌木旁边的针叶树根尖上是否有更多颜色鲜艳的真菌。
我选择纸桦作为我的试验物种,是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它能产生丰富的腐殖质。这些腐殖质不仅是小时候的我喜欢的一道美味,对针叶树也是有益的。此外,纸桦似乎可以抵御根部致病真菌的侵害。对木材公司来说,桦树毫无价值。但对其他人来说,它浑身是宝:白色树皮有很好的防水效果,树叶可以遮阴,汁液可以提神。
这个实验应该非常简单吧。
但事实让我大吃一惊。
我计划测试三个利润丰厚的树种(落叶松、雪松和冷杉)以不同方式与桦树混合种植的效果。我选择这三种树作为测试物种,是因为它们是那些未经砍伐的原始森林中的原生植物。我喜欢雪松像辫子一样的长针叶,喜欢花旗松像洗瓶刷一样光滑的侧枝,喜欢落叶松像星星一样的针叶,到了秋天它们会变成金色, 然后散落在森林地面上。当时伐木业认为桦树是最恶毒的竞争树种之一,因为他们认为桦树会遮蔽他们青睐的针叶树,阻碍针叶树的生长。但是,如果桦树树苗对针叶树有益,哪种混合种植方案会产生最健康的森林呢?这三种针叶树对桦树遮阴面积的适应性各不相同。星形针叶的落叶松可以适应的遮阴面积很小,辫状针叶的雪松可以适应大面积的遮阴,花旗松(花旗松是松科冷杉亚科黄杉属植物,俗名北美黄杉,因此书中有时会以冷杉代指)的适应能力介于两者之间。仅这一点就表明,最佳混合方案会随着物种不同而变化。
我确定了一个设计方案:首先在一块地上将纸桦与花旗松配对,然后在另一块地上混合种植纸桦与北美乔柏,再然后在第三块地上把纸桦与西部落叶松混合种植在一起。第三块地曾经是皆伐区,在这块地上进行过的人工种植失败了,连黑松都没有成活。我计划在另外两个皆伐区做同样的实验,看看地形稍有不同时,这些树会有什么反应。
我为每一种配对安排制订了多个混合方案,以便对这些针叶树独自生长时的情况和它们按照不同密度、不同比例与纸桦混合生长的情况进行比较,测试我的直觉是否准确——某些配置(例如:与落叶松混合时,纸桦的数量比落叶松少;与雪松混合时,纸桦比雪松多)是否真的会让混交林长得更好。我猜测纸桦会导致土壤的养分更加丰富,同时还是针叶树的菌根真菌来源。我之前做的实验也表明,桦树在某种程度上还能防止针叶树因为蜜环菌根病而过早死亡。
我总共设计了51 个不同的混合方案。实验将在三个皆伐区进行,每个混合方案对应一个独立的地块。
我开始在人造林做除草实验,观察植物和树苗一起生长的效果。几百天之后,我感觉到树木和植物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察觉到它们与邻居之间的距离,甚至能察觉到它们的邻居是谁。如果松树幼苗位于向四周蔓延、能将氮固定住的桤木中间,那么枝条向外伸展的程度会远远大于被茂密火草覆盖的树苗。云杉的芽会紧挨着鹿蹄草和车前草,但是与防风草保持较大距离。冷杉和雪松喜欢适度遮阴的桦树,但如果头顶上还有茂密的糙莓,它们就会萎缩。另外,落叶松需要与相邻的纸桦保持一定距离,才最有利于生长,根部病害致死率也最低。我不知道植物是如何感知这些条件的,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试验这些混合种植方案时必须精确。树木之间的距离也必须精准,因此必须寻找地面平坦的皆伐区。鉴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山地形,要找到三处平坦的试验场地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在查看树根、追踪调查针叶树种植在纸桦旁边时与土壤的连接是否比单独种植时更紧密之前,我尽可能做了精心准备:订购了一台立体显微镜和一本关于辨别菌根特点的书,并利用我在回家的路上采集的纸桦与冷杉进行练习。每次我把样品拖进公寓中由储藏室改成的办公室时,琼都会翻白眼,然后取笑我说我每次承诺做晚饭都会把锅烧煳。我善于做辣椒,她的专长是意大利面,但我们俩都对烹饪不感兴趣。我会躲在我的地下办公室里, 在那里忙到午夜。切除根尖,制作横切片,然后把它们装在显微镜载物玻片上。很快,我就能熟练地辨别哈氏网、锁状联合、囊孢菌,以及菌根根尖上有助于区分不同种类真菌的多个部位。
软针冷杉上有一些真菌似乎与纸桦上的真菌同种。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纸桦的菌根真菌或许会连到冷杉的根尖上,对它们进行交叉授粉。这种共同接种或共享真菌的现象,或者说共生关系,或许有益于新种下的花旗松幼苗,使它们的根不至于光秃秃的,使它们没有像我之前在利卢埃特山看到的发黄的树苗那样被判处死刑。林务员们推测,如果冷杉需要纸桦,纸桦就应该不会伤害冷杉。
经过几个月的搜寻,我找到了三个地势平坦的皆伐区,都是政府的土地。可能是因为生物失衡,在这些土壤上种植的人造松树林都失败了。在其中一块地上,我和一个在那里非法放牧的牧民发生了冲突。他大声抗议我把失败的人造林改造成试验场的想法,说他在这里住了多年,有使用这个皆伐区的权利。我反驳说,作为一名林业研究人员,我有权利用这个伐木区,而他是在侵犯公共财产,但他似乎不为所动。
见鬼了!这是我最不想见到的。
种植试验的准备工作又花了几个月时间。我需要在地面上逐一画出81600个种植点。首先,我们必须处理这三个伐木区的根病感染问题。原先的砍伐留下了大约2万个树桩。由于蜜环菌根腐病会感染死树的根,并以寄生的形式传播到幸存的树木上,我们需要将这些树桩从土壤中清理出去。大约有3 万棵受感染的松树已经死了或快要死了,或状况极差,所以它们必须和受感染的原生植物一起被清除掉。挖掘给森林地面造成了损害,留下了一堆堆树桩、死树苗和患病的原生植物。后来,推土机把它们都推到了树林边缘。至此,试验场地清理完毕。
在那些残枝败叶清理掉之后,我甚至不敢确定这个场地像农场还是像战场。我的研究经费不包括建造拦牛木栅的费用,所以我在入口处横贯马路画了一个假木栅。我听说牛不敢跨过马路上画的线,因为怕摔断腿。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这种方法确实奏效了。第二年夏天,我和同事在炎炎烈日下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历尽艰辛,终于把树苗种在了确切的位置上。
几周之内,所有的树苗都死了。
我惊呆了。我从未见过失败得如此彻底的人造林。检查发现,它们的茎有腐烂现象,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受到了严重的晒伤或冻伤。我把树根挖出来,放在家里的显微镜下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病理性感染迹象。但它们让我想起了在利卢埃特看到的经过防腐处理的云杉根。它们没有长出新的根尖,只有黑色的、没有分枝的次生吸收根。我回到试验场地,看着那一丛丛茂盛的鸭茅,很奇怪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就在这时,那位牧民开着车过来了。“你的树死了!”他笑着说,眯起眼睛看着那些死树苗。
“是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十分清楚。失去这块放牧场地让他异常愤怒,于是他在这个皆伐区洒下了大量的草籽。
我和同事们一边小声嘀咕着(主要是我),一边把草清除掉,然后重新种上了树苗。但种植再一次失败了。所有的混合方案都失败了:首先死去的是白皮纸桦,然后是星形针叶的落叶松,再然后是叶子像软瓶刷一样的冷杉,最后是辫子状针叶的雪松。先后次序与它们对光线和水资源短缺的敏感程度一致。
第二年我们进行了第三次尝试,又失败了。然后是第四次种植。
树苗仍然全部死亡。那个地方就像一个黑洞,除了茂盛的草什么都种不活。牛来到了场地上,对着我们得意地笑着,我想把所有的牛屎都收集起来,倒在那位牧民的卡车上。我猜想第一年种的树苗是被那些草抢去了水分,但我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怀疑土壤本身也出了问题。我马上想到了那位牧民,但是我心里知道我的场地准备工作非常充分,已经把林地表面置换了一遍,表层土都刮走了。因此,把责任推给那位牧民肯定于事无补。
花旗松和落叶松只会与包裹在根尖外面的外生菌根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而那些草只会与可以穿透根部皮层细胞的丛枝菌根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树苗之所以死亡,是因为它们需要的菌根真菌被那些该死的草才会喜欢的菌根真菌所取代。我突然意识到,这位牧民帮助我解决了困扰我的那个最深刻的问题:与合适的土壤真菌建立连接,对树木的健康来说是否至关重要?
第五年,我再次种下了树苗,但这一次我从邻近森林的成年桦树和冷杉树下收集了一些活土。我在1/3 的种植穴中各放了一杯活土。我打算把这些幼苗与另外的1/3 种植穴中的树苗进行比较,后者是平整土地后没有加入活土就直接栽种的。我还在最后1/3 的种植穴里放了在实验室里辐射处理以杀死真菌的老林土壤。这有助于我搞清楚一个问题:移土可以改善树苗状况,是否因为土壤里面有活的真菌或者有某些化学成分。在5次尝试之后,我感觉我很快就会有所发现。
第六年,我又回到了试验场地。种在老林土壤里的树苗长得非常好。不出所料,那些没有移土或移土经辐射处理变成了死土的树苗都死了,它们像往常一样遭遇了病害。多年来,病害问题一直困扰着它们,也困扰着我们。我挖出一些树苗作为样本,带回家用显微镜观察。果然,死苗没有新生的根尖。但是当我查看生长在老林土壤里的树苗时,我惊讶得跳了起来。
天啊!根尖上覆盖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真菌,黄色、白色、粉色、紫色、米色、黑色、灰色、奶油色,各种颜色应有尽有。
原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壤。
琼已经成了花旗松林和干旱寒冷地区树苗普遍生长不良问题的专家,我拉着她,让她也看一看。她摘下眼镜,朝显微镜里看了看,喊道:“完美!”
我喜出望外。但我也知道,我只是触及了表面。西马德山上最近出现了无数个皆伐区,原始森林被彻底摧毁。我曾驾车在那条沿着海岸新修的伐道上驶过。我们过去常在那里停泊爷爷的船屋,吉格斯遇险的户外厕所以前就在那里,还有亨利爷爷的水车和水滑道。现在,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皆伐区。砍伐、单作种植和喷洒除草剂彻底改变了我童年的森林。在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也为无情的砍伐感到痛心。我感到自己有责任站出来。我认为政府的政策削弱了树木和土壤之间的联系,破坏了土地,也破坏了我们与森林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必须站出来反对这些政策。
我对这些政策和做法背后的狂热有所了解,那是一种金钱支撑的狂热。
在离开实验场地的那天,我停下来汲取森林的智慧。我走到老鹰河边一棵树龄较大的桦树前。我曾在那里收集一些泥土移到种植穴中,它的粗大结实的树干四周都长有纸一样的树皮。我抚摸着它的树皮,低声向它致谢,感谢它向我展示了它的一些秘密,感谢它拯救了我的实验。
然后,我许下一个诺言。
我承诺,我一定要弄清楚树木是如何感知和发送信号给其他植物、昆虫和真菌的。
搞清楚它们是如何把消息传送出去的。
土壤中真菌死亡,以及菌根共生关系终止,揭开了我第一批种植的小树苗发黄死亡的谜底。我已经确定菌根真菌被意外杀死也会导致树木死亡。我从原生植物那里获取腐殖质,并将腐殖质中的真菌放回人造林的土壤中,这种做法对树木起到了帮助作用。远处,直升机正在向山谷喷洒化学制剂,以杀死颤杨、桤木和桦树,以便种植云杉、松树和冷杉等经济作物。我讨厌这种声音。我必须阻止它。
我对这场针对桤木的战争尤其感到困惑,因为弗兰克氏菌(桤木根部的共生细菌)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可以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氮,而小灌木可以利用这些转化后的氮制造树叶。当桤木在秋天落叶并腐烂时,氮被释放到土壤中,松树可以通过根吸收这些氮。这种氮的转化过程对于松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些森林每100 年就会发生火灾,大部分氮随之被排放回大气中。
不过,如果我希望在森林实践方面有所作为,那么我还需要更多关于土壤条件以及树木如何与其他植物建立联系并向它们发出信号的证据。艾伦鼓励我回大学读研究生,继续提升自己的能力。我当时26岁,几个月后我来到位于美国科瓦利斯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始攻读硕士学位。我决定做一个实验,测试桤木是否像那些政策所认为的那样,是真正的松树杀手,还是说桤木可以利用氮素改善土壤,促进松树的生长。
我猜是后者。
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比我想象的更有先见之明。我知道, 我对自由生长政策的深入研究可能会激怒政策制定者。我只是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大的反应。
作者简介
苏珊娜·西马德(Suzanne Simard),森林生态学家,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林学系教授,美国生态学会、美国国家生态分析和综合中心成员。她关于“树维网”的开创性工作曾登上《自然》封面。《纽约客》《环球邮报》《泰晤士报》等媒体都刊登过对她的研究工作的报道,她还多次应邀进行TED演讲、拍摄纪录片等。
前往“返朴”公众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此书。
特 别 提 示
1. 进入『返朴』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精品专栏“,可查阅不同主题系列科普文章。
2. 『返朴』提供按月检索文章功能。关注公众号,回复四位数组成的年份 月份,如“1903”,可获取2019年3月的文章索引,以此类推。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摘编。转载授权请在「返朴」微信公众号内联系后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