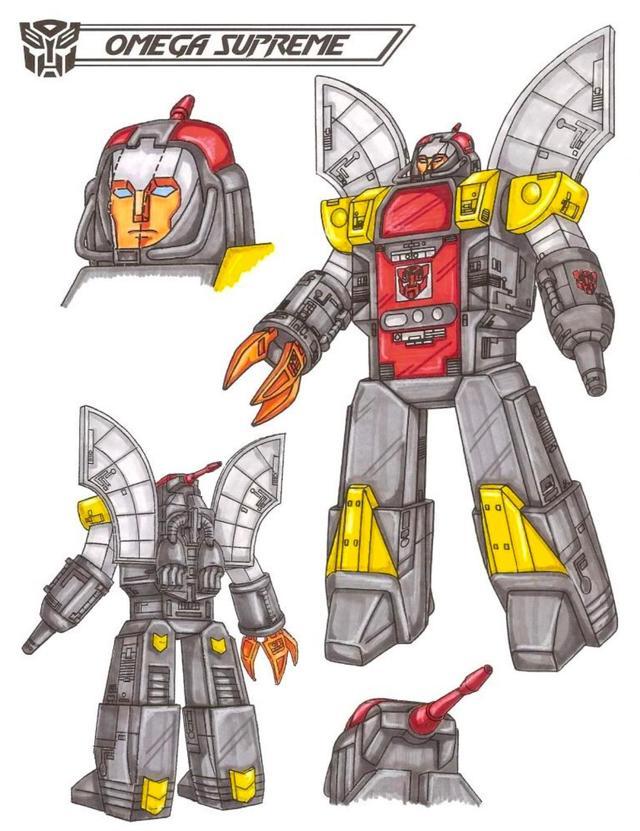《伤寒杂病论》对量的把握

量,指的就是程度的轻重,影响的大小。夫脉当取太过不及,非独脉也,余皆仿此,太过不及总从“病”看,其实“病”也是对比出来的,是用常人、平人的状态来做对比,才会有病人、病态,健康→亚健康→病,都是用程度来区分。说发热了,也是区别于正常体温,恒温动物体温高于平常了,就发热了。这方面容易看出来。但说脉浮了,多少才算浮,浮到什么程度,这是量的问题。诊脉说肥人责浮,瘦人责沉,也是从常态来做对比。病的程度,一般是从四诊得来的大致“数据”为准。中医不去计算详细的数值,但量上有区别,轻重不一的病不可能用一样剂量的药,都是一种模糊控制。影响量的因素有许多,诊断上以病情的轻重,正邪双方的强弱为主,治疗上以干预量为主。影响量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体重、胖瘦、生活工作环境、饮食、形志苦乐、天气原因等。因为影响因素众多,难以准确把握,所以说量是中医的不传之秘。关于量的问题,前几年写过一段内容,这里可能有重复。见另一篇《读伤寒杂病论随想》。
与量有关的内容,是最复杂的内容,诊断时也许对表现出来的性质容易判断,但对表现出来的性质多少则难以把握,比如恶寒的:微恶寒、恶寒、寒战,程度就有区别。比如痛:时微痛、微痛、时痛、烦痛、掣痛、绞痛、冒昧不知痛处、痛不可近、痛如被杖、按之痛、痛而按之不痛等等。程度上的区别和把握,往往与经验有关,也和诊断的细致与粗略有直接关系,仲景在自序中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能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治疗时对量的把握,对医者是一个考验。比如针灸,取穴多少,针入多少,针时多久,都有量的区别。《灵枢·官针》篇说:“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失针之宜。大者泻,小者不移。” 刺之深浅,灸之壮数,均需详审。
用药也是同样道理,病情轻重不同,药量也要与其相宜,老年人五脏皆衰,汗吐下法会重伤正气。小儿轻灵娇嫩,体质易变,应春气之生发,用药讲究短平快。小青龙加石膏汤条后有“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妇人有经、带、胎、产,诊治则必须考虑到相关的问题,前面说的“阳病十八”“阴病十八”还不包括“妇人三十六病”,原因就是妇女有其特殊性。人的体重大小,与药量相关性也比较大,两个年龄一样的人,一个40公斤体重的,用药不可能与重80公斤的相同。“强人”“羸者”当区别用药。前面说过诊脉时肥人责浮瘦人责沉,还经常说胖人多痰,瘦人多火,所以胖瘦对诊治的影响也相当大。《灵枢·口问篇》中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体质的形成,病的出现,与环境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也是不得不考虑的,生活环境和习惯的不同,会导致人身体出现不同的偏差,用药则要顾及到可能的偏差。“酒客不喜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尊荣人,骨弱肌肤盛”“强人”“瘦人”“素盛今瘦”都与这些因素的长期作用有关。形志苦乐,与病的发生和变化关系也相当密切。天气原因相关性就更大,无论诊断还是治疗,都得考虑天气因素,生理上,“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诊脉有春弦秋浮,冬沉夏洪的区别。这里单说用药,比如发汗方,天寒地冻用发汗药,则需要加大剂量,还需要温服或者能耐受时热饮,同时还要温覆促汗,不然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桂枝汤服后还需要“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病情的轻重,对量的影响最为直接,“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太阳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栝蒌桂枝汤主之。”都是太阳病,都有头项强痛,但病从单纯的头项强痛,到痉病的身体强几几,程度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药随证变,方随法出,故用不同的方法治疗。“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失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类似病情,不同的程度,方药的选择和运用,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药量的多少,还与用法有关,同样的方药,用法不同,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桂枝汤方后,有详细的记载:“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这种依据药后病情的变化观察而调整剂量,也是临床必不可少的。急救用药,不这样用,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是考虑多用则反生它变。得吐止后服,得下止后服,则是吐下类药的一个用药法则。刺激太大的药,例如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则分为五服。而病特殊又不能这样服用的,比如黄连汤,则采用昼三夜二的方法,或者还可以改为少量频服,才不致一次服用量过多而吐掉,又能让药力接续。小儿用药也多采用这种方法。除了汤剂,其它剂型的选择,也与量有关,同样是综合考虑而采用的恰当方式。
说到量,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剂量,关于剂量有很多种说法,前面链接里有所表述,这里不再赘述,但要提醒的一点,就是药材的质量,会严重影响药方中使用的剂量,过去用的中药,与现在所用的可能品质完全不同。过去的药材虽然品种和产地的影响大,但同一产地的同品种药材质量相对稳定,现今的药材则不然。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多,就不过多讨论了。
量,做为一个程度和数量,是分析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不可少的环节。用药如用兵,《孙子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一个合适的,恰到好处的量,是治疗时精确控制的前提,量虽然“不传”,但必须面对,并尽量接近最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