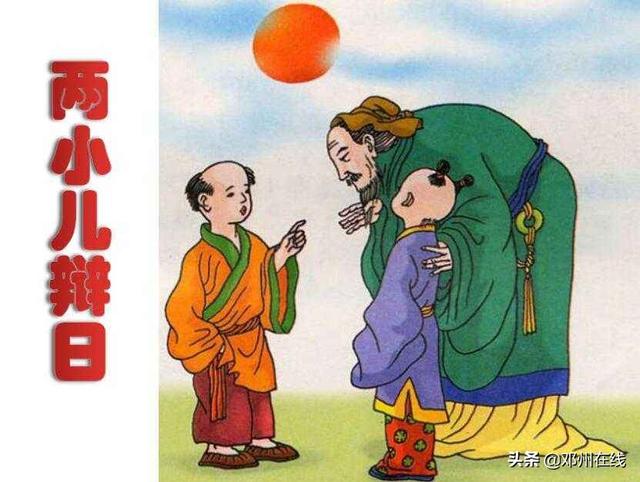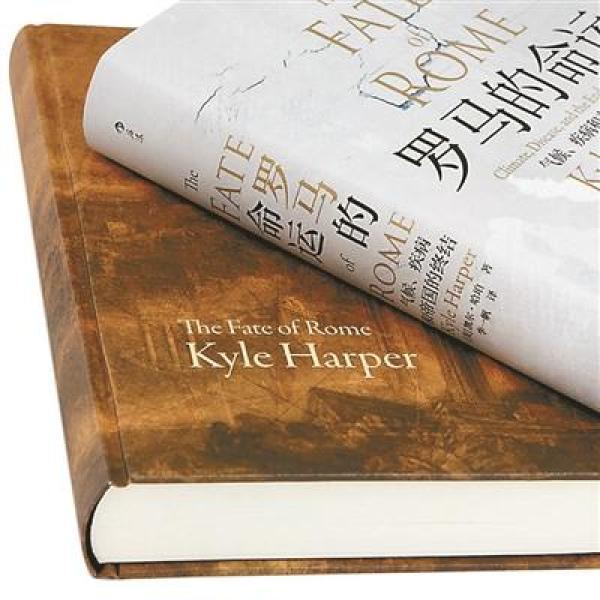


这是一个伟大文明与隐形敌人长期斗争的故事。在公元160年的帝国全盛时期,由著名的罗马大道和繁华的港口连接起来的辉煌城市,正等待着来自非洲中部致命的病原体。然而,在变幻莫测的太阳光芒下,在时而被火山尘埃遮住的天空下,或者缺少雨水的天空下,帝国依然顽强地坚持着。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新书《罗马的命运》论述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章节之一: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第一本研究气候变化和传染病在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所起作用的著作,叙述了自然战胜人类野心的故事。
受感染的老鼠一旦登陆,罗马的运输网络就会加速疾病的扩散。大大小小的马车载着偷渡的老鼠沿罗马道路行进。麦考密克已经证明了河流的重要性,它们是6世纪时瘟疫在高卢传播的有效渠道。但是,鼠疫杆菌的传播也可以与人类毫无关系,因此让人难以捉摸。它能到达任何老鼠所到之地。普罗柯比曾提到,瘟疫在每个地方都燃烧得很缓慢。它“总是以固定的时间间隔移动和前进。像是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动:它在每个地方会持续一段固定的时间,刚好足以确保没有人能忽视它的存在,然后从这一点开始向不同方向扩散,到达人类世界的所有尽头,就好像担心地球上有哪个隐蔽的角落能逃避它的魔掌。它没有放过任何有人居住的岛屿、洞穴或山顶”。疾病深入到了古代乡村最隐秘的地方。
病菌扩散的速度与背后的动物流行病进展有复杂的关联。在所到之处,鼠疫杆菌首先会在大鼠聚居地里扩散。随着大鼠数量减少,跳蚤会迫切地寻找血液。据研究黑死病的历史学家奥利·贝内迪克托估计,这个周期平均为两个星期。然后,饥饿的跳蚤不再挑食,从而转向人类。于是,人类瘟疫就此开始。在马赛的一次鼠疫暴发中,高卢主教图尔的格列高利记录了一艘来自西班牙的瘟疫船的到来,这艘船立刻夺走了一家8口人的性命。这之后是短暂的平静期,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动物流行病的定时炸弹在倒计时,接着瘟疫就暴发了。“就像被点燃的麦地一样,瘟疫的火焰在城市里熊熊燃烧。”两个月后,瘟疫自行熄灭了,可能是夏季气温上升所致。人们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便返回城市。然而,瘟疫却再次暴发。
穷人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啮齿动物密切接触。在中世纪的黑死病中,穷人最先倒下,但最终富人也无法幸免。在查士丁尼瘟疫中,疾病首先“急切地攻击躺在街上的穷人”。然而最终,大屠杀没有放过任何人。它降临在“大大小小美丽、令人向往的房子里,这些宅邸突然变成了屋主的坟墓,仆人和主人同时倒地而死,腐烂的身躯混杂在一起”。“人们生活的地点、方式、性格、职业,以及许多方面都各有不同,但是遇到这种疾病的时候,这些因素没能产生哪怕是最微弱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只发生在这一种疾病身上。”
鼠疫不可避免地从亚历山大里亚传播出去。如果谷物贸易是帝国流通的血液,那亚历山大里亚就是它搏动的心脏。亚历山大里亚出现瘟疫的消息漂洋过海,激起了各种末日预言。在瘟疫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人们就已经产生了恐惧。“来自四面八方的传闻在这里流传了一两年之后,瘟疫才抵达这座城市。”看起来,有可能是一艘政府船只冒着冬季的暴风雨,为首都带来紧急的消息。瘟疫于542年2月下旬到达君士坦丁堡。整个瘟疫留存下来的最早记录,刚好就是查士丁尼颁布的一项法令,因为银行家协会需要帮助,以便解决大规模死亡事件中的债务问题。“死亡的危险已经渗透到每个地方,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听别人讲述他的经历……发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事,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是542年3月1日。更糟的还在后面。
瘟疫第一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时,持续了四个月。普罗柯比和约翰都在现场。他们来自不同的精神世界,但他们的证词却惊人地相似。第一批受害者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死亡人数开始上升。“起初,只有少数几例死亡超过了正常死亡率,但随后死亡人数一路上升,达到每天5000人,然后是1万人,甚至更多。”约翰的每日统计与之相似。每天的死亡人数最高达到5000,然后是7000、1.2万、1.6万。一开始,表面上人们还能维持公共秩序。“人们站在港口、十字路口和城门口清点死者。”根据约翰的说法,可怕的死亡统计一直累积到23万。“在那之后,人们只是把尸体抬走,不再统计了。”据约翰估算,死亡总数超过了30万人。这座城市在灾难前夕大约有50万人口,那么25万至30万的死亡人数,完全符合暴发黑死病地区的死亡率的最审慎的估计,即50%至60%之间。
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然后彻底坍塌。所有工作都停止了。零售市场被迫关闭,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奇怪的食物短缺。“在一个货物充足的城市里,一场真正的饥荒正在弥漫。”“整个城市陷入停顿,好像它已经死去,所以食物供应也跟着停止……食品从市场上消失了。”钱也没有用。恐惧笼罩着街道。“每个人出门时都会在脖子上或胳膊上挂上标签,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皇宫也在劫难逃。从前庞大的侍从队伍如今只剩下几个仆人。查士丁尼自己也染上了瘟疫。他很幸运,成了从感染中幸存的那五分之一患者的一员。国家机构也逐渐消失殆尽。“一切经历可以总结为:(在君士坦丁堡)再也见不到任何人穿着短斗篷”,短斗篷是代表帝国秩序的人所穿的鲜明服装。
城市里很快就堆满了尸体。一开始,埋葬死者的工作由家属坚持来完成。后来,这就像试图在泥石流中站稳脚跟一样。“混乱开始用各种方式统治一切地方。”庄严的仪式还有基本的环境控制都消失了。皇帝连想要清除街上的尸体都很困难。普罗柯比和约翰都讲述过一个细节,查士丁尼曾任命他的私人牧师狄奥多罗斯来负责组织应急工作。人们在城市周围的田野里挖了许多深坑,但很快就被填满了。于是又用油布把死者拖到岸边,放到船上运到海峡另一边。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述,位于赛凯的军事塔楼里“杂乱地堆满”尸体。约翰的描述更加形象:死者层层交叉堆叠,就像“草垛里的干草”一样。死者“被踩踏而过,就像被踩坏的葡萄……约翰真切地认为,他看到的就是“上帝烈怒的大榨酒池”,这是末日的征兆。
这些关于君士坦丁堡疫情的生动的感官记录,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寂静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线索提供者坚持认为,大瘟疫吞没了“整个世界”。它横扫了罗马帝国以及更远的地区,包括波斯人和“其他野蛮人”。它席卷了整个东部,包括“库什”和阿拉伯半岛南部;还蔓延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其他编年史向我们证明,鼠疫曾到达多瑙河诸省、意大利、北非、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群岛。尽管这些记录非常简陋,与色块图像相差无几,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它们。
(节选自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新书《罗马的命运》,2019年6月出版)
关于中美贸易战,这些消息都是假的!搜“中国网”抖音号(787874450),看你想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