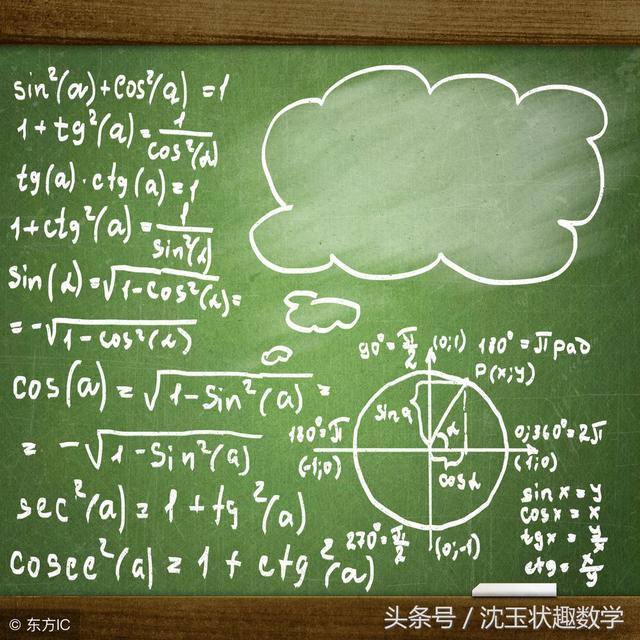原创 锅鱼滑 于华看社会
作为长期研究农村、农民的学者,在陕北农村做田野调查断断续续超过15年时间。从开始的听不懂方言到逐渐能听懂大半,再到能和村民顺畅地“拉话话”,慢慢喜欢上陕北话,而且发现其中不少有趣之处。我不是语言学家,无法做学术性探究,只把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陕北话做简单记述。
从事人类学田野工作,初到一地,最先遇到的总是语言交流上的困境,学好方言,成为研究者的第一门课。

(陕北骥村)

通常一种地方话中最容易引起注意的是那些骂人话(想起一些学外语的朋友常常从学骂人话开始,大概因为文化其实就在凡人琐事、人际关系当中)。此处为语言文明之故,不选取村民常说的那些Fxxk级别的脏话。
骂人的话
盖佬,意指被“戴绿帽子”者;我觉得这里的盖是指乌龟的盖,有缩头乌龟的意思;
黑皮(发音hepi),指流氓匪类,遇到不讲道理之人就说你个“黑皮”;
野鬼,应为本义,孤魂野鬼,无人祭奠的死者;骂人野鬼是指没教养缺管束之人;
混种子,这个好理解,杂种之意;
瓷脑,常用以形容一个人笨头笨脑、头脑不灵光;
儿,形容不懂事,不通人情,说某某人“可儿了”就是指其横行霸道不讲理;
八成,意为头脑不精明,糊涂,“半吊子”;
怂,在陕北话和关中话里都常用,如哈怂(坏、淘气),呆怂(呆傻),瓜怂(笨蛋)
草鸡,胆怯、害怕、认怂;
那入的(近乎英文rude发音),就是那驴日的(吞音了);这是个地道的骂人话,但现实中却常常并不带有骂人意思地使用,比如一村妇说到自己儿子:“那入的不晓得哪去(ke)了”。
文雅古语
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骂人多是下里巴人—村民村妇所用。在通行普通话的城市人心目中,方言即为土语,属于鄙、俗范围。但实际上,稍加注意,会发现陕北话中许多不同于普通话、不太好懂的言词竟多沿自文雅古语。查找与方言对照的文字时,经常在《辞海》中都找不到,得到《词源》中去寻。试举几例:
星星,叫“星宿”(发音xingxiu);满天星星,说“星宿赶稠”;
乡亲,叫“乡党”;
完成,说“毕”,吃完了说“吃毕了“;
可怜,叫“凄惶“;
打算,叫“谋虑”;
闭嘴,说“悄声”;
现在,叫“迩刻”;
不懂,叫“解不下”(发音haibuha)
拿,叫“荷”;
说话,叫“言传”;
头,叫“首”;外头叫“外首”;
高粱,叫“䄻黍”;
牲口,叫“牲灵”;
公羊,叫“羯羝”;
还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我们不禁会想,方言土吗?村语俗吗?所谓文野之分、雅俗之别是不是正好颠倒过来了?无独有偶,在陕北做田野调查三年后,当我能用当地语言和村民、村妇拉话时,他们一致称赞到:“郭老师,你现在说话不糙了”。哈,原来我的普通话和不够地道的陕北话在村民眼中才是“糙”的、“土”的。由此可见,和自己母语不同的说话方式才是“土”、“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生动传神
任何一地方言都是当地生活世界的表达,最能体现地方文化的特点。骥村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峁梁沟谷交织,山地贫瘠苍凉。这里的人们说话声音沉厚,后鼻音较重;而在黄土高坡上唱起信天游来,都是吼出来的,与黄土一般厚重。陕北方言的表达很有陕北人的性格,音色浑厚,直抒胸臆,直达现实。
父亲称作“大”,自是一家之主,家中老大;
叔叔叫“二大”;
爷爷称Yaya;
奶奶称Niania;
未婚女孩叫“女子”(重音在女字上);
已婚女性叫“婆姨”;
生病说“难活”;
漂亮叫“拴正”;
排挤叫“刻薄”;
大哭说“嚎起”;
节俭叫“细份”;
好友叫“拜石”;
不新鲜叫“死蔫”;
全部叫“一满”;
窑顶叫“脑畔”;
智障叫“憨憨”;
口吃叫“结卡”;
帮忙叫“相伙”,
热闹叫“红火”,
打架叫“鏖战”、“斗阵”;
陕北话常用叠音词,特别生动传神,比如:红个彤彤;蓝个莹莹;绿个茵茵;白个生生;笑个盈盈;新个崭崭;苗个条条;……形容女子漂亮说“俊个蛋蛋”;说某人身材矮胖,就说“猴胖个蛋蛋”。形人状物,堪称形神毕肖、活灵活现。

(坡地)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初到一地,遇到语言交流的障碍几乎是必然的,闹出尴尬也不奇怪。记得一次和同事正在村(骥村)里转悠,听闻村里的老会计(六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我们最重要的资料提供人)病了,于是赶紧“杠”(gone)到他家里。一进门,只见五十多岁的汉子捂着胃部疼得哭爹喊娘。我们赶紧拿出胃药和止痛药给他吃下;村里的“赤脚医生”正为其拔罐止痛,也不见效用。我和同事都感觉不可耽搁,应该赶快送医院。县医院距离村庄约20公里,当时村里只有一辆私人小面包车每天一次往返县城拉客。情急之下,同事说:“赶紧叫车送医院”,村民说:叫车找“要钱儿”嘛。同事气急道:“要钱儿给他钱嘛!”然后才发现,开私人小面包车的老板名字就叫个“要钱儿”(或者摇钱)。
幸亏误会解除,及时把老会计送到县医院。我们凑了几千块钱,并找县里亲朋帮忙,当晚做了手术——胃穿孔,很危险,切除了四分之三,总算抢救及时,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在骥村,白天做了访谈,晚上在房东家窑洞里将磁带语音整理成文字录入电脑。听录音时有一个词(音)“之拐—”,怎么也听不明白,结合上下文反复听还是不明其义。于是把房东大哥叫来询问:“之拐”是什么意思?他回答:“之拐就是之拐嘛”。再问:到底是什么啊?大哥急得抓耳挠腮,连比划带说:“就是之拐嘛!之拐嘛”!后来把嫂子也叫来了,最终才弄明白:是“这个—”,没有实义的口语词。所有人大笑而散。
事后我想,这个“之拐”应该不是当地方言,因其不是村民的表达习惯;而像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官方话语的渗透结果——村民在几十年开会、听报告、听讲话中习得了这个口语表达方式。(纯属逻辑推测,抑或许不是这样,欢迎指正)

(房东大哥,已故,怀念他)

(寨子上)
一地方言适合一地风土人情,最能表达出本乡本土文化本质的精髓。故而,在提倡、推广普通话时也需要给方言包括民族语言保留空间。毕竟,百花齐放才是春。对语言文化的态度,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可见多样为美,多样才美;而“大同”并非大一统,是多元共存,是和而不同。回望秦川大地,大一统的秦制建立,即使做到了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也没能把南腔北调的方言给统一了。否则,我们今天说的恐怕就不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而是秦腔秦调的陕西话了。

(村里最后一位扎白羊肚手巾的老汉)
语言之事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思维的材料,语言与作为精神活动的思考有着相互依存和共荣共损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根本方式,人如何使用语言,就会如何思考”。已往的专制暴君和独裁者想要控制人们的思想,往往会控制他们的表达,囚禁了语言,思想便被禁锢。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专门分析了语言与思考的关系。他指出,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而控制思想的办法之一就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
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还具有建构的力量。因此,控制了语言就意味着控制了思想,进而控制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大洋国中“新话的技术”就是控制语言并最终消灭语言的技术。对旧的词汇成批、成批地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一些用来表达复杂丰富情感或思想的形容词和副词被取消了,即使不能取消,词义也变得简单明确。这种消灭使词汇由词意的复杂和微妙转为趋于简单(和粗鄙)。
同时进行的还有《新话词典》的编纂,新词的创造是为了减少含义中的联想成分,直接达到其有限的目的。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大洋国不仅每年编纂新话词典,用新话来发表社论,而且用新话来改写莎士比亚、拜伦等历史上的文学家的作品,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写历史。
大洋国的双重思想,也是通过特定语言表达的。例如这样的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所谓双重思想就是思想中同时包含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通过语言的“辩证法”容忍矛盾,使人们有意说谎,但又真的相信这种谎言,相信被告知的谎言是真实的,使之成为一种诚实的自我欺骗,从而达到控制者所希望的思想定向。
不知怎么说方言说到奥威尔这来了。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并非只存在于寓言中。
2022年1月20日岁在大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