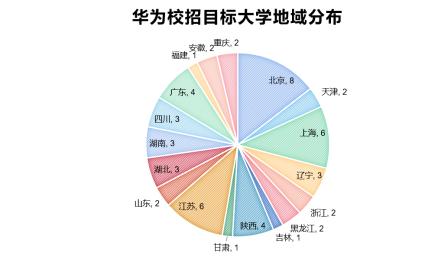爱心不能断,对色已消魂。
水从骨内出,火自眼中腾。
心雄胆已泼,业重障还深。
1
对于性的问题,佛教的回答多数都是暧昧的。
倒不是佛陀没有对此问题进行过清晰的揭示,
而是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
很多东西需要修正处理才可通行。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莲华色比丘尼受苦报出家的故事,
在汉文佛典里,独删去了“与其女共嫁其子”一报。
即便兼容并包如中国文化者,
对于这样的情节也是很难接受的。
正像陈寅恪先生说的,
“吾民族同化之力可谓大矣”,
“独至男女性交诸要义,
“则此土自来佛教著述,
“大抵噤默不置一语。”
儒家君臣父子的观念,
都可让佛教同化并接受,
独是这一问题,
僧俗两界都能到了高度的默契。
正是在儒释夹攻的社会现实中,
才会出现宝玉云雨神仙授技,
宝玉黛玉偷读《西厢记》,
才会“设男女之大防”,
以备“男女授受不清”。
生存于夹缝中的古代人,
如何获取性教育的知识?
佛教在其中是否也出了一份力?
想必这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
今天就来掰扯掰扯这个问题!

2
民国时期曾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扫黄案,
1924年,张辉瓒兼任湖南省警察厅长,
张信奉“万恶淫为首”的封建伦理教条。
于是在其上任的时候,
就打着“维持风化”的名义,
斩了长沙城著名的“调台”刘麻子。
这件事被《大公报》报道和渲染后,
闹得轰动全国。
如此重大的事情,
自然是请示了领导的。
当时的湖南省省长是赵恒惕。
这可是个奇葩兼传奇的人物。
据说为了求雨,
半月多不回公馆。
用当时某君的话说就是,
“不同太太睡觉”。
当时任四川省督办的杨森也要维持风化,
于是把一个犯奸的学生枪毙,以儆效尤!
周作人对这些讲礼教的人口口声声说的“风化”一词,
提出了深刻的批判,
抨击这些野蛮都督的思想,
总不出两性的交涉。
不要觉得这些事和佛教扯不上关系,
若深入了解,你便会发现,
“风化”一词,不仅关乎世运,
实牵动着整段民国史。

3
甘肃省立第三师范的教员高抱诚,
因原配翟氏病故,经校长赵希士介绍,
与该校毕业生张从贞订婚。
不意未及成婚,张从贞便病故了。
张母过意不去,
于是坚决将次女张审琴续配高抱诚。
1923年,高张正式结婚。
高张结婚一事立即引起了以甘肃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汉公等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夫的强烈反对。
他们攻击高张的结合违背“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
还组织成立了一个“纲常名教团”,
对高抱诚大肆谩骂,恶毒攻击。
这件事情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全国闻名。
据说当时还有人将《欲海回狂》寄给高抱诚,令其忏悔!
《欲海回狂》何书也,
竟得到这些卫道夫如此的厚爱?

4
《欲海回狂》是清周安士所撰,
收在《安士全书》第三卷,
书的本意是劝戒淫的。
所以送《欲海回狂》给高抱诚,
大概也就是劝止其淫的意思。
但是这本被作为杀人利器的书,
真的有此威力吗?
未必,周作人就不信。
在他看来,“做戒淫书的人和做淫书的人都多少有点色情狂”。
的论!
周指出该书总劝部分的“遇娇姿于道左,目注千翻。逢丽色于闺帘,肠回百折”就是艳词,
完全可以放进《游仙窟》里去!
佛教戒淫法门之一,有“不净观”。
观想此法门,能起到顿觉男女精血污秽的效果,
是为对治淫关的方便门。
《欲海回狂》讲“欲火动时,勃然难遏,纵刀锯在前,鼎镬随后,犹图侥幸于万一。”
圣人的只言片语也无法消融彼一片淫心。
所以淫心乍发之时,
即便看到了现在的因果
始终还是不能断了爱根。
要断爱跟,唯有“不净”二字。

5
《欲海回狂》的“不净观”,
总结了佛典中关于男女总相、女根垢相、女腹垢相、男躯垢相的内容。
周作人极反对“不净观”,但还是承认其有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不净观”就是古代的性教育。
但是这种性教育与儒家那种藏匿起来或严禁起来的做法不同,
“不净观”走的是“倒路”,反其道而行。
在科学不昌明的时代,
印度人便发明了铲除欲根的特殊“性教育”,
今日看来,不过倒行逆施而已,
但“不净观”毕竟是以生理为本,
总还是值得佩服的。
与“不净观”相对,
周作人认为现代的性教育才是正宗的“净观”。
何谓净观?
他说道:“净观的性教育则是认人生,是认生之一切欲求,使人关于两性的事实有正确的认识,再加以高尚的趣味之修养,庶几可以有效。”
疏导才是正路,
顺遂才是人生。
我们今天对于两性的认识视野肯定更宽阔了,
我们对于周作人所理解的不净观也未必认同。
但是,他将“不净观”看作古代的性教育的想法,
其实对我们有颇多启示和意义。
佛教讲“不邪淫”,不就是周作人所说“净观”吗?
不净观对治邪淫,正如重药治重病。
心有“净观”的人,何必非得吃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