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燕赵新报 杨素梅 燕赵新声 2022-05-19 08:14 发表于河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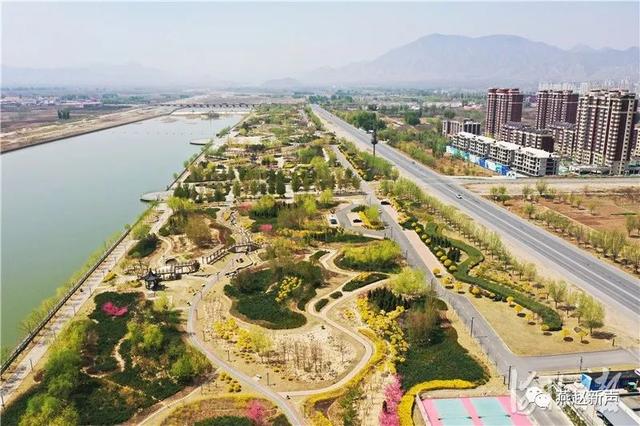


本书作者简介:
霍汉清,男,汉族,1956年1月出生,祖籍涿鹿县武家沟镇溪源村,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经济师职称。1979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供职于涿鹿县石油公司、河北省石油总公司6604管理处和中石化张家口石油分公司,2016年1月退休。
11岁辍学务农,编苇席,育良种,精通农业种植。1987年通过河北省自学考试取得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历。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员,张家口市京畿民间文化研究会、张家口市诗词协会涿鹿分会、涿鹿县民俗文化协会、涿鹿晋剧文化研究会等四个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涿鹿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涿鹿县戏曲界联合会副会长,涿鹿县苇席编织非遗传承人。2020年6月,被中共涿鹿县委、涿鹿县人民政府授予涿鹿县第一批“涿鹿工匠”称号。
参与涿鹿县多部书籍的编写和摄影,《魅力武家沟镇》副主编,著有《溪源记忆》《在溪源村的日子里》《情系中石化》《记忆中的涿鹿城》等。






晋剧音乐:孙红丽 - 晋剧精选唱段合集

【晋剧】《汾河流水哗哗啦》音乐:王爱爱 - 记忆的符号

精神世界的灿烂之光
杨素梅(中国涿鹿)
后人不止在前人栽的树下乘凉,还会对前人的一生品评总结。霍汉清先生著的《山西梆子在涿鹿》上下册,就是对这方土地上曾经流行的晋剧事业的收集整理。是一本本土晋剧志,一种文化的高度。读了这套书,对涿鹿以往岁月的精神文明建设造诣有了全面的了解,产生一份感动。这套书内容丰富,讲述简洁,有大量的彩色图片,印刷精美,值得收藏。
一


读完这部书,就似穿越了唱山西梆子岁月那起伏兴沦的全部历程,目赌了涿鹿这方人中老一辈们精神世界的喜怒哀乐。作者用全部心血精心收集整理编著出的近四十万字,大量的相关照片,蕴含了这方山水间昔日今朝的山西梆子班社组织,所有名角与演员、鼓师、琴师们以及戏台、戏装,民间百姓对这种戏剧的热爱程度,展示出一幅三、四十年代民俗祭祀娱神的巨幅画卷,传统文化的诗史般赞美颂扬。其实这就是一部涿鹿晋剧史,一部当地人精神世界的理想追求写真,山西梆子对人世民心的陶冶洗礼,60岁以上几代人对戏剧塑造人的刻骨铭心的挚爱。
山西梆子陪伴着他们走过人生的几十年,听着戏唱着戏谈着戏叹息着戏,浸润在戏的习习春风温柔雨露中,他们觉的活的很快乐很满足很惬意。戏的粉墨脸谱与五彩装饰,缤纷了他们苍白的岁月;戏的婉转悠扬与吼啸叹息般的唱腔,撞碎了他们的苦闷日子;戏的再现前人生存状态,越发倔强着他们的善良品行。山西梆子,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们活着的理由,是他们幸福的源泉,是他们苦中寻乐的一点甘甜。戏的道德教化引领作用,是他们离不开的启蒙形式,规矩约束自己与家人的重要方面。苦了难了吼几声熟悉的梆子,立即消烦去恼,心旷神怡。
涿鹿老辈人集体爱山西梆子,人人是戏迷,个个是票友。兴办过多少戏班剧团,出色过多少县级村级名角,村民筹资建起过多少戏台,会唱多少本大戏,书中都做了详细记载。这里搭起的演出平台,吸引来四外大批追随者,群星们从四面八方来此登台亮相,硬是把涿鹿唱成了“戏窝子”。“山西人要在河北出名,先要在张家口唱红,要在张家口出名,先要在涿鹿唱红。”涿鹿人看的戏多,名角儿多,唱戏懂戏的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涿鹿山西梆子形成一座后人无法超越的文化高峰。县剧团、民间戏班丛丛簇簇地四处冒出来,你方唱罢我登场,锣鼓声此起彼伏,处处闪耀着精神之光,让这方人感到无比自豪。蔡有山是传奇,三毛旦是精彩,在他们身后,山西梆子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二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切的古老戏剧形式都会与古礼教旧传统一样,必然会受到政治冲击,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挫折、毁坏、批判,这是绕不过的历史曲折发展规律,跳不出的文明与愚昧轮番上演的社会动荡。劲暴的山西梆子随着文化革命渐渐黯然失色,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奋起,怎么也抵不住从演员到服装剧本及舞台的整体重撞残损,已经成为过往成为文化遗产,成为曾经的辉煌。随着那一代人的离逝或老病,已到了即将消失的最后阶段,到了急需整理抢救然后封存的阶段。多少人为此忧心忡忡,千方百计要重振再兴晋剧。
人生不能重来,历史不会重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挡不住的时过境迁,不间断地移风易俗,一切都在不知觉中脱胎换骨地蜕变。霍汉清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了老一辈名角儿们带着遗憾一一下世,文武场的演职员们四散漂零,山西梆子的大旗撕扯的支离破碎。全县百姓集体心痛一部部手抄剧本的散失,懊恼一座座精美古戏台的残破倒塌,金贵古戏装的一件件被焚或不知去向,山西梆子——涿鹿人最爱的声音,一点点无奈地退缩着远去。
已近古稀之年的霍汉清先生,作为一个涿鹿学者,一个挚爱家乡的过来人,一个追随了戏曲几十年的人,他再也坐不住了,勇敢地挺身而出,立志要抢救这份文化遗产,整理这份民族精华,把涿鹿晋剧史写出来。凡志书必定时间准确,人物真实,不虚构不作假,他明知这是件苦差事,就是要做这件为涿鹿山西梆子建档存文的工作。这是他的自觉自愿,是涿鹿人的一种大境界大胸襟。于是,他不辞辛苦,到山西、内蒙、怀来采访,仅张家口就去了30多次,宣化12次,寻找名角后人搜集资料,做了大量笔记。了解情况,记录书写,为在世的和已逝的角儿们,鼓师琴师们箱师们做传,为曾经的古戏台留影拍照,为扶持这项事业的领导们著文纪念。通过一年时间的努力,这本书问世了,最大限度地打捞书写了所有人物与事件,尽量详尽地记录下那段唱山西梆子的岁月,添补了涿鹿戏曲事业的空白,是涿鹿一件值得赞颂的千秋功德。
晋剧如此地被涿鹿人民挚爱,被世代口耳相传,被不断地推崇发展,除了其精神世界的塑造引领,还在于其的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及其故事性、历史性,在于其传播了真善美的道德品性,鞭挞假恶丑的操守言行。一部戏就是一个历史故事,一个人的成败荣辱过程,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兴亡衰落启迪。戏讲的是人生哲理智慧,传承的是正确的生存方式,是后人慕仿学习的范例,是一次次寓教于乐的集体学习进步。戏曲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滋养着人类心志灵魂越来越文明高贵。所以,可以说有戏在演的地方是要求进步文明的一群人,有戏可观赏品评的一群人必然具备不同与众的眼光视界。山西梆子辉煌的岁月,正是涿鹿人民物质精神双飞跃的最好时期,是这方人“安其居,乐其俗”上下同欲的理想太平盛世。
三

那时,除了山西梆子,大江南北都有自己的戏曲剧种,百姓都为戏剧狂欢。那么戏是什么?是怎么起源的?客观地说,戏剧这种精神世界的表现形式与物质社会一起诞生,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笨拙到精细,一步步发展起来,任何事物都脱不开这个“一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霍先生在书中提出涿鹿人持守的观点,认为戏起源于涿鹿大战后的角抵“蚩尤戏”,当地有人认为晋剧起源于秧歌角(一说是铰,一种乐器),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辞海》解说:戏,角力,比赛体力的强弱。晋剧:中路梆子,也叫山西梆子,戏曲的一种。由蒲州梆子演变而成。一说系祁太秧歌,汾孝秧歌吸收蒲剧艺术发展而成。秧歌:插秧后或丰收后农闲时光的娱乐形式。《中国文学史》记:“唐以前的戏剧还处于萌芽状态,各方面还不成熟,只能算具备一些戏剧的因素而已。到了宋代,戏曲才随着其他市民艺术空前发展起来。”外国的戏专指话剧,中国宋代的戏分三类,一类是歌舞讲唱,如转踏、曲破、大曲、赚词、鼓子词、诸宫调。一类是与戏剧更接近的傀儡、影戏、杂剧。第三类是已有完备戏剧形式的南戏。然而,那时没有剧本留存下来。元朝为元杂剧。明代有杂剧与传奇《宝剑记》《鸣凤记》《浣沙记》。晋剧、越剧、豫剧、秦腔等所有剧种,就是在以上各种形式的基础上,用地方方言吐字唱词,最终形成各自的地方特色,改造演变而来。戏的最早形式是角抵,晋剧的前身是农闲时的秧歌,至今民间还有人称晋剧是秧歌。秧歌角是其中之一种,是晋剧的前身。其古老腔调早已失传,不可再觅,只能做为一种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无论是角抵还是秧歌,戏剧与歌舞,最早都是一种对神灵的膜拜和祭祀,是用形体动作与神勾通,向神倾述。从戏字的造字解,戏字是一个戈加一个戈,即两个人角抵,是为了娱神。这就应证了最早的戏是角抵戏,产生于涿鹿,是对华夏第一场战争——涿鹿之战的纪念。同时,也证实了戏台都建在庙宇的对面,特别是龙王庙和泰山庙。戏是唱给神的,起源于舜帝祭拜天地四方的请神台。而神是曾经用生命拯救过百姓,扭转过乾坤的伟大不朽的人物。比如村村有的龙王庙供奉的龙王就是轩辕黄帝的儿子们,应龙是他们的代表。三官庙供奉天、地、水三官是尧、舜、禹,泰山庙的泰山奶奶是轩辕黄帝的孙女,火神祝融是炎帝的后人,最早的药神是神农炎帝与轩辕黄帝及歧伯们……后人怀念他们,为他们塑彩像摆供品,代代跪拜祭祀。在他们生辰日,为他们唱颂赞歌诗文,畅述天下人对他们的无限缅怀与精神依赖。这种形式不断地增益添加,开始在脸上涂色,身上披挂,敲锣打鼓弹琴拉弦吹唢呐,戏剧、庙殿与戏台是紧密相依的共同体,是天下百姓对社会进程中产生的英雄圣贤们的念想,是轩辕黄帝倡导的孝、慈、义、信、言、忠、恭、勇、义九种美德的传承。
对这些美德的需要、渴望、期盼,就是戏剧产生的肥沃土壤,也是山西梆子及各种戏剧能够如此普及深入的起因。这方从山西大槐树下迁徙来的人爱晋剧,他们带来了故乡的土洒在新居住处,带来了故乡的树插在村头屋后,他们也带来了故乡的戏剧,这乡音让他们远离故地的惆怅情绪,那份肝肠寸断的思念减轻了许多。这是山西梆子前身秧歌剧在桑干河下游两岸村屯堡营风行半个多世纪的缘由。
四


晋剧诞生二百多年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传入涿鹿,涿鹿人对晋剧的喜爱似众星捧月,民间出现了蔡有山办的剧团,从女人不能演戏,到涌现出赵科甲、崔德旺、刘仙梅、牛雪征,及现在的席正德、陈东山等一个又一个杰出的名角,村镇里涌现一大批会唱戏的人,他们被观众称为“马武黑”“九岁红”“扳头红”“河北红”……他们从村里唱到城里唱到市里,有他们演出时一定会万头攒动。书中记载,一次蔡有山在沽源演出《打龙袍》观众达八千人之多,挤坏了卖票处的栅栏。蔡有山不只是涿鹿头牌名角,也是张家口的名片,在晋冀蒙有不小的影响。
他们之所以成为名角,就是因为他们下的功夫比别人大,吃的苦比别人多。他们大多没有文化,全凭死记硬背,他们拜师学艺,他们偷学苦练,取人之长,精雕细琢,永不满足,渐渐形成特色。超越别人的帽翅功、稍子功都是在别人睡觉时练出来的。蔡有山轻吐字,慢拖腔;彦章里的拖腕婉转、浑厚有力;三毛旦的诙谐幽默,成为民间的永远记忆。他们认认真真唱戏,一丝不苟地演出,个个有专攻,人人是戏包,不仅自己的戏烂熟于心,连过门腔、家伙点儿也把控在心,别人的戏也全部记在肚里。不论台下人多人少,都绝不含糊,一扳一眼地唱,不偷懒不惜力。观众对他们准确到位的表演,给予高度的评价与赞美,特别对于他们对戏对观众的恭敬态度啧啧称颂。就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出色出彩,涿鹿山西梆子越唱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成为当地的文化亮点,外地来客,主人必要请他们看一场蔡有山、刘仙梅、郝金锐、崔德才、袁西琴的戏。那时涿鹿县拿的出手的是山西梆子,是他们的名角们。
他们爱戏,他们更爱他们塑造的人物,爱大仁大义的三国刘关张,爱忠君为国的杨家将,爱铁骨铮铮的梁山好汉,爱公正廉明的清官包拯、况钟、海瑞,拥戴礼贤下士的唐代宗,尊崇从严教子的郭子仪们。一部《打金枝》唱了几百年,包拯惩治陈世美的《明公断》,看了还想看。《算粮登殿》相府三姑娘的忠贞影响了一代代女性的人生观。《三娘教子》把人们唱的泪花盈盈。戏中人物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让他们有了戏中人的家国情怀,眼界宽了胸襟广了。以人为镜,以史为勉,是唱戏的看戏的人共同的做人准则。
他们爱戏,村村都有自己的戏台,老台没了建新台,到1983年,涿鹿共有戏台198座,灯光布景齐全。戏台是他们的脸面,要雕梁画柱,刻花彩绘。每建起戏台要轰台、打台、镇台。战国时建村的辛店老戏台,梁头下有木雕牛腿 ,牛腿上大龙缠小龙;柱头做出象头,象头与龙头互绕。大斜阳村戏楼的额坊上有雕花楣子,额坊下雕大雀替,明间雕游龙,暗间雕绣球,山墙上砖刻山花。他们把自己的戏台打扮的玲珑精美,述说着他们对戏剧对文化的深厚造诣与极度的喜爱。古代的戏台从那方面说都具备集古建雕刻美术之大成的意义了。从前各类工艺大师非常敬业,那时的人对公共事业十分用心。
五



他们爱戏,不只百姓爱,政府也爱。那时的县领导深解百姓的述求,了解民情民意。他们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戏班子是他们心中十分重要的一伙人,晋剧的红火热闹让涿鹿名扬晋冀蒙。他们知道,剧团下乡马车拉着戏箱,交通工具不足,演员们要走几十里山路,许多时候车进不了村,就的牲口驮人背,非常艰苦。他们真正在践行领导就是服务的准旨,为戏牵线搭桥,为剧团分忧解难。候丕丞、王纯、傅广和、贾连亮等各级领导在剧团创建、人员调动、资金配置,资料整理方面积极奔走,大力支持,是涿鹿晋剧发展的优越条件。
他们爱戏,除了兴民剧社,涿鹿晋剧团外,民间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戏班,马姚班、赵二务班、培盛班、三顺和等一个个组织,那些富有家国情怀的民间的仁者乡绅出资出场地,吸引来一群群民间的戏剧能人们,盛开出一片片晋剧小花园……再小的村子也要唱戏,山谷中的小村没有几户人家,却有戏班,他们舍得买戏装,哪怕只是一蟒一靠,陈窑子与好地洼两村分一幅箱子。屈庄村的道具自己制做,“屈庄的戏不用问,一人一根檀木棍。”即使简陋,他们依然唱的绕梁三日,震天动地。那时唱戏报酬各家各户齐,村里凑钱买几条烟,有的给些小米。吃饭不用安排,村民自觉往家里拉演员,抢不到的还要哭鼻子。
晋剧的魅力不只在角儿,也在文场的伴奏,三通锣鼓,人心沸腾,戏台下观众掀起波浪般的欢呼。震憾人心的力量与晋剧的唱腔与曲牌有很大关系。马锣、大弦、二弦、三弦、四弦、胡琴、唢呐组成的乐音,或而低沉悲凉或而悠扬穿空,在年节时祭祀时的乡下夜空久久回荡,抚慰着人心。鼓师、琴师甚至箱子师,布景道具师们都是与角儿们一样了不起的人物。往往鼓师就是导演,是剧团的主心骨,保岱的鼓师朱占雄就是团长是导演,他的喜怒都在一双鼓锤上,演砸了他会把鼓锤直接扔到演员身上,眼珠子瞪的似铜铃,演好了他的鼓点敲得震天响,眼睛笑成一条缝。刘义成等就是在这种敲打中成了演啥像啥的角儿,保岱的戏在涿鹿以至张家口都有一席之地。后来茶坊村的陈河班,就是在保岱剧团一班人的基底上组成。
六


那个岁月,哪里唱戏,哪里就像过大年一样地红火热闹繁华,村街干净整洁人们穿戴崭新。三里五村人们拥向哪里,家境好的给老人们套着马车,有骑骡子的,大多都步行,来回走好几里夜路。哪里唱戏,商贩们必带他们花花绿绿的货物集体奔向哪里,在台场外摆摊叫卖。孩子们吃着瓜子,举着糖葫芦,跑着跳着叫着,一派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
在没有电视手机的年代,山西梆子是晋冀蒙一带百姓的一大文明。但是,民间绝不对戏剧轻浮亵渎,有许多的禁忌,以表百姓对唱给神佛的戏的无比谦诚谨慎。据原市文联民俗学者杨畅先生著的《张家口民俗》记载:当新戏台建成时唱首场戏,要先唱打台戏,先把“老朗神(梨园鼻祖)”请出来供在后台。打台戏是一个人单打或两个人对打,两个人称文武灵官,打过后两个人跳下台,再杀公鸡祭台,祭台时全体演职员要在台下跪拜。新建庙宇或为神塑金身后要唱开光戏;商店开市唱开市戏。请雨前唱请雨戏,下雨后唱谢雨戏。还有还愿戏、打炮戏、对台戏、罚戏、上马戏、丧戏、堂会、加官戏、封箱戏。唱戏是一种隆重的民俗画卷,繁富的市井人生再现。
开放与禁忌,自古来就是人类进步发展必须持守的法度与底限。
戏如人生,人生似戏。戏演的是过往岁月的精彩,歌赞的是优秀人物,传扬的是道德操守。老辈人对戏的评价准确朴实,他们说司法处是恶劝人,唱戏是善劝人。戏是活着的理由、欢笑的来源、谈论的主题、生活的色彩,日子的美好。百姓希望他们生存的时代人人懂礼义,知荣辱,识进退,明上下,级人伦,爱老幼,惜万物,近圣贤。自己生存的社会有德有仁有义有礼。这一切靠社会教育,文化引领,戏剧是最深入民心最接地气的一种教化。山西梆子最兴盛的时期,就是涿鹿精神文明最值得赞颂的时期。
现在,山西梆子与京剧等所有传统戏曲一起随着对神佛的不敬而衰落,在文革中受挫折,角儿们被批斗,下放劳动。正在兴起的年轻一代,失去了舞台和师傅们的教导,他们的戏剧天赋被泯灭。此后,虽然零碎顽强地生存,仍然挡不住分化瓦解,即将消失,让喜爱晋剧的人感到莫大的悲哀失落。如今,人们用自己记忆的唱段随时随地组班演出,是一种纪念。民间不甘心这种精神世界的沉寂,近年来涌现出李凤庭的昌鸣晋剧社、赵兰玉的志愿者协会晋剧社、田兴杰的振兴晋剧社、段世明的中老年业余晋剧演出团、刘德辉的晋剧学苑、唐世辅的怡謦戏迷俱乐部、丁桂茂、韩秀英的英姿晋剧社、谷晓云的新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建新的新生峰剧团有限公司以及70多个鼓匠班,把民间爱戏懂戏人再度聚在了一起,在节假日与红白事时,此起彼伏地演出,尽力活跃着、缤纷着、辉耀着这方人的岁月,抒放着一己的情愫。他们希望向过去一样,让山西梆子再度唱响。
七

然而,山西梆子的辉煌岁月不会再来,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懂戏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能静静地看戏赏戏的人都进入暮年。过去那种收费演出的形式已一去不返,曾经的万众看戏的单一娱乐成为过往。随着时代的转换,价值观的改变,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人心渐次从平静变成浮躁,观念从朴实到物质,裸露的歌舞、摇晃的蹦迪、踢腾的街舞,一浪浪从西方涌来,青年们欢呼的声浪波涛般汹涌,商演与追星族们把歌星捧上了天,成为新时期的富豪。即使形式多样,仍然人心苦闷、徬徨、烦恼。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现实脱节,贫富悬殊让他们找不到方向。平和的晋剧再也走不进他们心中,慢节拍的山西梆子不能解决他们的致富梦,任何形式的说教都救不了他们。只有不再用奋斗的老一辈人,闲适下来的老人们才有心情继续聚团说说唱唱,回忆从前缅怀过往。所以,唱戏的是老年人,看戏的也是老年人。老年人与青年严重分化,一条深深的代沟难以跨越。
在娱乐形式百花齐放的崭新岁月,特别是在电子不断换代的时期,影视明星引领着人们尽情玩闹娱乐来提高收视率,年轻人们全部忙着抓钱然后提前消费的价值观转变,满街花花绿绿商品的新时代,古老的山西梆子早已被冷落遗忘,甚至挤到为人终老送行的角隅。这种昔年的正剧,与所有的剧种一样进入了暮年,正在随着老一辈人的消失渐次消失其灿烂光泽。明眼人意识到那些与晋剧一起诞生的戏装、剧本、乐器,都将成为历史,该在档案馆里好好收藏保存了。及早动手做这件事,避免损失太大,是本地文化部门与学者们应该深刻认知的一点,也是他们的天赋职责。社会应该了解老辈人的家国情愁,给他们提供场地,给他们必要的支持。爱戏会唱戏的一代人都到了古稀之年,须发白了,精神不济了,他们心中有一本本的戏文,他们牢牢记着晋剧曲牌,他们会戏中人物的一招一式,这些都将随着他们的一天天老去而消失,成为新的遗憾,这样的遗憾已经太多了。抢救工作,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如果有条件,政府应建一座涿鹿晋剧纪念馆,为名角们留影,整理剧本,留住那一段灿烂的文化时空,保存涿鹿人曾有过的精彩。同时设专门演出场地,供各个新出现的剧社演出,成为一处晋剧文化聚人处,外地来客休闲赏心处,以解老辈人的晋剧情结,成为本地新的文明亮点,涿鹿的精神高度,迷人的特色,对外的窗口。
在涿鹿流行四十多年的山西梆子,是涿鹿历史的一页缤纷,精神世界的灿烂之光,这种文化牢牢地扎进老一辈人的心中,写进悠久的历史。《山西梆子在涿鹿》应做为涿鹿县晋剧史,在县档案局永远保存。
说了这么多,笔者深知自己对那段时空是陌生的,对山西梆子只识一些皮毛,对晋剧风行的岁月知之甚少,只不过谈了自己对人们追捧戏剧的心境,对戏剧热爱的缘由。因为文化永远是人类心灵的补品,是与物质相辅相成的心灵鸡汤,是地方精神文明的高度,物质建树的方向,人类前进的灯塔。《山西梆子在涿鹿》一书,详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那辈人的精神追求,记录了山西梆子的璀璨时期,读了这本书,就如走进了那段时空,了解涿鹿文化的最辉煌时代。
涿鹿人应该感谢本书作者。
(2022年5月13日)




本文作者:杨素梅,笔名青杨,河北涿鹿保岱人。曾任涿鹿县文联中级编辑,《涿鹿县报》主编。大专文化,作家。河北省作协会员。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出版过多部散文集。保岱历史文化研究会负责人研究员。


请关注 燕赵新报 共享美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