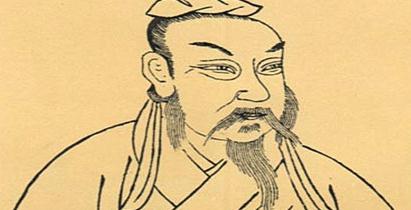导读:
各位书友们好,今天我们正式开始共读《曾国藩家书》。
建议大家在阅读时将前两章(1-81页)进行结合思考,以“修身”和“劝学”作为一个整体“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曾国藩,和他终身所奉行的理念。
这两章的数十封书信里,清晰地记录了曾国藩于“求学”和“律己”之路上落下的每一个切实的印记, 也正是这一步步伏笔,才使得中年之后的他逐步实现了“曾国藩”这个名字后来所代表的全部意义:“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穆彰阿的学生、李鸿章的师傅、“洋务运动之父”、湘军将领......曾文正公。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某种强烈的反差:一个先天资质匮乏的“庸人”与他后天所成就的圣贤、大师的形象之间的原始距离——但解开这个反差的秘密,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意志力极限的故事。
而这种意志力,正是使得生为“凡人”的曾国藩,却最终能够为自己镀上“金身”的原因。
一
有这样一则流传了100多年的轶闻:公元1825年的腊月夜晚,在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一户人家,一个14岁左右的孩子正在夜灯苦读,而此刻,他的房间里潜入了一个意欲行窃的小偷。
这户人家的孩子正在背诵一篇文章,于是小偷就暗暗藏好,准备等这个孩子休息了再出来行窃。
然而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这个孩子来回反复地念了背了多次,竟然都没能完整背诵下来。
小偷在这户人家里等了一整夜,眼看着天色放亮之时,这个孩子还是没有去休息,小偷最后只得在打了无数个哈欠后,悻悻地空手而归。
传闻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参照现在一个初中生背一篇《岳阳楼记》的时间来看,这个孩子的天资绝对谈不上是天赋异禀,甚至可以说是天资有限。
这种先天条件的有限还体现在,孩子的父亲一生考了17次秀才,直到43岁才勉强考过;兄弟5人里面,虽然也都是寒窗苦读,但无一人中举。
而这个孩子自己,从14岁开始参加县试,先后考了9年、7次,23岁才终于考上了秀才。
20多岁考上秀才是个什么概念?
对比同时代的其他名人就能一目了然了:小一岁的左宗棠14岁参加县试,就名列第一,次年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17岁即中秀才;稍晚几年的,康有为幼年时就已经被誉为“神童”,梁启超更是11岁就考中了秀才,16岁中了举人。
许多年后,这个孩子在回顾自己时,曾自评为“吾生平短于才”、“秉志愚柔”——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则是,“‘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愚钝”。
这个孩子就是曾国藩,也是后来备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推崇的一代大儒,曾文正公。

二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之前的传闻已经成为了笑谈,而“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成为了人们更关注的话题。
于是再去纵观这个人的生平往事,他一生共计写过1500余封家书,仅有300余封得以流传,其中的100多篇辗转收录为了今天的《曾国藩家书》。
这些寻常书信中所蕴含的处世之道、家教理念对于现代社会富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在《曾国藩家书》的修身篇和劝学篇里,曾国藩记录了自己在“为人处事”上恪守了终身的诸多信条,和与小辈们谈论“为学之道”时多次较为重要的箴言。
在个人修身方面,曾国藩强调高度自律、极为克制的自我约束理念,如“息心忍耐”、“力除牢骚”、“不苟不懈”、“虚心请教”、“谨慎为主”、“自立自强”、“时刻悔悟”等;在治学劝学上,曾国藩切合自身经历,向亲友们传授了自己的读经史、习字、作文等方法,和对于求学、阅书、拜师等方面的看法,所有这些思考,也是他在浮沉起落的人生命运中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如果以人为镜,将这些对于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的主题一一整理标记出来,我们会从诸多信条中发现,曾国藩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他经过长期的准备而厚积薄发的结果。
在未起之前,曾国藩一直在积蓄力量,不轻易在人前显示自己的真实实力,能暂屈人下,伺机而动;为了能使自己自己平稳地走向成功,且不被他人算计,曾国藩非常注意保存实力;为了能赢得上级的信任,他宁愿把自己的功劳让给别人……在一步步是走向了位高权重后,官位显赫之时的他仍然保持了自己一贯的谨慎和有所保留的行事风格。
在这两篇家书中,也可以多次看到他“处事须严密,出言应谨慎”的主张,教育家中子弟要谦恭谨慎。
但是,从前文中天资平庸的孩子,到这样一个后世所看到的属于曾国藩的历史形象,其中发生的成长和转变,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三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禀父母·谨守父亲保身之则(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清)曾国藩
写下这封信的这一年,是曾国藩人生中的第三十年。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著名作者张宏杰对此做过很详尽的分析:“30岁之前的曾国藩基本是个平庸的人,性格方面也有很多平常人的缺点。”
但幸运的是,曾国藩自己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为此痛改前非——他决心为自己树立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人生设定。
每个人都在做人生规划?为什么偏偏是他的这一个格外特殊?
一来,由这个设定展开的所有信条都能够高度地服己、服人;
二来,他要为此进行长达数十年的艰难坚持、自我贯彻,所有这些努力,都将是一种自我约束和克制。
《千年悖论》里曾这样评价,“曾国藩以他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把‘曾国藩’这个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么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成分。”
正是这一种毫厘之间的律己和克制感,在三十年后显现出定数一般的区别来,也使得曾国藩迈出了从庸人到圣贤的第一步。
曾文正公作为圣贤形象的起点,由此得以略窥一二:与其说这每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是写给长辈、手足,不如说,原本也是曾国藩写给自己、用以时时耳提面命的自省之书。

四
一朝天子一朝臣,作为历经道光、咸丰、同治的三朝元老,曾国藩在官场宦海沉浮了一生。
从一介文人、理学家到带兵点将的武生,从朝廷官员到“编外”地方军阀,几番起落,在后世看来,这是一位生逢其时的大人物。
然而如果将时间倒退二三十年,究其后半生之前,只是一介寻常凡人,若说有什么过人之处,无非是能够高度自我苛求的意志力,但也正是这唯一处的不凡之处,一次又一次成就了他。
如果说每个人来到这世上,都是怀揣着某种使命,换句话说,就是要明确自己将实现什么样的人生志向、朝着什么样的目标作出努力——由此再来看曾国藩,你会发现,他这一生的终极意义,就是要用尽自己全部的后天努力成为一个“化身”。
“化身”这个词也许显得突兀,但这正是曾国藩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生设定:此生不仅要成仁,还要成为一座金光闪闪的“圣贤之身”。
圣贤何以成为圣贤?
通读书中“修身”和“劝学”两篇的主题:“谨守保身之则”、“只问积劳不问成名”、“万望勿恼勿怒”、“必须逆来顺受”、 “须戒傲惰二字”等,它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圣贤”形象是近乎完美的、刨除人性的存在,刨除了人性里面的贪、嗔、痴、爱、恶、憎,剩下来的便是一个人身上可以绽放神性的部分了。
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深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思想熏陶,因而他为自己规划的人生志向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观的充分实现。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于瑰丽、令人唏嘘的人生设定,正是出自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形象。
各位书友,今天的共读就到这里,时代和命运的永恒交织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使得曾国藩在圣贤形象基础上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
明天的共读,我们将一起揭开曾国藩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