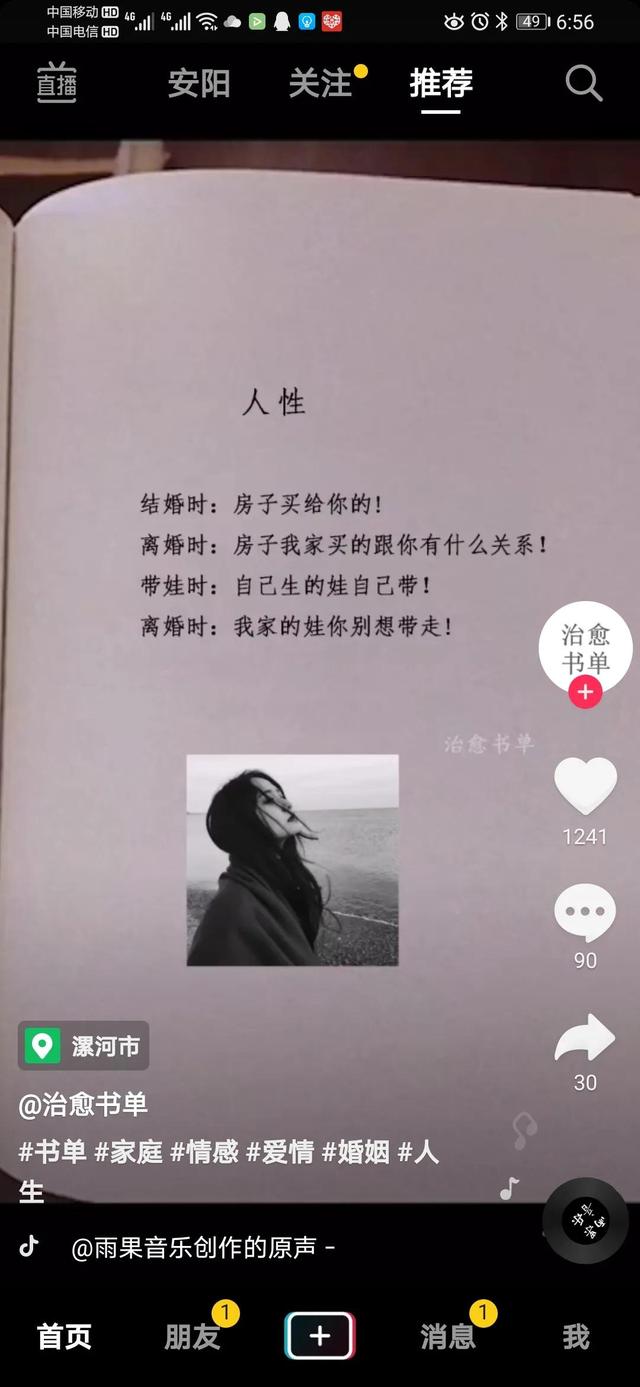央广网浮梁3月4日消息(王军荣)“这是一个让人挣扎的岗位”,李玉英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水利有这么可怕吗?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水利有这么可怕吗
央广网浮梁3月4日消息(王军荣)“这是一个让人挣扎的岗位”,李玉英说。
我们是在吕蒙镇水利管理站办公室见的面。该镇位于举世闻名的瓷都景德镇市昌江区。吕蒙镇位于市区南郊,进了政府大楼一楼右侧的顶头的有两间连着了房间。这套间是许多乡镇水利站通常的布局,外间用于办公和汛期值班,内间用于储存雨衣胶鞋及照明灯等防汛设备。此外,里面还铺了一张床,准备值班人员夜间休息用的。
比起镇里其他站所的办公室来,水利站似乎更显拥挤、更杂乱,也更充实。墙上挂了镇防汛形势图,水利站人员工作职责表,防汛抢险应急队伍名单及水系图等图表把墙塞满了。十几平米的房间内三张办公桌成“品”字形靠窗放着,桌面上文件摞成堆,只剩下中间一个电脑屏幕和一小块放手的地方。办公室变成了杂屋间,墙角放了一堆工地测量用的仪器,又放着一手持推车式测距仪,一看是刚从工地上下来,上面沾着不少新鲜的黄泥……一到这里,突然一种沉重涌上心头。
是的,世界瓷都、昌江、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女人……这些,只会让你感觉文化、生态、休闲。但是当面对这个全市唯一一个女水利站长,我想那些曾经在中国改革前农村生产队工作过的中国人一定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表面的相似之下,有一种截然的不同。在中国,水务站是水行政管理最低一层机构,低到都算不得是一个部门,只是乡镇中负责处理水利综合事务的一个站所。李玉英所在的水利站刚刚经历建制方面的改革,去年1月,吕蒙镇刚从市高新区划回昌江区,原来的农水局也改回了水利站。与1年前在农水局不同,不需要应对市水务局和省水利厅各样的培训和工程申报等会议。尽管这些事情现在昌江区水务局都给代劳了,但镇里作为一级政府,机构全面而人员紧张,2007年至今,除了担任水利站站长,李玉英一直兼任镇新农村办公室的副主任,此外还当了几个项目部的出纳,她说常常“很难定位自己”。
离过年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到来时,年终各项工作的接近扫尾,这或许该是持续了近1年忙碌期的暂停。但在镇里并没有看到即将歇工的迹象,自从近期景德镇市全面启动了西城区水系综合治理项目以来,一连串前期工作接踵而至。征用土地,拆迁房屋,测量工地,群众座谈,协调会议……农田水利建设本来就集中在冬春季节,这让李玉英有些应对无暇。然而工作继续朝她加码,几天前镇里工会的出纳被狗咬了,赶上过年发福利的时候,这活儿镇里又让李玉英顶上了。
3个月前,我已经应邀来采写这个女站长的。当时我有些踌躇“没有时间,而且关于基层水利人省里才专门出了一本书”,我是这么对景德镇市水务局总支廖新生书记说的。何况全省乡镇有1300多个,水利站站长多得很。在廖的一再要求下,我还是来了。
都是些平凡的事情,这让我无从走笔。我们在站办公室才喝了几口茶,谈话被迫打断好几回。一个工作人员从村里开会回来,和李玉英谈起征地的进展,又进来一个施工监理,才从水利工地上回来,脚上踏着一鞋的黄泥巴,向李玉英抱怨工作条件不够好。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遇到的每个人——李玉英都先递上一个纸杯泡的绿茶。这让她不得不中断接待,拿水瓶出去打了一回开水好给挤在办公室的人随时续杯。另外也是一个重要印象,李玉英很随和地回答那些上门来协调工作的人,似乎这些事情早就在她心里酝酿了很久,这让对方听起来很舒坦。东方女人逆来顺受和处事麻利的优点毫无痕迹拼接在她身上。
忙乎了一阵子,李玉英似乎感觉到了我未遂的采访。我里头预置2个小时的谈话计划踩不上这节奏了。来之前贮存在头脑中的提纲,变得模糊,一时竟找不到了调门,因为我本来是想让她带我们去水利工程施工工地,现场作个访谈,然后给拍个工作照。而现在,对这个水利站长的理解,却再度回到狭窄而繁杂的办公室。
“你是怎么担任了这个职务?”我问李玉英。她身着银灰色的羽绒服配着两只黄绿色的袖套,色差太大显得很协调,黑色皮筋扎的马尾发,显然没有经过美发打理,不像是其它政府工作的女人,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很多,更看不出时髦的痕迹。
这是既老套又无趣的提问。是啊,在20年前,我们社会的就业渠道并不宽阔,作为一个刚从江西省轻工业学校学校毕业的女生,会有多少机会拣选呢?李玉英是从一个叫官庄村委会的地方度过走入社会后的最初8年,然后,调入吕蒙乡(今日的吕蒙镇)工作,在这里,李玉英经历了她人生的另一次关键转变。2年后,因为当时水利站长到龄退休,在人手稀缺的情况下,她莫名地走上站长的岗位。
“哈哈,或许叫做‘被当’更适合些”。李玉英说,她说自己其实没有这个想法,却没有拒绝的资格。“在接任水务站站长时时我自已也曾犹豫过,生怕做不下来,总认为这应该是男性应该从事的岗位。”
这些年众多的水利项目激发了李玉英的工作欲望,大张旗鼓的水利建设热潮把她从一个门外汉训练成为一个土专家。2007年,刚接手水利站工作的时候,前任仅给了一大堆的手机号码。“这些都是业务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业务上不懂的就打电话问。”老站长很认真地告诉她。
“哭过很多次,”李玉英说。第一次上水库,也不知具体情况,她穿着裙子就去了,谁知走了一遍下来,脚全被路边的杂草划伤了,穿着高跟鞋也险些报废。从那以后,李玉英几乎告别了了裙子和高跟鞋。中国的古话很有道理,“路在脚下,路在嘴上”,前任站长留下的那一堆电话号码发挥了关键作用,靠着脑勤、嘴勤和脚勤,李玉英渐渐适应了手头的工作。
“唯一不适应的就是太忙。”李玉英给我杯里加了些开水,继续说。现在工作主要的工作是乡镇防汛、农村饮水,渠道维修和水库除险加固。几乎上级水利的各个部门最后都归结我一个人上了。特别是在高新区那阵子,由于下面只有一个乡镇 ,高新区农水局只有两个人,管全乡大农业,水利这块全落在她一人身上。
她是靠苦熬度过了那段最累的时光。作为女人,2010年迎来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结婚一年后的她作了妈妈。但工作依然按部就班,婆婆已经年届古稀,身体不好,站长、妻子、妈妈,她无力地在三个角色中挣扎。
“有个农水项目要去省城审核,当时我小孩才半岁,还在哺乳。那天项目修改了很多,一直到傍晚才通过。我只能搭乘最后一班高客回来。当时坐在车上,看上路边街灯,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味道。”为了哺乳工作两不误,另一次,李玉英带着丈夫和孩子一同出差到省城,参加一个工程审核会。在那年全区年度农口工作会上,她被评为先进个人。
我们的谈话说不上热烈,她算不上是能说会道。但凝重的气氛并不是由于工作的本身,这些年由于国家大幅度增加基层水利的投入,为农业和生态带来活力的同时,带给基层水利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是我知道的。社会对水利工作者的要求、家庭中必须的义务和女人自身对生活的盼望,已把李玉英模成一个更侧重实干的人。以至于结婚前打羽毛球,唱卡拉OK,节假日出去游玩等爱好她早已经放弃。
工程设计、施工本来就和女人的形像的不符,何况危险常常悄然伴随。去年汛期,李玉英有一天六次去了同一座水库,“没有遇过那么猛烈的风雨,当时伞都吹到水库里去了,人被风和雨吹得几乎不能呼吸。”据李玉英回忆,当时她死死的拽着坝上的那个搅拌机,才没有被吹到水库里去。
“当然,现在的情况要好的多”,她说。水库除险结束了,小农水渠系建设也接近了尾声,更好的是小孩现在已经上小学了。但对于一个作水利站长的女人说,劳累确是深深刻入思维中的。而且,作为镇里的防汛办主任,两个月后就要进入汛期,那时,电话传真特别多。而且经常是在正常上班时间之外。“我自己无所谓,但总是早晚电话不断,吵醒家人令我感内疚。我常常问自己,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合适吗?”
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合适吗?我试着作出解释:舍小家为大家,干事业都不容易,你的付出让很多家庭得到安全,社会会记得水利人的付出,我感到自己语言的笨拙与无力,随即意识到,这解释背后的焦点——一切都源于代价,只是女人,你要当个水利站长代价有点“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