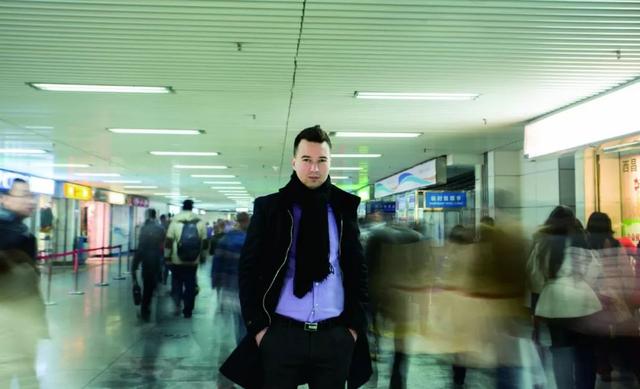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见解都未超出中国隋唐普通禅僧的常识水平,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女生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女生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维特根斯坦的所有见解都未超出中国隋唐普通禅僧的常识水平。
"对无法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
这句话如果是一个唐宋的普通秀才写出来的,那在唐宋文人圈子里绝不会引起惊讶,也绝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秀才的原创,秀才本人也不会被认为有任何值得称道之处,因为这显然是拾禅僧之牙慧。在文人认知里,这和“道可道非常道”一样是常识。
实际上,《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中的观点,都有这个问题,禅宗常识与其相比,关于逻辑、语言、概念、辨析、表达、沟通等问题,尤其在终极问题的探究上,早就远远超越了维特根斯坦的认知水平,并且非常成熟圆融。
在中国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常识中,无为法,或终极问题,或世界的实相,是脱离语言的,是无法用语言体系映射的,是无法用语言交流和传授的,陷在语言体系中试图辨析和探究终极问题,肯定是头上安头自欺欺人之举。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学僧入门常识,维特根斯坦只知前半句,未知后半句,看到了逻辑的局限性,却还试图在逻辑体系里讲道理,只会让初级禅僧失笑,维特根斯坦知道不能安立在言语上,却指望安立在心行上,典型的才出虎口又入狼窝,是他前期思想不成熟的地方,这一点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
实际上,这是几乎所有西哲的痼疾。
维特根斯坦明白哲学必须直面语言,“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明白试图创造一套严格的可以表述哲学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但他只意识到了“边界”,也停止于“边界”,以为这样就可以“终结问题”,而在禅宗那里,边界问题是常识,而超越边界的终极问题也是清楚的,如何处理边界内外的态度和方法也是清楚的,否则就不存在悟后起修的传承了。
禅宗语录公案之于禅僧,就像论语之于儒生,当然是常识级别的。而公案里随处可见“说似一物即不中”、“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道”、“无情说法”、“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之类的开示,早就深刻认识到了语言的边界问题,区别在于,禅宗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不依赖语言,又不摒弃语言,却能指向语言背后,这是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西哲始终没有做到的。超越边界的能力他没有,超越之后的是什么他更不知道。
且问:西方语言所反映的边界,和东方语言所反映的边界,是一还是二?原始人语言所反映的边界,和机器人语言所反映的边界,是一还是二?
禅宗明确知道,这个“语言”下面,本有更底层的东西,超越语言与思想,不因东方语言和西方语言而有不同,不因各人水平高下而有不同,不因世界的唯物呈现和唯心呈现而不同。讨论公共语言和私人语言是无聊或不重要的,属于小学生给同桌出题自娱自乐,可以打一百分,但不属于真正的学问和成长。
"对无法言说之物,应保持沉默"。
且问:这个沉默是知还是不知?是可以体悟而保持沉默,还是不可体悟而不得不保持沉默?
黄龙祖心举拳问僧:唤作拳头则触,不唤作拳头则背,唤作甚么?
对禅僧而言,对无法言说之物,不要试图通过语言说清楚,所以不可说,但语言依然可以作为指月之手,而那个不可言说的东西,那个终极问题,实可经此开示,实可证悟。
禅宗是不依赖语言,而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方式,激发语言和思想背后的那个东西,以通达“事实以及这些就是一切事实这个情况”,这从理论到实践都远比维特根斯坦高明。而“激发语言和思想背后的那个东西”在维特根斯坦早期是不在场的,晚期他称之为“直觉”,禅宗称之为“自性”。
沉默并无不可,但绝非只有沉默。哲学止于语言?
面对德山有无之问,沩山灵佑保持沉默,坐断天下舌头。但德山棒、临济喝,与沩山一默并无抵触,南泉斩猫,赵州吃茶,雪峰滚球,普化摇铃,都指向无法言说之物,这是维特根斯坦远未触达的。
禅宗并不认为“不立文字”就不能用语言引导学僧开悟,历代“语录公案”不断,也不认为只有语言可以引导学僧开悟,历代“行为艺术”不断,但同时更指出这些包括语言在内的交流只是随缘对机,其实都是“老婆心切不惜落草”的“一勺恶水”而已,不可执于语言,不可昧于思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体”尚不知,何谈所“用”。对语言哲学的认识,维特根斯坦远不彻底,于是更谈不上对言语后面的世界的探究和正确认识,于是基于其半吊子认知的哲学研究只能是个不成熟的半成品。
洞山良价:“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是维特根斯坦从未梦见的境地,直到晚年也没有打开这个格局。
南泉普愿:“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
南岳怀让:“修证既不无,污染即不得”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岂是维特根斯坦走到半山腰就急着写词谱曲感慨大好山河可比?
语言的局限性和语言的有效性是一体的,西哲往往明白“一体两面”的道理,却很难把“两面”去掉,真正领悟“一体”,所以维特根斯坦用早期的认知推出了“哲学的终结”之类的东西,显然落了下乘,从大人聊正事聊成了小孩开玩笑,这是未开悟的入门学僧都不可能犯的错误。因为否定不代表终结,空不代表寂灭或虚无,这些在佛教中是顽空断见,“离四句、绝百非”是大乘入门学僧的常识。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明白了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生生不息的,是哲学的基础和源泉,所以哲学的本质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解决,在“游戏”中理解游戏。这合于禅宗“平常心是道”的看法,合于“喝水搬柴即是神通”“饥来吃饭困来眠”的禅学常识,但并不明白“好事不如无”,并未达到“觅心了不可得”和“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统一,并未达到“事理不二、体用双彰”的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明白了应该在生活中研究语言,而不是将语言当成一个“本体” ,他开始搞教育编词典之类的实践,才是在“事理体用”上开始摸到门了,正在开始修证,而这对于禅宗学僧而言,并非开悟者的悟后起修,而是知解宗徒的日常修证,为开悟做准备的路上而已,一辈子也没越过第一道门槛。
“事理不二,体用双彰”是圆融的、是生机勃勃活力无穷的,这不仅是哲思哲理上的超越,更是有对生存态度的明示,和对提升思想的具体指导,无论在“本质”层面,还是在“发生”层面,大乘中观绝不会导向西哲钻牛角尖的偏枯狭隘,维特根斯坦虽然指出了西哲的哲学病,但其实自己也陷入了这种哲学病的习气中,这在禅宗学僧中都算不上根器好的。
玩逻辑玩分析,禅宗不乏“三玄三要”、“君臣五位”、“四料简”、“四照用”这一类掰开了揉碎了讲的,曹洞宗绵密回互,敲唱为用,沩仰宗语默不露,明暗交驰,实际上讲课很细腻,充分运用语言的有效性,充分尊重逻辑的作用,但绝不被语言和逻辑所绑架,而是搞情境教学,讲究“啄啐同时“让主客体同时起作用,这种全息的境界是维特根斯坦从未想到的,他知道不能被语言逻辑绑架,就只能止步于此,而禅僧知道不能被绑架,却无碍继续前行。云门宗更是以“一字禅”三位一体的做到“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的境界,这是维特根斯坦做梦也达不到的。
对语言哲学的认知深度,维特根斯坦远不如禅宗在唐朝就已成熟的水平,对语言和逻辑的超越和运用更是差的太远,直到晚年才开始摸索。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正在向禅宗思想前进,其提出的“语言游戏说”、“不要去想而要去看”,全都契合禅宗思想的方向,可惜未遇明师点拨,未能从“止观”、“镜鉴”的知见,前进到“无所将来”、“不借借”的水平,维特根斯坦若有幸学习过中国禅宗的认知体系,那么以他虽非顶级但也一流的资质,如果能有效对治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带来的debuff,此生开悟甚至很年轻就开悟是问题不大的,但因为没有接触这些禅宗智慧,最终停留在了门槛上。维特根斯坦的探索和局限,正是历代西哲在东方思想面前始终理解不到位的形象缩影,他和海德格尔都很有典型意义。
实际上,当代西哲也和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一样,正不断向真正的东方哲学靠拢,但他们的通病就是只在“事理”上熬脑力,却在“体用”上长期处于盲区,这还需要一个很长的阶段让他们明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