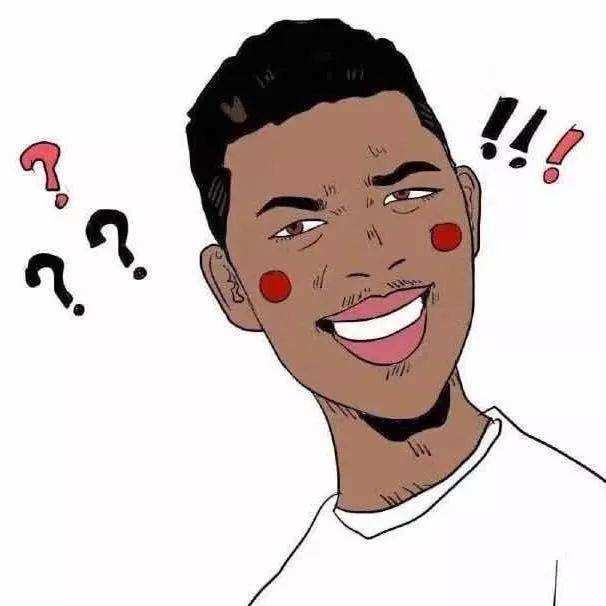渤海早报记者 杨扬
“南开杯”第三届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今晚即将在中国大戏院落下帷幕。在过去的两天内,28部作品在4场决赛竞演中一一亮相,接受了津门相声界艺术家、专家和普通观众的检验。海内外的专业、业余相声作者踊跃投稿创作新作品,年轻的相声演员们积极参赛表演新作品,连续六年三届大赛都在为相声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添柴加火。但在一片可喜的气象中,老一辈相声艺术家、理论家和创作者,也发现了当今相声行业存在的许多问题和隐忧。
新作品怎样才能留住?
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自2009年举办以来,已经走过了六个年头。首届大赛曾征集到1000多件作品,引爆了海内外相声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创作热情。第二、三届大赛征集到的作品虽然减少至300余件,但作品质量稳步提高,特别是一些大学教授、各行业专家和自由撰稿人也拿起笔来创作相声,为新作品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气象。然而,三届大赛推出了近百部优秀新作,真正能在剧场、茶馆的日常演出中传得开、留得住的作品却并不多。
为何上“新活”那么难?怎样才能让优秀的新作品留在舞台上?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渤海早报记者的问题引起了在场艺术家、理论家的热烈探讨。本届大赛评委会主任、著名相声作家王鸣禄和大赛评委、相声名家魏文亮,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上“新活”风险大,魏文亮更是为一线的相声演员演新作品所要承受的压力而倍感忧心。“现在有些剧场、茶馆的经营者,或者说一些所谓的‘班主’,眼里只有票房,演员今天把观众说走了,明天就别来了!今天演出效果不好,明天就减演出费!就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每届大赛都涌现出那么多好节目,可是最终很多节目都没人说,就因为演员不愿意说,怕说新节目把观众说走了。”《相声大词典》副主编、相声理论家高玉琮则提到媒体在传播相声时的“副作用”,“有好多好相声,比如牛群演的《领导冒号》、姜昆演的《虎口遐想》、马季的《五官争功》等,电视台里一放,别人谁还敢演?”
在王鸣禄看来,一部新创作出来的好作品,想要留在舞台上,必须经过演出实践的千锤百炼,而这个过程往往并非一人一时之功。“很多传统节目,其实都是群众创作的结晶。同一段作品,全国各地演员都在演,有的作品至少能有十个版本,最终流传下来的是各个版本的集中和精华。”因此他很想恢复作品的竞争模式,一部新作品不是交给一对演员表演就行,而是交给三四对乃至更多演员来竞争,“一个作品大家都来说,才能形成保留节目。”让王鸣禄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已经有一些年轻演员意识到新作品的重要性,“成熟的老作品确实演出效果好,但总演,观众会腻的。观众也想听新鲜的。青年演员已经有了危机感,渴望优秀的新作品。这次参赛的部分作品,就已经有演员在他们自己的演出场所里反复让观众检验过,用行里的话来说就是‘压活’。”王鸣禄还提供了过去的经验,“过去我们的相声演出团体,对上‘新活’是有保证机制的,演员每一到两个月,必须上一个新节目。新节目一般都放在最好的场口,也就是整场演出的第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观众还没坐稳,第二个节目观众才开始进入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耳朵开开了’,到了第三个节目,观众状态正好,这时候上新节目。”
创作队伍如何培育呵护?
老舍先生曾说过,相声是最难写的。对此,写了几十年相声的王鸣禄深有体会。“想要写好相声,既需要掌握观众的心理,也需要掌握演员的心理,而且还往往要根据演员的特长有针对性地写。写相声是需要天赋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写出幽默感。台上演着可乐,可台下的创作其实是很枯燥的。”正因为创作的艰难,全国的职业相声作者不多,且人数在不断萎缩,不仅让王鸣禄也让许多相声演员感到焦虑。而发现、培养相声作者正是举办“南开杯”全国(天津)相声新作品大赛的一大初衷。
向大赛投稿的业余作者中出现了许多修养高、见识广的大学教授、各行业专家以及一些视角独特的自由撰稿人,令王鸣禄感到特别高兴。但业余作者有他们的薄弱之处,“业余作者毕竟对相声本身的艺术规律、舞台效果的呈现、观众的心理、演员的习惯不了解,或者了解比较少,许多作品都不是拿来就能用的,必须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因为缺少作者,一些演员干脆自己拿起笔来写相声,“演员自己创作有好处,因为他们有长年的舞台实践,对相声更了解,但很多演员的文学修养不足,写出的作品在舞台上虽然能把观众逗乐,但质量和品位不一定高。”王鸣禄还提到,平时有些演员在对一段作品进行了二度创作之后,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署进作者一栏,“一段节目,本来观众只记得谁演的,很难记住作者是谁,演员非要挂上自己的名字,那作者就更没人知道了。”为了尽可能鼓励作者的积极性,本届大赛所有参赛作品只给原作者署名。“比如给苗阜王声的春晚相声写剧本的刘春山,是咱们天津青年演员中创作能力很强的人,这次管新成、张尧表演的参赛作品《谁信那》,就找了他给进行二度加工,但我们没有把刘春山的名字挂在原作者后面。演员加工得再好,我们也不给署名,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扶持作者。”王鸣禄说。
“不正之风”何时才能刹住?
新作品难“出头”,新作者难培养,固然令相声界的老艺术家们忧心,更让他们焦虑不已的是相声行业出现的不正之风。历届相声新作品大赛都在极力倡导“干净的相声”“绿色的相声”“能让全家老少一起听的相声”,针对的就是这股不正之风。
一提到这个话题,魏文亮显得有些激动。“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为了提升相声的艺术品位,对该说什么样的相声、怎样说相声煞费苦心。侯宝林等前辈大师在北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把相声洗刷得多么干净!可是现在呢?乌七八糟,瞎说八道,为了上座率,什么脏的、臭的、黄的都敢说,我心里特别难过。还有的演员,带着录音笔偷着把别人的节目录下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自己拿来就用,艺德何在?”在大赛开幕演出前,天津文联主席陈洪接受渤海早报记者采访,也提到相声行业的不正之风,“我还记得四五年前,看一位相声演员的专场演出,当时觉得确实不错。可是之后再看,有的内容其实少儿不宜。同一个人的演出,有这样的变化,一是他没有新的东西,二是他对市场判断有误。”尽管目前一些演脏包袱、臭包袱乃至涉黄内容的相声票房很火,但在陈洪看来,长此以往,是相声的自杀。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鸣禄认为,在相声不景气的那段时间,有些演员主动走向市场,把相声带回了人们的视线,但为了票房,传统相声里本已丢掉的糟粕也被捡了回来,让年轻人误以为这样说相声才火爆、才挣钱,对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旧社会的传统相声里确实有脏活、臭活,有低俗的内容,就像《笑林广记》里也有黄段子,但那是为了增添乐趣,绝不是骂大街!”王鸣禄特别担心一些高校里的相声社团,“比茶馆里说的还脏”,“有人辩解,说脏活是因为观众爱看。适应观众无可厚非,但适应观众最终是为了征服观众。相声不仅是逗人一笑。旧社会的平民百姓很少有机会读书认字,就是通过相声、评书、戏曲的演出了解历史,懂得道理,在娱乐中受到社会教育。但我们现在把相声的这个功能给丢了,倒退得太厉害!”
昨天上午,由中国曲协组织的曲艺界行风建设调研座谈会,趁相声新作品大赛期间在谦祥益文苑召开,许多老艺人、中年的茶馆经营者和年轻的相声演员,都在探讨如何出台行业规范,扭转这股不正之风。他们的一个共识是,行业内的不正之风,不仅与“唯钱是从”的思想有关。有的作品没了低俗包袱观众不乐,有的演员没有创作技巧就堆砌网络段子,创作力的匮乏也是低俗相声盛行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公认的行业标准,“没规矩”。老艺人们不禁回忆起过去的“规矩”。魏文亮说:“我们年轻时,每场演出,无论演到多晚,结束之后一定要开总结会,谁哪里说得不对,哪个包袱、哪句话用得不合适,都要讨论,要是有人刨了后面的活,更得严厉批评写检查。那会儿我跟李伯祥还年轻,经常赶不上末班公交车,我们哥俩就一路翻着跟头走回去。现在谁管啊?只要人们还需要笑声,相声的魅力就永存,因为这是扎根在泥土中的艺术,是最符合人民需要的艺术。但相声的生命力,经不起百般糟蹋。我们得尊重我们的艺术,让它能健康地发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