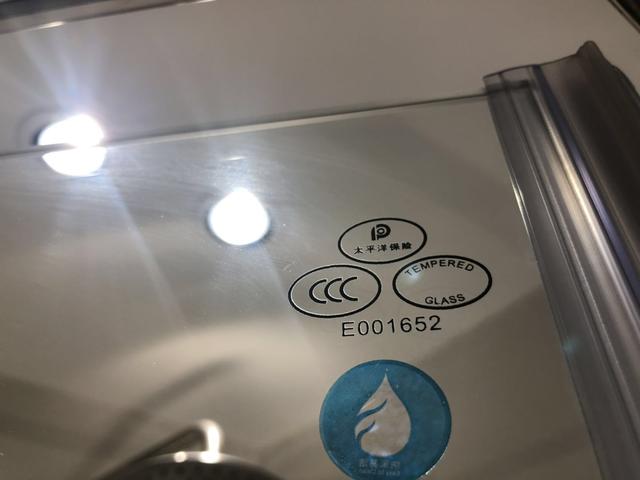我第一次怀疑人生,从看聊斋开始。八零年代经典电视剧除了西游记外,还有一部至今也没有多少人记起的《聊斋志异》。《聊斋》激活了“我”的意识,让我感觉到身体将我的灵魂与外界分离开来,因此在“我”之外还有其他东西的存在,而这些东西是我不曾了解,更不可能认识和掌握,但它们却充斥在整个冥冥时空,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绽放出偶尔的跳动,就如放置在空无一人屋里的一盆水,不知为何“咚”的一声,然后平静的水面泛起阵阵波澜,你不知这股搅动水面的力量从何而来,但你能若隐若现的察觉到这股力量的存在。由此我开始意识到,有一股未知隐藏在我所熟知的环境,我居然从未觉察,于是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助,感觉到内心的孤独,从那以后我开始切实的体会到,什么叫恐惧。
电视剧《聊斋》的“开机”画面依然让我颤栗不已。一开始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诡异黑暗,然后似乎有些影影绰绰,似乎有些东西在闪动,定睛一看原来是荒草在黑风的吹动下摇曳,接着一个让我至今想到就难以入睡,一看到就触发我全身鸡皮疙瘩的事物出现—白色纸灯笼。灯笼中的烛光忽亮忽灭,让人感觉似乎是在半空中飘荡,我现在看到有人家在门口挂灯笼心里就不舒服,不管灯笼是红是白,它总能在汗流浃背的酷暑夜晚,让我感觉到一股阴森森的拔凉从后背莫名其妙的升起,后来看到很多鬼故事,灵异现象出现的标志就是门口大灯笼里面的烛光突然被吹灭或是被风吹得摇摆不停。慢慢的白灯笼后面的形象出现,好在是个中年人而不是鬼,这让当时年幼的我大大舒一口气,这个人轻轻的推开茅草屋的木门,走到书桌前,点亮火烛,在微弱的烛光下开始奋笔疾书,一篇篇令人惊悚呼号的灵异故事徐徐在笔下铺开,原来这个人就是蒲松龄。

《聊斋》是中国灵异文学作品中最浪漫,最温情脉脉的名著。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鬼怪创造,像魏晋时期干宝的《搜神记》还是唐朝时期的志怪文学,纯粹在于构造各种虚无莫测的超自然幻想,本身没有明确意义,也就是为了“搞鬼”而搞鬼。而《聊斋》不同,它虽然讲述很多鬼狐神怪,但最终着意还是在人情,它的故事要不就是对人性黑暗进行偏僻入里的鞭挞,要不就是对身处不幸遭遇中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当我读《聊斋》时,我总被书中描绘的阴曹地府,阎罗小鬼,黑白无常等形象吓得直打哆嗦,也会被冤魂索命,狐妖报恩等情节惊叹不已,我极其佩服蒲松龄磅礴的想象力,他居然构建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幽冥系统,在读《聊斋》时,我的身心能从压力大,节奏快的现代物质社会中抽脱而出,在蒲松龄的指引下去游历另一个完全不受物理定律约束的灵幻世界,灵魂在蒲松龄的世界里酣畅淋漓的云游翱翔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肉体,我原有的紧张,焦虑,愤恨,妒忌等负面情绪几乎一扫而光。
《聊斋》中有很多让我感慨万千,嘘唏不已,甚至泪流满面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的灵魂一起,钻入蒲松龄光怪陆离的幽冥世界,一起感受一个我很喜欢,也很促动我的灵异故事,叫《凤阳人士》,它离奇而又诡异,更令人诧异的是你又会觉得它异常真实。话说安徽凤阳有个书生外出游学,久不归家,独守空闺的妻子对其是日思夜想。一天深夜,妻子在冰冷的月光中喟叹,在对远方爱人的思念中,意识渐渐模糊,当她正要在书桌前睡着,突然一个围着大红披风的美人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蹦出来,质问她想不想见老公,妻子刚一点头,美人不由分说就拉着她往外跑,妻子脚小追不上,美人就脱下自己的鞋给它穿。
没走多远,妻子居然看见丈夫骑着一匹白骡过来。美人不说自己是谁便把夫妻两领回自己家,并在庭院摆酒庆祝他两久别重逢。饮酒时,丈夫居然用色眯眯的眼神在美人身上不要脸的四处游移,并把妻子晾在一边,对美人说很多暧昧之言,妻子只好在一旁生闷气。丈夫厚颜无耻的让美人给他唱小曲儿,曲儿名叫《占卦》,是扬州清曲,歌词优美多情: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这首曲儿在幽怨凄美中有一丝冰凉的诡异。一曲唱罢,美女假装酒醉进入闺房,哪知丈夫居然像条哈巴狗一样,捏着人家的裙角寡廉鲜耻的也钻进去。妻子在外听着两人浪荡的调笑,在又羞又恨中夺门而出。在门外她突然遇到弟弟三郎并把自己受到的羞辱告诉他,弟弟气得冲入院子,不由分说举起一块大石头狠狠的往美人闺房的窗户砸过去,只听见美人一声惨叫,大呼丈夫被砸死了。妻子吓坏了后悔不迭并埋怨三郎,三郎窝火甩手不管,妻子急火攻心一下子惊醒过来,在神志慢慢缓和后,才意识到原来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第二天丈夫居然回来了,还真骑了白骡,三郎闻讯姐夫归来也过来串门,妻子把那个梦讲给大家听,没想到丈夫和三郎居然也做了一样的梦,只不过不知道梦中美人是谁。
蒲松龄不愧为文学大师。且不说故事构思上情节乖张,意象含混,单就一个”梦“就能把读者带入诡异的玄冥世界。很多国家民族的民俗文化认为生活中有两样东西是两个平行宇宙的桥梁,一个是镜子,另一个就是梦。而且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抓手,他认为梦是人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释放。在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有三个自我,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例如食欲,性欲,弗洛伊德将其称为力比多,本我特点是无意识,非理性,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如果本我不被控制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泄出来,就会导致违背人伦,道德或法律的行为,因此它必须被压制;”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它对应我们的情绪;而”超我“对应人的理智,它用于压制本我,控制”自我“,”超我“的构建是人文明化,社会化的标志,是人脱离于禽兽的象征。人能组成社会集体,实现分工合作,必须依赖”超我“压制”本我“,如此个人才会自觉遵守社会纪律,执行交易契约,整个社会才能有序稳定的发展。
”超我“对”本我“的压制使得潜意识中的欲望与意识层面上的理性自制发生严重冲突,这常常是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压制对于古代受封建理学束缚的女性特别明显。由于女性对男性存在无法抗拒的性吸引力,因此在寻求绝对稳定的农耕文明里,女人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机制加以强力控制。在明清时期,假道学发展到畸形的地步,为了压制女人性魅力对男性的影响,道学家制定了一系列精神枷锁对女性予以打压控制,例如贞操,三从四德,在家随父外嫁从夫,妻以夫纲等等,这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防止女人释放出”性魔鬼“破坏社会和家族的稳定。清代假道学发展到极致,因此那时的女人更加不幸,按照王小波说法,她们过的是一种”无性,无智,无趣的人生“。那时的女人不能表现出对欲望的所求,任何一点在性事上的主动,都会被批判成”淫荡“,”道德败坏“,她们为人的本能被严格压抑,性爱对她们而言绝对不能是享受,而是一种必须承担的生殖义务。

被压制的欲望必须找到释放的出口,而”梦“正是人们释放被压抑潜意识的常见方式。《凤阳人士》所描述的梦境有三个重要角色,一个是美人,一个是妻子自己,另一个是她弟弟。美人对应妻子的本我,也就是一直被压制的欲望,弟弟三郎是她的自我,也就是情绪,而她自己则是超我。妻子对丈夫有生理和心理双重需求,这种欲望给她带来羞耻感,但理智告诉她不能让波涛汹涌的欲望冲破理智的堤坝,于是她只能借助一个未知第三者表达出来,这个第三者无论如何放肆都不会给她带来伤害。故事里有个重要细节那就美人脱鞋给她穿,在古代女性所穿绣花鞋代表女性的生殖器,当女人向男人表达爱慕并愿意以身相许时,往往把自己的绣花鞋送给她,有些流氓调戏妇女时,也喜欢去脱她脚上的鞋。等美人和丈夫进屋调笑后,妻子的欲望得到变相释放,此时道德和焦虑开始占据上风,在封建礼教压制下,妻子没有反抗丈夫的权力,所以面对丈夫背叛只能愤恨的离开,但是委屈让她在情绪上很愤恨,所以借助弟弟的形象进行报复。在古代流行一种很糟糕的价值观,妻子不能妒忌并阻止丈夫出轨纳妾,因为那会破坏传宗接代大计,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做古人难,做古代女人更难,因此古代女人自杀率特别高,《聊斋》里很多索命厉鬼都是女性,不少都是自杀死的。
出于时代局限性,蒲松龄即使再伟大他也难以理解女性权益和女性的身心解放。蒲松龄敏锐的感知到女性心灵深处难以言说的痛苦,他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于是借助一个故事来表达内心的情绪,艺术的本质就是用形象化的手法传达无法言说的情感,蒲松龄对女性痛苦的觉知来自于他对妻子深沉而笃定的爱,恩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先他而去,他来到亡妻墓前悲哭:”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扣无一应,泪下如流泉。“,写了大量鬼狐神怪的蒲松龄是多么希望逝去的妻子能化鬼化狐,与他再见一面。或许正是蒲松龄对妻子深沉的爱而提升他对女性难言之苦的察觉,于是他在故事中对女性的压抑之苦进行释放,解构,让一速光射入女性阴森冰冷的心灵地窖,让她们的苦被看到,被感知,对他人苦难的深切同情,是蒲松龄除了文学艺术成就外的另一伟大之处。
合上《聊斋》,夜已深沉。感谢蒲松龄,在这个冰冷孤寂的夜晚,给我心灵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
,